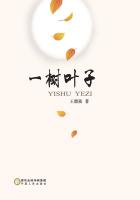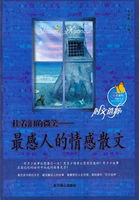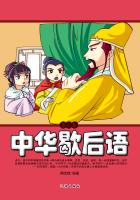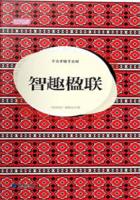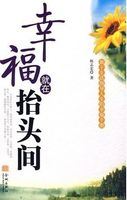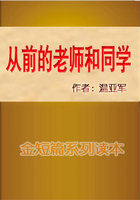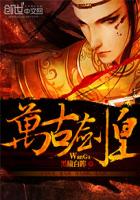这部宏大的作品是对宏大叙事进行自虐式的解构,传统小说叙事的基本叙事策略--虚构,在这里面临根本的挑战。刘震云意识到已经无法完整虚构历史,也难以依靠虚构去获取美学上的充分意味。文学叙述的审美动力来自于语词本身的快乐,如果仅只是追求这种快乐,何以需要四卷200万字的篇幅去建立一个宏大的文学帝国呢?这种矛盾正是“经典性”(canon)严重危机的表征,刘震云的写作冲动完全有可能隐含了创建“经典”的梦想,但在寻找经典的途中,他又不得不损毁经典的本体论存在。它把一个完整的审美客体打碎,并改变为语词的游戏状态。经典性丧失之后,作家在美学上暂时失去方位感,在历史与文本之间犹疑不决,其结果导致语词颠狂式的表达。刘震云最后实际放弃了个人记忆,语词的暂时狂欢式的表达,掩饰了并不充分的个人记忆。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记忆方式处在犹疑不决的状态,个人无法进入历史深处,语词提供的叙述平面则是个人炫智的理想场所。
刘震云试图建构一个乡土中国的完整历史的努力终归失败,他的非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他的失败,他有意制造了这样的失败。《故乡面和花朵》宣告了乡土中国历史记忆的终结,在它之后,所有的完整记忆都必然显得相形见绌,正如在《白鹿原》之后,《故乡面和花朵》必然显得力不从心一样。刘震云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用语词的碎片掩饰了他的困窘。
九十年代的作家既不能不顾一切进行艺术形式实验,制作纯粹的叙述学文本,又不愿回到现实主义的老路,他们处在矛盾的境地,这使他们的小说叙事经常处在虚构/纪实的双重矛盾中。个人记忆不断侵入历史虚构中去,以至于那些历史叙事结果变成个人的精神自传,客观化的历史被个人的自我意识所替代。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作家普遍有一种回到个人直接经验,回到个人化写作的诉求。特别是一批女作家,以讲述个人的内心生活、个人的直接经验故事,激起文坛持续的兴趣。但是,是否真正回到个人生活,回到个人的自传文体中,这也使作家陷入矛盾。在虚构与纪实之间,正如在个人与历史之间,作家并不能准确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刘震云不得不用语词的狂欢戏谑打碎重建历史叙事的幻想;对于其他作家来说,进入到个人化的经验中,则是摆脱历史整体性的有效方式,是“隐私式”的记忆。
2000年,女作家铁凝发表长篇小说《大浴女》,《大浴女》讲述一个年轻女编辑对少女时代的回忆以及在不同时期与两个男人的情爱关系。显然这一回忆追究的故事和生活的实质意义,与她后来经历的情爱挫折和自我超越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以赎罪式的心理情结作为叙事的起点,它试图把小说叙事限定在个人经验的最内在方面;其二,它暖昧的自传体特征表现出脱离历史的潜在愿望。但是,关于个人化的话语并没有真正摆脱历史--这就是铁凝这代有着真实历史经验的一代作家所面对的困难。他们也试图摆脱宏大历史的纠缠,但是,他们最终却要求助于历史。这使外在的、客观化的历史强行侵入小说叙事内部,它除了使命人最内在的记忆发生异化,并且变得虚假之外,并没有深化个人记忆。
小说一开始就把个人的生活史推到极端,直逼人性的痛处。像尹小跳这样看上去纯洁正直的女性,她的内心隐藏着抹不去的记忆阴影(关于妹妹死的自责)。这个动机一直潜伏在故事的主导体系中。但是,小说的叙事并没有按照这个原初动机展开,这个动机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给叙述人以思考的契机。这种原罪应该归结于个人,历史,还是归结于人性?就这一症结问题,作者一直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在叙述中使之悄悄地普遍化,并且随着自我审视和道德升华,叙述人使尹小跳逐步从这个原罪般的动机中解脱出来。爱欲的快感代替了对原罪的审视;关于人生错误的思考代替了原罪的忏悔。
关于原罪的审视并不是真的要进行忏悔,而是进入个人的隐密内心生活的捷径。这是一种坦诚,也是一种掩盖,当一个人把她内心深处的悔恨,即见到亲妹妹死而不救的那种罪恶感都能表达出来,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在小说的叙事中,这一原罪感的发掘,实在是为更具有真实的隐私意义的情爱故事提供了一个铺垫,它同时也是对潜意识泄露的反向遮蔽--不自觉的表达真实意图的一种改写。
如果小说从这里切入个人的内心生活,这部小说也许是中国少有的真正审视个人心理历程并具有个人忏悔意识的作品。但关于个人的精神探索很快就被置换,被超越,个人的故事迅速被思考历史的评价性体系所替代。这个故事的主体已经逐步演变为爱情失败主义者的挽歌。到底那个原罪般的动机与这个动人的挽歌有什么关系呢?原罪被改换成错误,那个不能逾越的人生障碍,又是如何轻易地超越了呢?
通过反思,通过与我们的过去对话,铁凝那些饱满而细致的笔调,使这一切变得亲近。叙述人面对的是个人的整个历史,而不是某个生活死结。我们没有罪,我们经历了生活磨难,我们作出了选择,生活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确实,那个原本以为要起决定作用的赎罪意识,现在完全被一系列生机勃勃的生活掩盖了。
于是,隐私式的自传文体放弃了自我探索,转向完整的历史思考。正如那个原罪意识被转嫁到历史中去一样,关于个人的情爱故事,也转向了对历史的反省。小说一开始试图进行的个人的忏悔和呈现隐私的冲动,并没有构成小说叙事持续的动力,它只是一种叙述策略和修辞手段。相反,小说叙事由此衍生出持续性的反思性叙述(评价)体系。很显然,这种反思性的叙述并没有依照原有动机导向对人的内在的意识揭示,却转向了外部世界,顽强地超越个人而转向历史。就叙述技巧而言,反思性的关键的动力来自开始设定的那个赎罪性的动机,尽管--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样,那个动机被隐瞒和挪用了,但它却给小说叙述注入了反思的契机。叙述人总是在那些人物处在生活的困境时,反思那种不可知的力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把握的历史理性与生活的那些偶然关节的连接,造就了各种可供叙述人反思的契机。这些反思性叙述拓宽了人物的心理世界。但似乎并没有依循内在化的原则确立一条主线反恩人物最根本的自我意识。圆熟的技巧非常老练地使那些思绪闪烁着思想的机智与敏锐,并且恰当地对根本性的人性的、历史的、政治的症结绕道而行。这些生动的反思没有追究人性的原罪,也淡化了历史之恶。
叙述人的反思性叙述确实是生动有力的,她总是可以越过个人的肩头看到背后的历史。反思性的叙述没有纠缠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个人精神的刺痛感淡化了,或者说那种内在性的紧张感消失了,但历史的背景被拓宽了。从个人记忆的深处转向思考一个历史/时代,这部小说的性质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部自我追问的作品,转向了历史化的反思的小说。人性的‘追问,变成了对历史的探究;内心的疏理,变成了外在历史呈现。
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对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进行了一次颠倒:它把全知全能的、本质化优先的历史叙事悬置了,个人化的记忆被作为小说叙事的起点;但个人记忆经历了历史化的反思之后,它被改变成了历史化叙事的起点。个人性的叙事被历史化再次颠倒,但是这种颠倒并没有使个人性发掘变得深刻有力,而是显示出它的虚假性。但是不管如何,铁凝的叙事表明,完整的假定性的历史叙事已经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不得不借助更具亲历色彩的私人性话语作为叙事的起点。过去个人不过是历史叙事的材料;现在,则是它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它没有生长出新的花朵,只是散落着呈现出一些青枝绿叶,与其说它显示了历史主义的倔强性或回光返照,不如说更像是后历史时代的转基因植物。
本质与深度的陷落:重新历史化的困难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无可否认,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社会主义平均化抹平的阶级差别,在当今中国又产生严重分化。去表现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反映社会问题,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路上。苦难主题显示出重新历史化的倾向,文学叙事重新校准价值尺度,重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深度。怀有责任感的一批青年作家,有意反抗九十年代已经形成的崇尚感觉和个人化的文学趋势,他们要重新确立文学的现代性方向。然而,历史似乎很难重演,他们坚定的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叙事,并没有如期建构历史的内在性,相反,大量的非本质的表象和感官崇拜不断从叙事的各个方面涌现出现,它们淹没了批判性的历史意识。
2000年第2期的《花城》杂志登载了荆歇的中篇小说《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该期的《花城》杂志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标题加以强调。作为一位还鲜为人知的优秀小说家,荆歌被忽略是不奇怪的,更何况这篇小说也说不上是荆歌写得最好的小说。像荆歌所有的小说的一样,他能抓住那些富有标志性的要害的因素,把它们进行夸张而偏斜化的处理,略微扭曲它们的本质特征,使之富有戏谑性的效果。这就是荆歌的小说技巧,他能把小说叙述处理得生气勃勃,始终富有张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普通女工青春年华的遭遇,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还难以明确归纳。就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她的一系列不幸以及最终的死亡来看,这里面无疑隐含了苦难主题。
实际上,苦难主题近年受到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关注,鬼子在继《被雨淋湿的河》之后,于1999年发表《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可能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了一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就是找到出走变心的丈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是女儿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也终于死去。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暴露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以及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
2000年,熊正良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历经艰难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的故事。这个家庭似乎是彻底崩溃了,无情无义的父亲,下岗并且有点偏执狂的母亲,做妓女的大姐,做广告模特儿的二姐,再就是无所作为的“我”。
这几篇小说的具体主题无疑有所差异,但都写到了当今底层劳动阶级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苦难”呢?这些“苦难”在小说叙事中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先来看荆歌的《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计帜英的苦难伴随着她的性爱史的发展而走向绝境。计帜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与马科的情爱被刻画得神奇细腻,充分显示了荆歌小说叙述的惊人才华。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马科出事的时候,计帜英正在医院。这一次,计帜英独自一个来医院,是来与医生洽谈,进行她的第三次人工流产的。
小说就此开始呈现一个女工不幸的青春故事。计帜英作为一个普通女工,生活不易,住在破烂不堪的屋子里,守寡的老母,死去的痴呆的哥哥,作为逃犯的男友,以及她历经多次人流等等,这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普通女工的苦难史。但人物并没意识到苦难,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化的生活,都被叙述人作为背景式的历史加以叙述。实际上,青春年华的平静和美好是被爱欲打破的,是主体的选择和爱欲的“谬误”引发了随后的生活变故。爱欲成为生活不幸的根源,但人物却是自觉沉醉于其中,爱欲与个性的合谋造就了苦难。
苦难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热的性欲史,这部历史的主角怀着全部的激情充当了欲望的冒险英雄。像所有性欲史的主角一样,计帜英有着明显的性欲化标志:她长得白晰,惊人的白晰。一白遮千丑,在所有传统审美趣味范围内,“白”构成女人首要的审美效果,也是男性欲望化对象的显著标识。计帜英被设定为这样的角色,她的成长史主要是性欲成熟史。作为另一种性欲化的标识,计帜英的同伴姐妹张妍则是一目了然的欲望化对象。小说再三写到她出众的胸脯,她们躲在被窝里互相抚摸的准同性恋举动,关于处女的猜疑,关于张妍与车间主任偷情的推测等等。
所有这些构成计帜英(与张妍)青春年华的主导内容。随后“姐夫”与马科分别出现,前者使性欲史变得暖昧,而后者则使之变得冒险刺激。这也许就是荆歌的小说出类拔萃之处,那些叙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内在动荡不安的张力,它们一点一点渗出,使生活发生拐点转折、错位或者断裂。马科就是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轻而易举就把计帜英的暖昧的情爱史变成性欲的冒险史。马科从一名商人变成了杀人犯,我们注意到,杀人犯的身份远没有性欲冒险者角色重要,从新疆潜回计帜英家的马科,以一个逃犯的角色从事欲望化英雄的事业,他给计帜英的印象是,“异样的感觉”,“既让她痛恨,又不可抗拒”。最后给计帜英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并不是贫病交加的物质生活,而是与性有关的交易。马科以五千元的价格,把计帜英出卖给一个陌生男人。这个结局当然可以读解为是精神破灭导致的后果,但在小说叙事的现实生活层面上,它依然是关于性的活动。作为一段“性史”,它在叙事层面上也就相当完满了。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作为苦难根源的爱欲其实是充满快乐的,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尽管计帜英的青春年华--从小说的开始到结局都被注定了受难的特征,但在整个过程却如同爱欲的狂欢节。
也许荆歌并不过分专注“苦难”,他的小说叙事历来关注性格与命运构成的反差关系,苦难只是他的那些扭曲的故事和性格依托的特殊语境。那么看一看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苦难又是如何展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