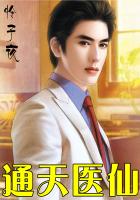梦醒了,夜更长了。
郭家唯倚墙坐在角落里,两只布满了血丝的眼睛如死人般盯着墙顶上幽暗的亮灯光。负责值夜班的是相貌堂堂身高足有一米九的吕铭启,而人们却叫他’大驴‘。另一位是满脸忠厚下暗藏奸诈的刘广城’流氓城‘。如若仅凭着外表,你定会为自己的阅历浅薄和以貌取人后悔以及的。昏暗的光线中一高一矮两个影子好似两头在磨房工作的驴来来去去地转着,不时也聊上几句。
大驴把他酷似低音炮的喉咙往下押了一个音节说:“兄弟困不困?扛不住就聊会儿,说说话好多了。官司打到哪儿了?”
流氓城小心地左右看到人睡熟了,轻声回到:“还早呢,刚他奶奶的检提一次,你算快到头了。你瞧我,哥哥······不是说你到头了,是熬到头了,让兄弟羡慕啊!”
大驴又气又笑地回到:“算你说对了,就是快到头喽,羡慕我,羡慕个毬!快上路的人了还不是得一天天熬,您在外面搂着妞喝大酒风流快活的时候我就在这儿受罪了。你要真羡慕我?哼哼·····你我换换?”
流氓城道:“谁怕谁啊,换就换。哎?!不行,你犯得啥事我还不知道呢?“
大驴轻蔑而不客气地说:”你那嘴跟那个似的就喷吧!我看你也没那个胆儿“
流氓城仍旧肉烂嘴不烂地说:”你这才叫说不着的话呢,你要是宰了人我也换?那我脑子才真叫进屎了。“
听到‘宰人’二字大驴脸部的肌肉好似触电般的颤了颤,一丝不易觉察的冷酷一掠而过,激动地说:”杀人,杀人新鲜吗?知道吗,恶有恶报,恶有恶报!那是他们找死!该死!”
大驴眼中涌动的杀气和怒不可恶的凶相让流氓城的后背一阵阵发冷。他脑子飞速地一转,故意用话挑逗大驴,说:”什么恶有恶报,你没听说过’修桥补路命不长,杀人放火活千年‘“
“你小子骂我?骂的还不带脏字是吧?”大驴显然是歪解了流氓城的用意。
流氓城忙补充道:“误会了,误会了哥,你是啥人我眼睛又不瞎?像你这么仗义实在的一个人肯定是被逼急了,没路了,才会····”流氓城变手掌为刀在大驴眼前比划了一个’杀‘的动作。流氓城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却已准确地击中了大驴的心结,更让大驴感到惊喜的是在里面竟能遇到这样一个难得的知己,于是他的话头儿也随之丰富起来了。
他说:“兄弟,还是你懂得哥哥的心,说句真心话,那天如果他们不是把我逼得没路了,我怎么下得去手呢?再咋说她也跟我睡了十年了,那可是三千多天呀!“
流氓城见大驴动了真情,心想:俗话说的好啊,名字有给起错的,外号没有起错的。大驴呀大驴,你丫绝对比驴还蠢。人家对你都那样了,你还下不去手。嘴上又是另一番话:“你说这个我绝对信,不是吹,兄弟混了这些年没学会别的本事就是看人看不错。兄弟见你第一眼就知道哥哥你指定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几句话把个大驴说的浑身通泰受用,他看着眼前这个相识恨晚的知心人,真想把自己压在心底的苦水统统倒出来。
流氓城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人不鬼说胡话的小人,他还有个偷窥别人的隐私癖好,一旦获得了某人的一些不可示人的事情,便会使出最卑劣的小人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胸有成竹的他估计再加把火就能将这个蠢货拿下,接着又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兄弟如有半句就叫我不得好死,再说咱哥俩萍水相逢我犯的着吗?兄弟长这么大看人还没看走过眼,我真是觉得哥哥你人仗义实在,咱哥俩也有缘才多说几句,如果换了那些`······哼哼·····”说着朝板上的人瞟了一眼。大驴的心一下子觉得热乎乎,流氓城的肺腑之言算是让体验了一把让人信任的自豪,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他。于是他轻轻地拍了拍流氓城的肩膀,每一下都充满了深切的感激。
两个人的话一字不落地传入了郭家唯的耳朵,内容虽然无趣,但用以它打发慢慢长夜的无聊与孤寂还算不错。
流氓城说:”大哥,打比咱们号吧,别瞧就十几号人,他奶奶的一百多个心眼儿。从早到晚那个劲儿,恨不得要把谁活埋了似的,啊呸,看一眼就知道丫的是什么变的。什么大说什么,偷个钱包硬说的跟抢了个银行似的,猥亵妇女非说自己是杀人进来的,什么玩意儿。不是吹牛逼的,真敢拿刀杀人的除了哥哥你还有谁?”
”嗯·····嗯·····'这一刻大驴觉自己是个’英雄‘,至少在他的这个兄弟眼里。
流氓城又故作崇拜状,道“别说杀人了,杀个鸡我都肝颤。哥,跟兄弟聊聊杀人是个啥感觉,是不是特爽?”
郭家唯边听心里边骂:这王八旦,真孙子!
别看大驴杀过人,可要问他那是种啥感觉,他真的是没想过,也不是不想,而是不愿想不敢想。现在,被流氓城将进了死胡同的他不敢想也得想想了。他像放电影似的在脑子里把个夜里的事捋了一遍,还强迫自己想象杀人的’爽‘快感。他的眼睛向往事找寻着仇恨,黑暗的前方正在变红,污浊的空气里仿佛充斥着血的腥味。心中期待的’爽‘快非但没有如期而至,却再次体验到了那个与死神交汇的夜晚带给他的的恐惧。如果灯光能在这一刻驱逐黑暗,流氓城面对的将是一张惊惧又惨白的脸。
大驴抬手抹去额头的冷汗,佯装镇定地看了流氓城一眼,那种被人崇拜的英雄感渐渐死灰复燃了。他暗自握紧双拳感觉自己正握着那把杀过人的刀。他挺直腰杆闷声‘嗡嗡’了几下,这样就可以呵退一直以来令他恼怒不堪的恐惧。也就能‘明正言顺’地以一个胜利者,一个英雄的姿态讲述自己的‘正义‘之举了。
渐入佳境的大驴眼中现在除了他自己已然什么都不存了,他确信已经找回了那个夜晚的自信。他十二分地享受除了自己一切都不存在的感觉,那才是在他梦中幻想了无数次的唯我独尊的感受。
正沉浸在‘一个英雄’的享受中的大驴被流氓城的呼唤声惊醒:“驴哥,驴哥!您别再折磨兄弟了,快讲讲,快讲讲吧,让我也长点见识。”大驴踟蹰片刻,那里逃的过流氓城的一双贼眼,他决定再将大驴一把,于是说:“怎么了驴哥,不方便还是看不起兄弟,不方便就算了,都是我这见什么都好奇的臭毛病,真是娘的没出气。”流氓城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还在脸上抽了一巴掌。大驴忙的一伸手这才制止了他继续抽下去,并且用几乎是命令又是关怀的口吻想流氓城说:“你这是打谁呢?这样以你后别叫我大哥。”流氓城心道: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让你也过回当大哥的瘾。在英雄和大哥两个角色中仍意犹未尽的大驴当然还要继续享受下去,他故作神秘地对自己唯一的兄弟说:“兄弟,我可就和你说,你可千万别······”流氓城拍着胸脯说:“驴哥,你说我听等于烂在我肚子里了”
然而大驴那里知道自己正在向流氓城为他精心设计的陷阱一步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