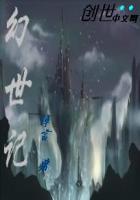方文欣是他前女友。
在与方文欣分开之后,程子怡在夜里依旧混迹于各个酒吧,携每日更新的女伴亮相,坐在一起玩牌,喝酒。
人与人的学常之处,有时候真的是找不出一丝带有新意的交流来,又或许交流是疲倦费神的事情,谁都不会真的关怀他人的不幸,个人尚来不及咀嚼个人的遭遇,这是为何人间之所以是人间。
程子怡和陌生女人调情,遇到中意的,就带回家,若没有遇到就叫鸡,不过多半都不需他费力,便有大把女人往身上贴。大陆从七十年代到今天不过四十年上下的时间,就走过了这般匪夷所思的社会进程,性压抑的时代早就过去,如今有钱男人总是不缺女人,哪管他长相?何况程子怡生就一副漂亮皮囊。他高兴时就扔一万块钞票给台柱舞女买一百个大花篮,摆满整个夜场,让别人几乎坐不下,营造阔气的快感如同女人的谄笑和酸软身体一样,都令他欣快发抖。
时间与排场都渐近尾声时,如果没有打架,他便醉酒开车带着女伴回家行欢,在黑暗街道把车开得一路飙驰,迅疾得像是坠落黑色悬崖的一颗石子,因为意识模糊所以可以任意赌博性命,包括他人的,这大概是没有希望的人最乐意的事情。
但时不时的,如此时刻他偶尔还会听见有声音在失意的深处对自己说:文欣走了,文欣走了。她回不来了。
他蹲在街边,我递给他一支烟,给他点燃,然后我也抽起,什么也不说,只顾着抽烟。
去年这个时候程子怡追去方文欣的宿舍,趴在楼下的铁栅栏上,像头发狂的狮子一样的喊,文欣,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楼道里的女生听见,纷纷对文欣侧目,或者在耳旁小声告诉她,下面有个人一直在喊你的名字要见你。
文欣淡淡的说,“我知道了。”
天黑的时候她还是下了楼去,程子怡见着她,便一把拉着她说话,一遍又一遍:原谅我,对不起,等等等等。
程子怡身着青色的合身休闲服装,这个漂亮的男人在文欣面前不停忏悔,身旁是素面朝天的普通大学生三两成群的走过,穿着廉价的普通恤衫,嘴上唠叨着食堂饭菜的价钱和味道,提着开水瓶,胡乱扎起的头发,容貌平庸无神,她们纷纷侧目,互相交头接耳不断猜测。
程子怡泪水诚恳,但文欣知道尽管他是真心舍不得,也不过就是仅仅止于真心舍不得,爱并不是如此,至少她需求的不同。
程子怡不肯放弃,说,“跟我去检查,我要你把孩子生下来。”
文欣说,“子怡,你走吧,孩子已经没了。”
程子怡一把就抓住她,几乎快要把她提了起来,说,“不可能,孩子肯定还在,你这么爱我,肯定舍不得。”
文欣一阵心凉,事到如今他仍然只说,“你这么爱我,肯定舍不得。”他心里仍然还是只有他自己,可是她连气都气不过来了,只能心如死灰的回答他,真的没有了。
不行,你******必须跟我走。
你弄痛我了,放手。
程子怡把她塞进车子,不由分说就开回家,一开门,文欣看见看见了家里突然多了很多她曾经喜欢的东西。她见了突然心里一阵刺痛的酸痛,但也仅仅一瞬,这不过是把戏,如同一切男人送的大把玫瑰,意义空洞,她静静的看着他,说,“子怡,孩子我已经做掉了,你醒醒吧,别闹了,我也不想再与你走下去了。”
她在他面前短暂的闭上了眼睛,想起的是自己一个人去学校附近的医院做有痛流产的情形。
之前曾经陪别人去做人流,看到她们全身麻醉之后失去知觉,张开双腿耷拉在手术台上,任人持各种器械深入,做完之后人事不省,劈着双腿软塌塌的躺在手术台上,狼狈至极,需要有人抱下手术台来。
文欣不要,她说,“我不能忍受这样狼狈,没有尊严,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这一面。”
她要体面,于是就需要忍受,心里铿锵有力的想着,这个孩子如何带着痛楚来到身体里,便应该如何带着痛楚离开,于是她咬着牙没有用麻药,惨叫几声,抓破了床单,终于把手术忍了下来。完事之后在手术室外面坐着休息了很久,冷汗湿透了衣服,只觉得眼前是黑暗的,她坐在空寂走廊,忽然很想祈祷。
但主并不在身边,她只觉得头脑中空旷干净,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一瘸一拐的离开了座位,花了身上最后十几块钱到超市买卫生巾和方便面,慢慢走回来,躺在学校宿舍的窄小铺位上,虚汗如雨。她极少回宿舍,同屋的女孩子们见她回来都新奇,你一句我一句的询问,你怎么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专业课老师点名很多次了?今天下午的课你还去不去……
方文欣只觉得这些声音在她耳边回响,她一个字都听不清,她又累又痛,说不出话,最终一声不吭的昏睡过去。
这其实是不久之前的事情。
子怡,她说,“我已经决定了,你也放下我。”
程子怡还是不让,他神神道道的又把她从家里拖出去架上了车,开着就去医院,把她带去医生那里,非要做超声波检查不可。
文欣知道拗不过他,又觉得疲倦无力,就顺从的躺在检查台上,医生做检查,弄了几下说,“神经病,孩子都没有,检查什么。”
程子怡呆在那里,文欣看着他凄楚神情,这光鲜四射的金玉之外也不过就是败絮其中,彼此霸占的欲望这样焦灼焚心,他与她都觉得这就是爱,她曾为着程子怡这一具光鲜皮囊辗转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是何时的事情?她竟无法清晰记起,她只明白,而今不再,从此不再。
你这下知道了,孩子我已经做掉了。
程子怡大闹,在病诊室失去控制,胡乱砸东西,医生叫来保安才制住他,把他们赶了出去,他像抓了一个布偶一样抓着她瘦弱窄小的肩,她更瘦了,身体像是快要消失一样单薄,程子怡剧烈摇晃,求她道,“文欣,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回来,我马上就娶你。”
文欣一滴眼泪都没有,此刻再有日升月落都不再明媚人心,她只是说,“子怡,你可知道希望这种东西放在你身上即是祸害,你还不够老,定不下来,但我也等不起你了。我还是想要幸福,我不想再做你的储备粮,身边女人青黄不接的时候才想起我,这些都给你说了这么多遍,我觉得恐怕你该懂的。”
去年那个时候他心里还是有这样巨大的信念:文欣会回来,这个感情陪衬他永远都不会失去。
然而如今,文欣还是离开了,程子怡这样悲伤的想着,狠狠的干着身下的一个鸡,她****得痛不可忍,大叫不止,他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出声。”
程子怡迅速一泄为快,疲惫而烦躁的把她赶下床,给了钞票便叫她快滚。
他又重新坐回寂静的夜里,房间黑暗,空如墓穴。
这个****超常旺盛的男人,过去在文欣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频繁的借泄欲为由,带形形色色的女人回家来上床,文欣渐渐习以为常,独自翘着二郎腿在隔壁看电视,任他在这边房间不停的做爱,她只要求说,“你们不要叫床。”
他于是常常按住女人的嘴,不允许其出声,有时他已经大醉,做完之后文欣还会替他付钱打发那些女人离开。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今晚他只是又一次说,原来文欣早就离开了、。
我一直觉得人若带有欠缺降临世上,一生走向就带有一种注定,生命的到来大约是唯一公平的事情,不论贵贱,该降生的人都该降生了,一如动物,但在人间,世事从来都是不公的,这是为何我们会感到痛苦,文欣的不幸,不知道是不是她的****。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能抚平一切,将心里好的或是坏的痕迹一刀刀刮去,只留下个面目模糊的疤痕。
从医学上来说,痛觉的丧失其实是一种病态,而且相当危险,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痛,那么他就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
所有的爱都可以生生掐掉,只要你足够绝望。
感情从来没有公平。
感情不是个好东西,它总让人流泪。
不爱也有不爱的好处,分开了,尽管遗憾,但也仅仅是遗憾而已。我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卑微,但是不可以在我爱的人面前低下头,不可以!夏虫不可以语冰,他永远没法了解我所在的那个世界。
有些东西就算在心里结了疤,仍然是不能触碰的。
其实我觉得,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等待也是徒劳。如果回头也看不见他,不如向前看,毕竟都柏林的风光那么好。
有些东西一旦碎了,总是千般弥补,也再也回不了当初的模样。
时间过去了,多深的伤都会结成一个面目模糊的痂,跟血肉长在一起,这个受伤的地方就会变得坚硬。
也许比较在乎的那个人永远是输家。。
有些最伤人的话往往出自最美丽的嘴。
爱情通常看起来全无道理,可是当你置身事外来看,凡事都有迹可寻。大多数人在人群中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灵魂,而也有一部分人则会爱上拥有自己渴望却缺失的那部分特质的人。我属于后者。
就算我不能够蜕变成像他一样雪白的天鹅,但至少,我不要一直做丑小鸭。
我站在尘土里渴望着云端的那个人。
理智明明让我远离他,感情偏偏背道而驰。
我在最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最美丽的青年,即使他将我视为洪水猛兽落荒而逃,即使从此沦为一个笑柄,但是我没有后悔。。
世事有时是多么无奈啊,假作真时真亦假,我爱的人就在我面前,可是他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从来不说假话。
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可能,可仍然会有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