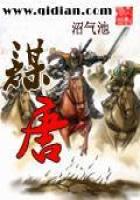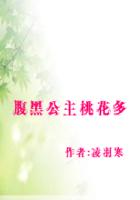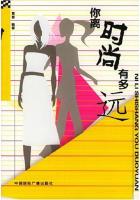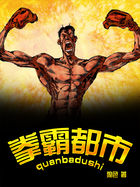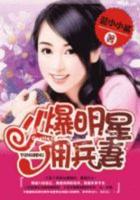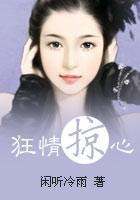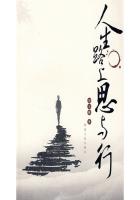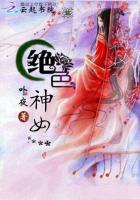然而在《李家庄的变迁》中,赵树理并没有表现外来的党组织对李家庄农村革命的领导,而是大量写小喜、春喜这些人是如何在太原投机钻营以及在农村对农民强取豪夺的。从第7节开始,小说的时代背景到了“七七事变”后,阶级斗争的主题和抗日斗争的主题交混在一起了,一直到小说结束,是在讲李家庄的村民怎样投入到了抗日战争和与李如珍等汉奸的斗争的故事。在社会时代的变化中,坏人李如珍等人的身份也发生变化。先是抗战初,日本人打过来,溃败的散兵在村子里乱抢东西,李如珍等人也不可避免,甚至李如珍都被孙殿英的部队绑了票。但后来在小喜的撺掇下,李如珍当了汉奸,又回到村子招引日本人残杀抗日农民,开始了对农民血腥地迫害,农村中你死我活的斗争才真正开始。抗战前,他们作为地主恶霸,尽管坏事做尽,却没有造成流血的后果,虽然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但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当他们变成汉奸杀人后,人们终于无法忍受,因此最后他的下场也是被群众活活地撕成了几大块,就文字描写来看是赵树理小说中最血腥的一个场面。当县长认为太残忍时,白狗说:“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人们这种仇恨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李如珍当汉奸杀了村里的乡亲,并不是阶级的原因。在小说中人们最最仇恨的是小喜,同样对他的最大仇恨是他当了汉奸,带日本人杀了好多村里的人。这样,铁锁等人和李如珍等之间的矛盾重心就由阶级斗争变成了村民和汉奸的民族斗争,李如珍等豪绅地主的身份变成汉奸身份,矛盾斗争激化,人们对李如珍等的仇恨中不光是阶级仇恨,更加上了民族主义的仇恨。
同样,在小说中还有两个人物不好放进阶级斗争理论中,一个是富顺昌杂货铺掌柜王安福老汉,一个是社首小毛。老掌柜王安福在村里来讲,他是一个小商人,在和小常交谈减租减息动员群众抗日时说自己放债“总共以现洋算不过放有四五千元”,这在当时农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从财产的占有来看是和李如珍等一样的大户人家了,同时他又见多识广,非常关心时局,也可算乡村里乡绅式的人物了。因此从阶级属性上讲,这样的人应是和农民为敌的,但实际上,王安福却处处替大伙着想,在春喜等人欺压霸占铁锁家产时,王安福尽力主持公道,但他人单势弱,孤掌难鸣,最终无可奈何。抗战爆发后,在为牺盟会抗日捐款中,他身上体现出了强烈的家—国意识,王安福老汉“虽说不是个十分有钱的户”,可是他对干部们说:“会里真有用钱的地方,尽我老汉的力量能捐多少捐多少!就破上我小铺交捐款!日本鬼子眼看就快来抄家来了,哪还说这点东西?眼睛珠子都快丢了,哪还说这几根眼睫毛?”他后来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全捐给抗日队伍。在小说第9节和第11节中,赵树理把主要的笔墨给了王安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在写王安福时是把他和李如珍对照起来写的,在整篇小说中,他们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这最主要的刻画王安福的单节中,赵树理对两者进行对比就更明显。一者是在村内斗争中完全站在普通村民这边的,在抗日运动中也完全站在村民一边的,做了开明绅士;
而另一者在村内斗争中是完全站在压迫普通村民的一面的,在后来的抗战中,更是做了汉奸。因此王安福便和李如珍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相互斗争的敌我矛盾,而这个变化的主要驱动是对待抗战的态度。在这样的表现中,人物的身份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阶级理论来区分就分不清楚了,而普通老百姓却是用最简单的标准把他们区分得一清二楚,即是农村的传统道德标准:“好人”与“坏人”。李如珍等原来就是村子里的恶霸,欺压普通老百姓,是“坏人”。小说一开始,李如珍和侄儿李耀唐(即春喜),欺负外姓人张铁锁,霸屋占地,甚至把铁锁一家人扫地出门。他们仰仗山西军阀,横行乡里,而到战时他们先要了解军阀对抗战的态度,再见风使舵,派春喜跑到县里终于打探清楚,军阀和县团长的意思是“只要孝子不要忠臣”的虚假抗张态度后,又开始欺压百姓。而当日本打过来占领了县城后,他们就变成了汉奸来欺压百姓。在这群人中,小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泼皮无赖,是个集大恶者,这种人没有任何操守,见风使舵,正是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在越混乱的社会中越能浑水摸鱼,欺压百姓,占尽便宜,而这才是人们最最痛恨的。这样的人会欺压任何自己可以欺压的人,因此在村中曾经也是有头有脸的王安福,在日本人得势后,首先成了小喜抢劫的对象。
因此,和普通村民一样,王安福同样和李如珍等人有深仇大恨,一是国恨,一是家仇。
另一个人物是小毛,他在村子中没有任何地位,只是跟着李如珍能占到些小便宜,如在处理村务时能吃上一份烙饼,吃上一口好饭,能在伺候李如珍后吸上李如珍吸后的几口烟灰,常常是“既做巫婆又做鬼”,成了李如珍的狗腿子。按说这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应是属于村民一边的,一起来斗争李如珍等人的,但实际上他却是李如珍等欺压村民的帮凶,他也不断地来回穿梭,当村民的力量壮大时,他也忏悔求饶悔过,一旦李如珍等卷土重来时,他又固态萌生,成了狗腿子。因此人们同样对他充满了仇恨,但与李如珍等不同,他并没有杀过村民,因此他最后的结局是大家只是让他赔了大家的损失,留他悔过。同样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是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所干坏事的程度轻重来对待的。这样的人物在赵树理后来的小说《灵泉洞》中又有表现,也有不同。《灵泉洞》中写道:“一听说杂毛狼又出了世,小胖他娘打了个寒颤。她说:‘娘呀!又该人家吃人了!’”杂毛狼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更没有李如珍那种大户人家的背景,他只是依附于有钱人的地痞流氓,却因平日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让老百姓担惊受怕。侵略者在乡村招募汉奸,别人不干,但杂毛狼素来“有奶便是娘”,全无道德廉耻,自然成了“积极分子”,“依靠力量”,也就更加耀武扬威。“战争造成生灵涂炭,但对小胖娘这样的普通农民来说,它的罪恶更在于侵略者摧毁了生活赖以维系的一套道德法则,黑白颠倒,老实善良的人要是落入‘杂毛狼’这一类人手里,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小说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描写是在忠奸善恶之间进行的,从而合情入理地揭示中国农民投身抗战的文化原因。”
在这里,革命的、阶级的斗争观念隐退,而传统道德观念去伪存真,作为民族精神象征,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的底蕴。
另外,《李家庄的变迁》中有大量的细节铺衍,这使一些批评者感觉小说显得杂乱无章,混沌不清,甚至有点文不对题。赵树理笔下的细节,仿佛信笔所至,像乡村的日子,一事一事又一事,由作者细细道来,密密麻麻织成一片。这些细节淹没了故事的经纬,冲淡了传统的套路。但细节的铺衍,结构的散漫,中心人物的不突出等,实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在散漫的叙事中展现出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结构方式,不以某个人物为中心,也不以某一矛盾事件为中心,而是以更为庞杂的空间或群体作为表现对象,即题目所标示的“李家庄的变迁”。也就是说,小说所表现的主体是“李家庄”这个社会空间或群体,而不是张铁锁或小常。现代小说家惯常采用的小说结构方式是以一个家族或一个主人公来表现社会变迁,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每一阶段的社会变迁不可能用一套社会理论来完全概括,每一阶段的社会变迁会在文学中留下历史烙印,这些烙印在文学中往往包含着比某一叙事理论本身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历史上许许多多问题在文学中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它们往往在文学叙事中变成了讲不清楚的东西,而对这样问题的叙事反比那些明朗的某一理论指导下的叙事更为重要,需要更为仔细地观察。赵树理小说中这种“散漫”的、不能被某种理论或某种叙事理论所规范的叙事,或是说从这种规范叙事中溢出的大量细节,反显出了当时社会复杂性,显出了赵树理小说的丰满性。
《李家庄的变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散漫”,不断受到批评,《三里湾》写成后赵树理又做了自我批评,对照革命现实主义的标准,将自己作品不符合的地方归纳为“三个缺点”:(1)重事轻人。人物描写不集中,更谈不上典型。(2)旧的多新的少。“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3)有多少写多少。对应该写,但“脑子里还没有的人和事就省略了”,比如“富农在农村中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之类”。
而且这些“缺点”,在他后来的作品,像社会上影响较大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中也没多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