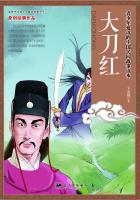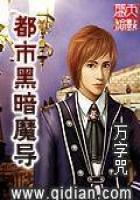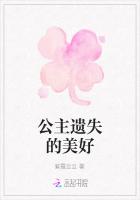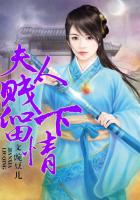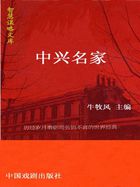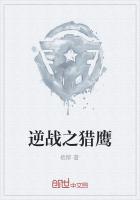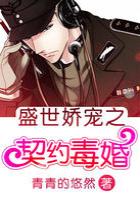这里有环境作用存在。在大家都在矫揉造作或不得不这样的环境里面,一个人不这样就象有点难乎为情,这就如在长袍马褂的社会里面一个人不好穿短打的一样。
因此我很羡慕作者,他是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活》,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他就象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株子大树子。这样的大树子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作者是这样,作品也会是这样。
或许有人会说我在夸大其辞,我不愿直辩。看惯庭园花木的人,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也会感觉生疏,或甚至厌恶的。这不单纯是文艺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意识的问题,这要关涉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发展。口舌之争有时是多的,有志者请耐心地多读两遍这样的作品,更耐心地再看三五年后的事实吧。
(《文萃》第49期,1946年9月26日)
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最初发表于1946年7月20日,刊于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编辑的大型文艺月刊《长城》创刊号上,后又载于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而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文章发表于1946年8月16日《文汇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发表于1946年9月26日出版的《文萃》上,两篇文章都后于周扬的文章。我们姑且不说郭沫若文章发表时是否看到了周扬的文章,单把这三篇文章放到一起时,可看出郭沫若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和周扬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极为不同。
郭沫若在《〈板话〉及其他》中说自己在火热的夏季花一天时间匆匆读完小二黑及李有才的故事,“这在我是好些年辰以来所没有的事。”他连用五个新字来表达他的喜悦感,但具体的“新”郭沫若却没有展开,而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中,郭沫若对赵树理小说的“新”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这样的大树子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为开创五四以来近代文学传统,并从其中成长起来的郭沫若从赵树理文学中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是小说艺术的冲击,是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形式、风格等给他的强烈印象。郭沫若一点都没有强调赵树理小说是对《讲话》精神的实践,没有先验式地把赵树理小说创作与毛泽东的《讲话》联系起来,也没直接采用阶级理论来分析小说中的农村斗争,并不认为赵树理小说是伟大理论指导下的伟大作品。郭沫若完全是从一个文艺批评者的眼光,用“自然自在”、“不受拘束”、“大大方方”的“原野”气息等非常具有文学特性的词来概括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点,认为小说体现着一种新鲜的艺术品质,这种批评显示出了赵树理小说当时给郭沫若这样的文艺批评家的真实感受。
郭沫若在两篇文章中表露出的都是赵树理小说给他的“新”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以前的文艺中没有的,也是文艺理论中不注意的东西。这是一种“原野”气息,还有“自由”的创作环境。赵树理小说中的这种“新”的、“原野”气息的感觉,我在后文有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此处谈谈郭沫若强调的“自由”的创作环境。
郭沫若在文章中反省自己创作与农民的差距,“我很羡慕作者,他是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这里“自由的环境”是指赵树理所感受到的农村世界和农村文化而言,赵树理的创作摆脱了五四文学的束缚,获得的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境界。首先是赵树理所承载的文化。赵树理虽然在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使他身上承载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同时对这种新文化的自觉反省,以及农村地域文化的影响,使他身上也有非常浓厚的乡村文化传统。赵树理的父亲是个民间艺人,赵树理从小就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技艺,也被熏陶出了土色土香的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他八岁就学会了上党梆子,十五岁学会大鼓板,他能一个人打动鼓、钹、锣、铉四样乐器,而且舌头大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至于说书、弹词等民间文艺形式,更是赵树理所从小接触和熟知的第一种文学。可以说,是地方戏剧和曲艺等民间艺术,给了他为文之初的艺术的营养,影响了他的创作的自由思想。其次是赵树理生活的农村环境。赵树理说“我生活在农村,中农家庭,父亲是给‘八音会’里拉弦。那时‘八音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赤农,五个儿子都没有娶过媳妇,都能打能唱,乐器就在他们家,每年冬季的夜里,和农忙的雨天,我们就常到他家里凑热闹。在不打不唱的时候,就没头没尾的漫谈。往往是俏皮话联成串,随时引起哄堂大笑,这便是我初级的语言学校”。赵树理尤其在他的小说《盘龙峪》中详细地描写过这样的情节,十二个青年的随意俏皮话,使小说第一章充满无限生机。同样在《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窑洞里大家的畅谈、老槐树下的聚会等,都显示了农村生活中的自由自在的状态。应该说是在农村自由自在的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里促生出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精神的自由自在,这种精神状态使赵树理小说产生出了这种“山野”的“气息”,这种充满生气、生机的气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赵树理自觉地对中国小说传统自由的现代转化。赵树理的小说在艺术来讲,并不是对五四新小说艺术的延续。中国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实现了一种现代小说的走向,这种新的现代小说观念在破除五四前小说观念束缚的同时,已为自己限定了一个新的框框,限制了人们以一种超越这种限制的眼光去看待小说创作,“还自以为这个框框里的自由是无限的”。赵树理的小说是对五四小说路向的自觉纠偏,是另一路向的现代小说,而这种意识让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越出了五四现代小说框框的束缚,在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接续中达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
同为作家,心有灵犀,再加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员主将,郭沫若比一般人更敏锐地发现了赵树理这位“文摊”作家对新文学的意义。赵树理没有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家的毛病,他不屑于混迹“文坛”,扎在“长袍马褂”的文人堆里讨生活,也不屑于“装腔作势”,好像不穿在理论和知识的“长袍马褂”里面“就有点难乎为情”。“赵树理没有被五四那种重视启蒙现代‘知识’的文学路向所禁锢,没有被建立在此基础上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束缚,而是对自己认可的乡土自足文化的自信使他以自己顽强的个性开辟他生活期间的‘自由的环境’,也使创作也‘得到了自由的开展’。”
更重要的是,赵树理的“文学观本身就是新颖的”,他的小说创作是“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自觉地从现代文学中摆脱出来”后自由自在的创作。
当然,把赵树理小说归结于一种纯粹的、未受政治“污染”的写作姿态,同把赵树理的小说归结为政治运作的结果一样,都是难以自圆其说。
周扬等人的评论的确是抓住了赵树理小说的一些独特性,如赵树理对农村社会变革的表现,赵树理小说“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对新人的塑造,语言的口语化等,进而论定赵树理小说创作和毛泽东《讲话》的关系等。
这些方面也的确是赵树理追求的,在“老百姓喜欢看”的同时还要在“政治上起作用”。但问题是这些论述更多是预先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出发的,是从赵树理小说在现实中发挥教育意义的角度出发的。当文学批评中艺术审美追求和现实功利性追求相远离甚至冲突时,文学现实功利性的强调便可能遮蔽甚至否定艺术的审美追求而占据主要地位或独一地位。郭沫若的批评却首先是从艺术审美感受的角度看到了赵树理小说的独特性、新颖性。
郭沫若的这种感觉同样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非常出名的作家孙犁身上出现,孙犁在《谈赵树理》中说“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敌后的著名抗日根据地,在炮火烽烟中,绽放了一枝奇异的花,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而进京后的不适应新环境的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从一样的角度看到了一样的特点,不能不让我们认为赵树理小说在除周扬为代表的对赵树理的评价的特点外,还应有一种一直没有被赵树理研究者重视的另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