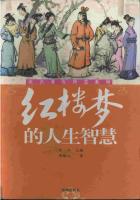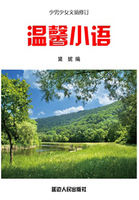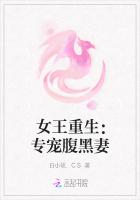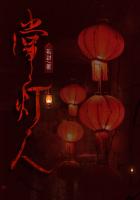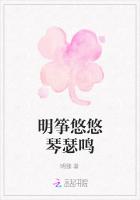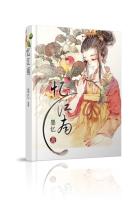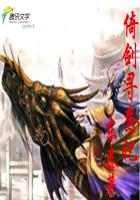对沉默者“实”利的坚守
———论赵树理对农民的关注视角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的杰出作家中,赵树理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土生土长”,“有着地道的农民气息”,“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彻底农民化了”。这种特殊性使赵树理在关注农村时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作家有了不同的视角,农村呈现出另一种光景。我们暂且放弃一下五四以来政治与艺术逐渐结合而成的“深刻”、“史诗”、“阶级性”等一系列新文学批评标准,而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从三晋文化的浸染与底层农民的体认来重新审视赵树理的乡村世界,我们可体味出别样的意味。
“三晋”即现在的山西地区,黄土高原东部,西邻黄河,大山环绕,地势相对封闭,多山少水,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如此的地理环境给当地的人民带来的首先是艰难的生存处境。赵树理出生的沁水县尉迟村,是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小山村,更能体现三晋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如此的生存困境决定了三晋乡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生活习性,重实利,重物质,而轻名利,轻精神。
“实”是三晋民性的核心,史籍多有记载,皆言其“敦厚质实”,其一是指为人的诚恳、质朴、厚“实”;其二是指为事方面的务“实”,“实”便成了三晋民性的核心。在这封闭与保守的社会中,农村与外界接触少,商贾交流也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而生存的困境迫使农民不得不注重实际利益,他们从与土地的联系中得出的经验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实干无以收获,也无以果腹。对他们来讲,吃饭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实实在在的生存温饱问题是最重要的,因此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聚集在能摸得着、能看得见的东西上,聚集在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解上,这使得人们无法把眼光放得远些,只能趋向于眼前的利益。尤其是在乡人的待神方面,他们是“为利而求神,无利便弃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故凡是与自己的生存和日常需要方面密切的,人们往往是有神必拜,以寻求庇护和免灾。出生于如此环境中的赵树理首先不得不受到这种三晋气息的浸染,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西度过的,以至于形成他固执的难以更改的求“实”的乡土习性。
辛亥革命后,山西仍处于闭塞落后的状态中,几乎隔绝着与外界的交流。阎锡山的专制独裁,近代中国社会的破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本来贫困的生活。赵树理家早已被贫困所困扰、挤压、驱使,又加他求学、祖父母延医治病、病故厚葬,赵家四处告贷。在如此困顿中长大的赵树理首先要解决的是现实生存的实际问题,对“实”利的追求成了他潜意识中不可抹去的追求。为了能找一个可以混饭吃的出路,不必再为失业发愁,在父亲再次借贷下,1925年夏,赵树理去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其目的不过是想谋一个微不足道的能够端稳的小学教员的饭碗。
在长治师范学校,赵树理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学潮风波的结果是他再一次地流落到社会的底层,生存的困境长达十年之久。赵树理曾一度化身郎中聊以糊口,后遭两度逮捕,一度进国民党开设的山西自新院,又先后当过几个小学的教员、一位杂牌军“上校参谋”的勤务员、省政府的小录事、河南开封一书铺的学徒,还曾在太原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的当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演员,直到1936年夏落脚长治乡村师范学校,他糊口的职业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家庭生活中,这期间又经历了女儿夭折,前妻病故,第二次娶亲,父亲为他“被捕”的疏通,赵家是雪上加霜,债台高筑。这种生存的困境一直到1937年赵树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自己的职业政治生涯,他才寻到一种生命归属感和生命安全感,个人的物质的生存困境虽有缓解,但这种经历使这位来自底层、农民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对“实”利有更加深刻的体认。
当赵树理在30年代辗转在省城太原时,面临现实生存境遇的无情逼迫,他最初所从事的文艺创作便更多的是为“稻粱谋”,是为了求生,求“实”利的现实需要便是其文艺创作的主要目的,所以赵树理在从事文艺创作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将文学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和依托,而是直到他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并在这一领域中显示出了才华与能力,被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发现并赏识,赵树理才开始了他自觉的文学创作。赵树理也曾夫子自道:“有些同志问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的?其实,我原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在旧社会,我做过小学教员,同时又是农民家庭出身,干过农活,对于种地的活路也还熟悉,那时家境不好,常常受高利贷的盘剥,因此我跟贫苦农民的感情上有些沟通,在他们中间有些根子;参加革命后,虽也做过编辑的工作,在这种岗位上,有时候就需要写点什么零星文章;
自从写了《小二黑结婚》后,领导上说,你会写,就写吧!以后我就脱离别的工作干起这一行来了。”
三晋文化中“实”的浸染,底层人生阅历中对“实”的体认,最初文艺创作中为生计的实践,这三者渐形成了赵树理重“实”利的价值观,以至他无论是此后的文艺创作,还是参加社会革命实践活动,都把这种“实”利的追寻当成了自己最高的价值取向。无论是赵树理自觉的“为农民”的文艺大众化努力,用小说对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反应,用小说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对很少有人问津的地方戏剧的改造,还是为农民现实的生存处境而奋不顾身地对权势说真话等,都展示出的是一位农民式的朴实的知识分子对农民“实”利倔强地歌与悲。这种“为农民实利”的价值标准的坚守使赵树理在风吹浪打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
正是在这种文艺价值观的基础上,赵树理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乡村生活时,很自然地把农民的“实”利问题作为了他文学关注的核心,而长治师范学校所接受的都市知识分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由于与农民“实”利相距太远而被边缘化。也正由此,在赵树理的笔下我们看到的农民就是现实生活中求“实”利的农民,无论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还是发生蜕变的年青一代农民,还是“农村新人的形象”。《小二黑结婚》中刘修德老汉阻碍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老汉给小二黑收养的童养媳是难民老李带来的一个“便宜”;《李有才板话》中,老秦给老杨“咕咚咕咚”磕头,行中国人认为的最大礼节,称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是因老杨为他重新划回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是在天灾人祸的生活困境中才会无赖式地“撒泼”;《富贵》中的富贵为了吃饱肚子维护生命延续不得不去偷窃。对他们而言,物质问题是他们存在最核心的问题,他们为物质而生,为物质而死,物质代表着他们心中最神圣的部分,物质是他们存在的本体而不是达到另外什么目标的跳板。而诱发农民发生蜕变的直接因素,也恰是这种物质的“实”利。《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当上干部不久就改换了穿戴,割柴、担水、锄地都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起主任来了;《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刚当上农会主席就分了地主刘锡元的房子、土地,和原来地主的狗腿子小旦混在一起,强逼着刚从地主强迫婚姻下挣脱出来的软英嫁给他儿子。而农村中的新人形象,他们从来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政治觉悟与“远大”的革命理想,在现实贫困的生活境遇中,他们的人生目标也十分简单,也非常务实。小二黑和小芹只是因个人的婚姻自由受到金旺兄弟的现实压迫后才与新政府发生了联系。《传家宝》、《孟祥英翻身记》的新媳妇是在占据了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地位后才在婆婆跟前挺起了腰板。《三里湾》中的灵芝在权衡有翼与玉生后,最终选择了“没文化”但却“创造了好多别人做不出来的成绩”的玉生。就连地主人物,固然具有许多革命语义所规定的许多反革命特征,但赵树理更注意揭示他们身上对“实”利的追逐性,即他们的反革命选择与其说是反革命立场的选择,不如说是对物质“实”利占有、囤积的一种心理性行为的表现。赵树理这种一开始写农民就已经把农民对“实”利的体验倾注到他的笔墨下的价值取向,使赵树理与农民之间没有距离,正是这种状态使赵树理真正能了解乡村世界的价值取向,这是生活在都市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体验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认为,人的生存需求是一个多层次需求所构成的组合体,高层次需求的出现是以低层次需求获得满足后,才能逐步走向尊严、爱情等高层次的需求提升,最终成为一个自我完善的人。
在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农民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的物质问题。在恶劣的生存困境中,他们的生存质量不会很高,精神需求更不会高,他们只有在掌握物质财富、使自身摆脱物质贫困的拘束和羁绊后才能真正走向新生,而这种追求便成为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始土壤。这种土壤孕育了现代历史中丰富的启蒙和革命话语欲望,“但来源于物质贫困的启蒙和革命话语并未在物质的意义上关注民间的启蒙和革命,民间的启蒙和革命内容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之外被悬搁了”。
鲁迅是五四一代启蒙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深受晚清一代启蒙大师的直接浸润与影响,他投向乡村的目光与情怀带着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当他弃医从文投身新文学运动,将自己的视线与笔墨投向乡村时,他把自己对乡村的目光放在乡人思想世界的变化与否上,他抱着“启蒙主义”的理想要“改良这人生”,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就有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七斤、爱姑、阿Q等一系列“麻木”、“迷信”又“愚昧”的农民角色,但这些农民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启蒙两不相干。在《故乡》中“我”震惊于闰土一声“老爷”的麻木,但结尾却又感悟到“我所谓的希望”与闰土的“偶像崇拜”具有同构性,“知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在《祝福》中,即使“我”真诚地抱着为祥林嫂着想的心情想对其有所帮助时,“我”仍无法做出符合祥林嫂需要的回答,甚至是带去适得其反的结果。面对启蒙的对象,启蒙的结果不是“我”——启蒙者对乡人启蒙的胜利,而是“我”不得不逃离乡村的失败。“我”渐渐对那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对乡人“麻木、愚昧”的历史性预设的批判意识产生深深的不安和怀疑,当瞥见“我”并不能真正进入乡村世界的黑洞时,除了像作品外的鲁迅那样“逃异的,走异路”,举家逃往知识分子汇集的都市以外别无选择,否则魏连殳和范爱农的命运就会悄然惠顾到自己的头上。
鲁迅的这种发现使他感受到现代文化与乡土社会、现代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以及现代中国与乡土中国之间的无关和隔膜。这种发现带来的是历史的悲凉感,“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
倘写下层人物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与无产者并无补助”,民众的启蒙只有“以俟将来”了。因此,鲁迅虽是开了中国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先河,以他独特的艺术方式对乡土中国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但也不得不承认,对乡村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一位逃离乡村的知识分子,他自己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精神守望。
农民身份出身的赵树理对底层农民的物质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才放弃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思想启蒙,而是强调对农民“实”利的重视。赵树理在建国前夕归结自己创作中的中心问题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变革中,是否得到真实的利益”,也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实际地给中国农民带来好处”,这种为农民“实”利的价值标准使他主动与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亲和,也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基点。由此可见,赵树理虽继承了鲁迅开创的对农村、农民生活的现代文学表现,但同时呈现出与鲁迅异样的特色。在关注农村的视角上,赵树理对农民“实”利的坚守是现实关注的,而鲁迅对“病态社会”中“农民的精神病苦”的关注则是历史预设的。鲁迅认识到自己无法启蒙闰土、祥林嫂等人后“逃异地,走异路”,逃往知识分子聚集的都市。而赵树理没有这样的自觉,求“实”的价值取向孕育出他对“实”坚守的同时,也使他染上了固执与倔强,不去“逃亡”的赵树理,坚守着农民的“实”利,这种“为农民实利”的价值坚守使赵树理在风吹浪打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1962年大连会议上赵树理对农村中实际情况的反映,变成了在“文革”前夜中国文坛上知识分子最凄美的“天鹅绝唱”。赵树理虽然明白,对“实”利的追求是农民自身摆脱物质贫困的拘束和羁绊,走向新生的核心问题,这种追求带来的斗争将成为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始土壤,但他却没明白,革命斗争在另一方面又同时在不断地强调非“实”利的思想、意识,在不断地突出心灵的伟大性、道义性、合法性,并一再压抑对物质的欲望,物质“实”利又成了革命须小心面对的禁忌之物。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赵树理仍在“为农民的实利”上下奔波时,迎接他的是一系列的厄运,是由《说说唱唱》上发表《金锁》带来的检讨,降职,是1959年的大批判,最终于1964年被调出了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