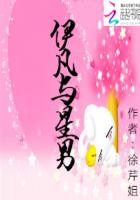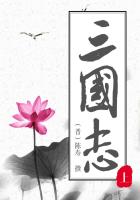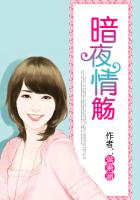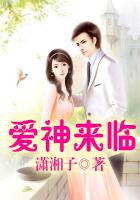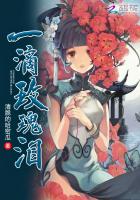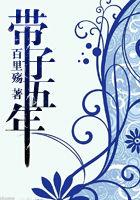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从小就是个“戏迷”,终生喜欢上党干梆戏,他对导演、音乐设计、舞美设计都作过研究,并且有独到的见解,他还是个热情的剧作家、评论家。“据《赵树理全集》,从1939年至1966年,赵树理创作改编的大小剧本有13个。同时,从1940年到1965年,赵树理共写文艺评论115篇,其中,关于戏曲的文艺评论就有25篇之多,这在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可以说,地方戏剧和曲艺,给了他最初文学创作的艺术营养,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思想。张仁义、栗守田在《赵树理同志与上党戏》一文讲到赵树理少年时代酷爱上党梆子的几个动人的故事,其一说道:
尉迟村七十多岁的老农吕培信,在十多岁时的一个春天,在自己的“窑背上”谷子地锄小苗,忽听见塄上有人唱“干梆戏”,虽然嗓音不大优美,可是吼得还怪响呢。同时,有个人念着“工尺谱”给他伴奏。吕培信知道,上边是双全老汉的地,准是他父子俩休息时候高兴呢。本来这也没啥看的,可是,他还是爬上去了。哟!真是。在一棵柿树下,赵树理“推”着“三把”,唱着“随父帅镇边关淄川罗成”的台词;他父亲双全老汉靠柿树坐着,歪着脑袋,拍着大腿,“工六五,上五六”地哼着,真有意思。
赵树理小说《盘龙峪》第一章中,在十二个农村青年兄弟结拜时,就有唱上党梆子的描写,在《李有才板话》中介绍李有才的描写中,也写到了李有才扮演焦光普的清唱,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节,六个放牛的孩子在山坡上玩唱戏,赵树理在多篇小说中也提到农民观看戏剧的热情。这种唱戏行为到底给赵树理的小说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当时农村,唱戏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敬神娱神,期望人身平安和庄稼风调雨顺等;一是自娱自乐,通过唱戏行为达到自己精神的愉悦,以此来消解物质困境和所受压迫之苦,通过唱戏行为达到暂时心灵的自由飞扬。我认为赵树理主要是从后一方面来写唱戏行为和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唱戏行为就是农民单纯的自娱自乐。在《盘龙峪》(第一章)中,十二个二十岁左右的农家小伙敬神结拜,之后就有人不等“邀神”的人来急着要唱戏,“要不是图唱戏的话,我磕了头就走了”,“大家因为要唱戏,吃得很快。不等大家吃完,小松却早把乐器安排好了”,这就马上开始进入各自的角色了,唱了《精忠传》,又唱吕布戏貂蝉的戏,“这出戏完了鸡就叫了”,这才一哄而散,“出到院子里,看见已偏了西的月亮”。在这样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农家小伙对唱戏的痴迷。而在《李有才板话》中写到,正月里李有才唱戏吸引邻村的一小伙上门请教,五十多岁的“有才见他说起唱戏,劲上来了,就不客气地讲起来。他讲:‘这焦光普,虽说是个丑,可是个大角色,唱就得唱出劲来!’说着就举起他的旱烟袋算马鞭子,下边虽然坐着,上边就轮打起来,一边轮着一边道:‘一出场:当当当当当令x令当令x令……
当今x各拉打打当!’”又是一种痴迷。
《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描写是:
平常来这里放牛的孩子们本来要比这天多,因为这一天村子里给关老爷唱戏,给自己放牛的孩子们都跟他们的爹娘商量好了,要在家里等着看戏,只有他们七个人是给别人放,东家不放话,白天的戏他们是看不上的。
他们每次把牛赶到坪上,先要商量玩什么。往常玩的样数很多———掏野雀、放垒石、捅酸枣、捏泥人、抓子、跳鞋、成方……这一天,商量了一下,小囤提出个新玩意。他说:“咱们唱戏吧?兔子们都在家里等看戏啦。咱们看不上,咱们也会自己唱!”
“对!可以!”七嘴八舌都答应着。
小管问:“咱们唱什么戏?”
小胖说:“咱们唱打仗戏!”
大家都赞成了,就唱打仗戏。他们各人都去找自己的打扮和家伙(作者按:家伙,就是乐器),大家都找了些有蔓的草,这些草上面有的长着黄花花,有的长着红蛋蛋,盘起来戴在头上,连起来披在身上当盔甲;又在坡上削了些野桃条,在老刘地里也削了些被牛吃了穗的高粱秆当枪刀。二和管分拨人:自己算罗成,叫小囤算张飞,小胖、小管算罗成的兵,铁则、鱼则算张飞的兵。
满囤说:“我算谁?”
二和看了一下,两方面都给他补不上名,便向他说:“你打家伙吧!”
戏开了,满囤用两根放牛棍在地上乱打,嘴念着“冬仓冬仓。……”
六个人在一腿深的青草上打开了。他们起先还画个方圈子算戏台,后来乱打起来,就占了二三亩大一块,把脚底下的草踏得横三竖四满地乱倒。
好一番唱戏,多么自由自在而又快乐的童年啊!我举这三篇小说中的唱戏描写是想说明在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中,几乎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痴迷看戏、唱戏,而赵树理对戏曲的痴迷正是如此,无论是童年时,还是青年时,还是中年、老年时。对不熟悉戏曲的人来说,在看戏唱戏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能把这样一群人吸引得如此着迷呢?
我们还是先从《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孩子们的唱戏说起,小说中这群孩子在野地里唱戏的身姿非常适宜从生命自由需要的角度去分析。孩子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开始唱戏,是一种游戏娱乐,完全是一种无拘无束下的游戏,因此他们很快沉入了一种近乎忘我的境界,“他们起先还划了个方圈子算戏台,后来乱打起来,就占了二三亩大一块,把脚底下的草踏得横三竖四满地乱倒。”“满囤在开戏时候还给他们打家伙,赶到他们乱打起来就只顾看,顾不上打,后来小胖打了鱼则一桃条,回头就跑,鱼则挺着一根高粱秆随后追赶,张飞和罗成的主将也叫不住,他们一直跑往坪后的林里去了。满囤见他们越唱越不象戏,连看也不看他们了,背过脸来朝着坪下面,看沟里的水。”戏台不管了,打的乐器也不管,更不管戏剧情节,只是自顾自地打玩起来了。在这种忘我的境况中,这儿原本的戏对他们也没有了任何约束,原先的戏里的人物、故事,只是他们开始玩打的一种方式,一旦开始玩打,这种方式就再也无法限制他们了,呈现出的只是孩子们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种孩童天性中对生命自由自在状态的呈现更能够体现出审美的原初意义。这样的细节我想也是赵树理对小时候玩得最高兴时光的一种回忆,也是最自得其乐的回忆。一般人在成年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更多是一种幸福快乐的回忆,是较少回忆到不幸和痛苦的,当然也有些东西会留在童年的记忆中成为我们的精神创伤。但当我们回忆这段时期时,更愿意回忆美好的情节。如鲁迅在他的《故乡》中对自己和闰土生活的回忆,在《社戏》中对夜晚划船去看戏和回来吃玉米豆的回忆,还有对百草园的回忆,在鲁迅的童年回忆中,大多数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是金色的。
大多数成年人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都有这种情怀。当然这篇小说唱戏后的故事,不再是孩子视角,而是用成人的、阶级的视角来表现孩子之间的不平等与受欺凌,在后面的描写中,童年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感受很快就没有了,有的是成年人的对那段生活感受到的压迫的愤懑。
在对赵树理小说的评论中,傅雷的《评〈三里湾〉》是一篇重要文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大多数批评家从政治观点评价赵树理小说时,傅雷却能从艺术感受出发评价赵树理小说,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如同40年代郭沫若对赵树理小说的评论。我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在这篇评论中,傅雷非常独特地提到了赵树理对儿童形象的表现,他说:“赵树理同志还是一个描写儿童的能手。他的《刘二和与王继圣》,以及在《三里湾》中略一露面的大胜、十成和玲玲三个孩子,都是最优美最动人的儿童画像。”
可能自有赵树理研究以来,从未有人注意过这个方面。傅雷并不熟悉赵树理,而且写赵树理创作的评论文章只有这一篇,这儿毫不吝惜地给予“最优美最动人”的赞词,连用两个“最”字,自是赵树理小说中儿童的形象给傅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感触。“最优美最动人的儿童画像”具体指什么呢?我想就是每个人对童年生活中自由自在生命状态的怀念,而这种状态是随着每个人的渐渐长大而失去了的一种生命状态,这种渐渐失去的生命状态成了每个成年人生命中想追求实现的梦想,实际也是整个人类永恒的追求梦想,只不过不同的人追求这种生命状态时所借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赵树理的小说世界中,农村人便是用看戏、唱戏的方式去追求这种梦想中的生命自由自在的状态。在农民的心目中,他们为之欢跃的唱大戏,主要不是什么为“艺术”,而是为了生命愉悦的宣泄,为了追求生命存在的自由自在,甚至也可以说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忘我的状态,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种狂欢仪式从本质上说是长期积累而成的精神渴求的爆发,是漫长时间的身心煎熬与偶尔精神自由的爆发。因此赵树理笔下的孩童、那些青年、那些李有才一样的老农,更有赵树理本人,对戏曲的喜爱其实都是具有超越现实而最求终极自由理想的色彩的,在戏的氛围里,他们解除了各种现实规范的约束,自由地展开想象,重新寻觅一度丧失的和谐自主的本性,获得了短暂的无羁和瞬间的自由自在。
看戏、唱戏不仅在满足着人们自娱自乐的需要,而且也给农民们构建了一种所谓的类似于“公共空间”的乡村社会,在这个类似的公共空间中,观众也在实现着自我身份的确认。如同旧中国城市的茶馆一样,在农村也有许多这样的大众活动空间,而参与人数最多的便要算戏场了。一般大一些的村庄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只要喜欢的人都可以参加,在大家共同的唱戏、演戏、交流、编排、观看中,大家被联系到了每人都可参与的一个文化公共空间中了。在这儿,戏剧的创作者、表演者、观看者、批评者都可以在这一空间中自由存在。他们在参与这个空间的活动中寻找到和自己有共同文化喜好的人,他们不再是单独存在者,而是共同寻找到了精神皈依和精神休憩的一方天地。在唱戏所营构的这个类似的“公共空间”里,戏曲带给了人们一种置身于传统的“家园”的感觉,而获得了自由自适的归依感。十一二岁的少年,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五十多岁老人、赵树理式的人物终生那样痴迷于戏曲,我想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吧。
也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理解农民听、传李有才的快板时产生的快乐效应。小说中的快板就如同戏剧中的念白唱词,农民以唱戏的方式说板话,表达了他们对村庄权威的不满乃至抗争,而当阎恒元垮台后,阎家山的村民们更是满村高唱“干梆戏”,以此种方式来宣泄他们内心获得的某种自由感和身份的确认感。
戏曲中的自由自在精神既包含有生命对自由本身的渴望,又包含有民众生存的自在逻辑。这种自在逻辑不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同时也体现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戏曲创作中。唱戏的过程也是演唱者自由创造的过程,而编写戏剧的过程就更是这种自由精神追求的一种外化,这显然要求创造者必须要有自由自在的心灵。在戏曲的创作中,戏剧的自由存在形式和自为发展的状态以及由此对创造者提供的审美自由空间极大地影响了创造者的自由意念,赵树理正是在这一“自由”、“自为”的戏曲审美氛围中,在不知不觉中培植了自己的自由自在的审美情趣并激起自由的审美创造能力。
除了怡人性情的地方戏曲,还有游走四方的艺人说书,流行于田间炕头的板话,出现在人们调侃之间的“顺口溜”等创作,给予了赵树理一种极自然的陶冶。在自由自在的审美创造和接受的氛围中,在创造者与接受者的非功利性的对应契合中,赵树理逐渐把自己的感觉和追求的这种自由的愉悦渗进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建构他眼中的世界,他要摆脱现代小说所规范的各种条条框框,于是便形成了不同于五四现代小说审美规范的创作意念。汪曾祺说:“赵树理最可赞处,是他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了一份好情趣。”
同样也可以说,赵树理的创作最可赞处,也是“他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写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艺术世界。
赵树理曾经与杰克?贝尔登交谈时说道,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的书没啥意思。抗战前,作家们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这种作家对于描写在我们的农民中所进行的革命是不感兴趣的。我若请这种人写政治性的书,他们就很不高兴,觉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从前我却办不到”。赵树理感觉到了自己写作的自由,这不光包括题材选择的自由,更应包括作者驾驭材料、结构小说的自由,这两方面的自由使赵树理的写作能够跃出现代文学或是古代文学的叙事限制,实现他自由自在创作的理想。当然,这种写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他小说中的这种自由灵气的东西不得不消退了。我想这就是最初郭沫若读到赵树理小说时给他强烈“新颖”感的主要原因,郭沫若说赵树理的小说“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这也就是日本学生冈本庸子在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感受到的:“我在读《李家庄的变迁》的时候,不禁对小常、铁锁这些人物产生了羡慕之情。他们生活在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