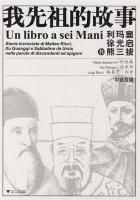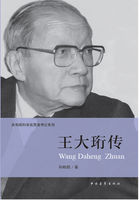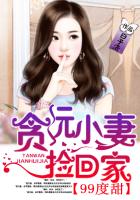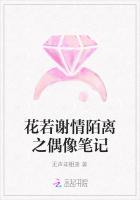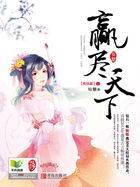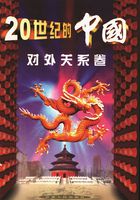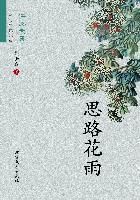军队的其他人不同。据张知行回忆,冯玉祥练兵时有8个特点:1.注重官兵的体力锻练。“它不像其它军队仅以挑出一部分官兵进行器械操的专业练习,而是做为全军官兵首要的锻练项目”。2.注重射击教育。3.注重战斗教练。为使识字不多的士兵易学易记,把操典、射击教范和筑城教范中的主要部分编成“战斗动作歌”及“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4.注重劈刺教练。即在体力锻练的基础上,注重同敌人肉搏突击的锻炼。5.注重夜间教育。6.注重耐热、耐寒、耐风雨的锻炼。7.注重爱国爱民教育。8.注重士兵的文化教育。《冯玉祥在陕西》,第123页。通过上述措施,冯玉祥所率部队的军容军纪大为改观。二是改编陕西地方军队。在地方实力派军队中,胡景翼部势力最大。
胡景翼(1892年—1925年),陕西富平人,字笠僧,又作励生、丽生。早年入西安健本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在陕西举兵响应,任第一标标统。民国后赴日本留学,1914年回国,在陕西地方军陈树藩部下先后任营长、团长等职。1917年12月组织靖国军,为靖国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了解到冯玉祥是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后,胡景翼即刻写信给冯,表示只要冯玉祥“能带着他们救国救民,任何办法都可以接受”。冯对胡的态度表示欢迎和理解。同时,鉴于阎相文杀郭坚之后,曾引起陕西境内地方人士的疑惧,及遭致地方部分上层人物的非难,因此,冯玉祥放弃用武力肃清的计划,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办法。冯玉祥派人多次与胡景翼联络,商议如何改编陕西地方军队之事。冯和胡二人互交金兰,结为兄弟。在改编靖国军的问题上,冯玉祥、胡景翼极为慎重。因为,靖国军是陕西人民在国民党人组织发动下,于1917年护法战争中诞生的一支义军,有着光荣传统和艰难历程,许多陕西革命党人和地方将领对其有着深厚感情。在改编问题上,胡景翼和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政见不一,明显分歧,但他们的私谊很深。尤其是对于右任的才识和为人,胡景翼钦佩至深,冯玉祥也极为推崇。冯、胡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于右任,请他为改编靖国军出谋划策,而于右任的耿直、倔强也是闻名于世。于右任非但不同意改编靖国军,甚至连冯玉祥为他安排担任陕西省自治筹备会会长一职,也坚辞不就。冯再次提议北京政府,委任于右任为陕西林垦督办,外加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职及一等文虎章,于非但不接受,甚至躲起来,冯玉祥仰慕于右任的人品和才学,只好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允许于右任出走离陕。胡景翼于1921年9月18日在陕西三原县召集周围15县民众代表开会,“当众宣布靖国军树帜缘起及应取消之理由”,并于9月25日“通电取消靖国军名义”。冯即把胡部改编为陕军第一师。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44页。10月8日,冯玉祥电请北京,拟请任命胡景翼为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至此,陕西地方势力中最大的一支部队被冯玉祥改编。对其他的地方部队,冯玉祥也用请地方人士从中周旋,分头与各首领接洽,予以改编的办法,实现了军事统一。但对陈树藩残部则仍采用武力进剿的方式。冯委任原陕西地方实力派将领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并令吴向陕南进军,追剿陈树藩残部。12月初攻克陕南,陈残部逃入四川,陈本人则只身逃往上海。
再次,选贤任能,广征博采,启用了一批治省治县的优秀人才。经过审慎考虑,对西安周围各县地方政权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了一批有德有识之士。委任薛笃弼为长安县知事,邓鉴三为临潼县知事,任右民为渭南县知事。这几位都是在地方为官多年且清正廉洁之士,深受地方人士欢迎。薛调任陕西财政厅厅长后,邓调任长安知事。邓为官多年,一向清正廉洁,除了一个衣箱外,再无他物。当冯玉祥离开陕西时,邓随冯离任。临行时,长安县父老百姓惜别灞桥,“扶老携幼,数以万计。邓乘洋车出城,并有诗云:‘一辆洋车一蒲扇,清风两袖去长安’”。在选贤用能方面,冯玉祥还大胆启用了一批陕西籍地力人士,先后有“二李、二郭、二宋,还有一位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仲特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冯玉祥认为,“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决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是民国初年曾任陕西省省长的宋联奎先生,品学兼高,为人尤为澹泊。此外,还有两位牧师,其中蒲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西安创办圣公会,任会长兼圣公会中学校长。冯玉祥于1913年驻节湖南常德时开始信奉基督教,因同为教友,故常请浦化人为官兵“讲道”。浦化人聪明干练,且口才颇佳,甚为冯所器重。自西安后,浦化人被冯邀为座上宾达6年之久。
他跟随冯玉祥参加直奉战争,********后随同冯赴苏考察,北伐战争中协助冯玉祥负责工运工作。经过各路人士的鼎力协助,冯玉祥这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开始能够在陕西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西北大省施展宏图大略了。
又次,改设督军署,树立新形象。做为北洋军阀体系中的一员,冯玉祥早就不满军阀政客及达官贵人们的奢侈之风,他就任督军后,首先要解决督军署的住房问题。原来的督军署设在西安皇城内,乃西安城中最为显赫的地带,深宅大院,重门叠户,雕梁画栋,气派十足。庚子年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为躲避八国联军而西逃时,曾以此为行宫。因此,虽为一幢旧建筑,但皇家气派十分浓厚,因而历任督军、将军等军政首脑都愿久驻此地。但冯玉祥却极看不惯这种腐朽的封建气息。
同时,督署设在皇城中心,城内无法驻扎军队。这样,督军住进督署,自然与部队远离,出身行伍的冯玉祥自然不愿与士兵隔离。为此,冯玉祥亲自在西安城内选址,他选中城东北角的一块空地,即在此动工修建新督军署。
修建新督军署需要一笔资金,而陕西地方财政十分拮据,难以支付这庞大的开支。冯玉祥想出办法,一是新督军署按简易军营模式修建,二是借用旧有材料修建。他命令将旧督署的几座旧房拆除,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新督军署的砖木材料,动员部下官兵为人工,仅雇了两名泥瓦匠当指挥。修建新督署的工程开工后,冯玉祥当大工头,卫队营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冯和士兵们每日推着小车,在炎炎烈日之下,搬运砖石。
冯玉祥少年从军,甲午战争前夕,15岁的冯玉祥就曾跟随父亲所在的清末北洋军队在天津大沽修筑炮台,炮台前后修筑两年,冯玉祥对建筑工地的劳作也颇为谙熟。因而,此次修筑新督军署,虽说资金紧缺,但冯玉祥在工地上也算得上得心应手。两个月内,空地上已竖起200间房子。左右各16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西边为各科办公室。新督军署虽没有皇家气派,不那么豪华,但却具有军营般的威严,冯玉祥可以每日清晨,亲自赴操场督练部队。只要能够和士兵在一起,冯玉祥心里就踏实了,而且新督署光线和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十分实用,冯玉祥对此最为满意。新督军署的修建共耗费5000元,这些钱并不是由省库支付,而是用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案犯的罚款,也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
治理陕西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陕西局面初定。而后冯玉祥开始思考陕西的地方治理。他决心大干一场,在西北一隅实现其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
禁种鸦片,是冯玉祥督陕期间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成的麻醉毒品,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因它具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进口。
17世纪,吸食鸦片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灯火吸食。吸食鸦片者,极易上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颜色枯赢,奄奄若病夫初起”。《鸦片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98页。几百年来,鸦片一直毒害着人类。自19世纪以来,围绕着禁烟问题,中华民族同西方列强曾展开了十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在这场斗争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鸦片战争后,鸦片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清廷腐败,内外忧患之下,禁烟问题时起时伏,导致流传甚广,毒害益深。烟毒之祸害,其根源无非有二,一是洋烟的大量输入,二是土烟的广泛种植。清末政府的政策中“寓禁于征”的作法,遂使得土烟种植放开,其害也遍及海内。在国人均可种植鸦片时,西北首当其冲。陕、甘一带土烟产量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王劲:《甘宁青民国人物》,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页。
据1906年统计,甘肃的土烟总产量居全国第五
位,人均占有量居第二位。陕西亦和甘肃一样,山区民间广种烟土。民国后,政府虽命令严禁鸦片,但一些地方官吏以地方财税主要来源鸦片为由,不断变换手法长期发“鸦片财”。这在西北尤甚。他们借口“寓禁于征”,设土药、官膏、征稽、督察等机构,一面高额征税,一面借漏税以便没收。民间存的土烟,逐渐流入官府手中。然后他们凭借权力,贩毒走私,中饱私囊。除在省内销售外,还贩运至京、津一带,甚至一些地方官吏,用烟土馈赠北京权贵。
冯玉祥发现,陕西一些投机商人受巨额利润相诱,从外地,尤其是沿海一带运来鸦片,官府只设卡收税,谓之“验票税”。在只有“禁种”而不禁运、禁售的情况下,那些所谓禁烟巡缉队,也就名存实亡。民间吸食鸦片之风有增无减,沉溺于烟榻上的不仅有平民百姓,而且上至官府,下至商户,吸食者不乏其人。冯玉祥在陕西十分赏识并较早启用的陕南镇守使吴新田便是其中一例。吴新田系陆军大学的高材生,“除了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冯玉祥曾多次劝阻其贩烟,并将陕西一位美国神父研种的苹果转赠于他,希望吴在陕南大力倡导栽种苹果而禁绝种植鸦片,并期待着他把大烟戒掉,恢复精力和体力。而吴新田非但不听劝告,“到后来终天在床上,守着烟灯,放下帐子,日夜地喷云吐雾,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饭拉屎亦在床上行之。”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48页。
镇守一方的将军况且如此,更何况士农工商及普通百姓呢?可见陕西各地鸦片的泛滥程度,也可以想象到在这里禁烟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