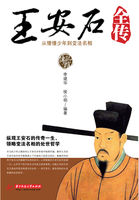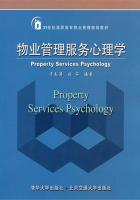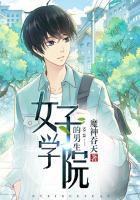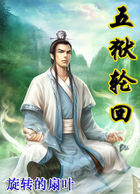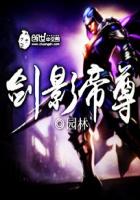并于9月23日,向驻山东青岛的德国海军发动进攻。
日、德在中国领土交战,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领土的侵略蹂躏。日军在击败德军攻占青岛后,俨然以战胜国自居,成为新的“主人”,并在此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抢劫财物,霸占民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在进攻山东的同时,日本还筹划另一个更大的阴谋,那就是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旨在使中国沦为其附属国的狰狞面目。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
2.要求东北的南半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4.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湖州间的铁路建造权,允许日本在福建省筹办铁路、矿山、建筑、船厂、海港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代表在怀仁堂递交“二十一条”时,对袁世凯软硬兼施,“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六,第91页。
当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之时,袁世凯则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袁本人“轮流召集各省旅师长以上武人探听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同时,策动舆论,鼓吹帝制,下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大礼。并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登天坛顶礼膜拜,重演封建时代“君权神授”以“天意”压“民意”的把戏。教育部则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宪法草案》
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时之间,尊孔读经的逆流遍及全国。
这股逆流的出现,与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分不开,首先是文化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帝国主义文化和旧中国的半封建文化本为一对孪生兄弟。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受聘为孔教会顾问,英国威海卫行署长官庄士敦喧嚷“能使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沙俄贵族盖沙令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这些无疑给袁世凯复辟帝制打了一针兴奋剂。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7页。
其次,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日本不仅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同时,派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担任袁世凯的顾问,作为帝制的策划者之一。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直接向袁世凯表示了他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意见。美国人古德诺,对于帝制的极大贡献则是他于1915年8月发表了一篇为袁世凯所需要的《共和与君主论》的论文,从理论上说明中国“民智低下之国……绝无政治智慧。……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杂志社,1936年。第163页。
袁世凯则经常以古著赠人。
名为征求意见,实为扩大影响。美国还借给袁世凯五六千万美元,这很明显是有着政治借款与投资利益的双重目的。
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的消息,不能不使冯玉祥感到十分焦虑。在此种形势下,中国将何去何从?他个人的前途将会怎样?是他日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冯玉祥认为,此时此刻,对军队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十分重要。要使部下明确当兵入伍的目的是什么?驻兵汉中时,冯“讲习武事,不稍松懈”,为提高士兵知识水平,尤其是精神,希望士兵能为国牺牲,编了一本《军人精神》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传统道德、基督教义和古代爱国故事溶为一体,以此来感化官兵、维系团结和提高战斗力。这本书分为三节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学习等内容。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自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着重强调军纪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明确提出“干犯军纪,为爱国军人奇耻大辱”。《冯玉祥自传》,第24页。每日早上阅操时,冯玉祥都向士兵提问,“为何要当兵?”部下答道:“保国卫民,捍御外侮。”
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他就是用这种精神来提示部下,军队绝
不能成为军阀专制的工具,军人应首先以国家安危为天职,以此来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带来的消极影响。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被报刊披露后,国人为之震惊,冯玉祥无不感到“周身的血液立即沸腾”。
“虽欲尽力控制,但我20余年来的军人生活,正造成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静不下来,甚至几天连饭都不能下咽。”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84页。
冯玉祥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深切的感受。甲午战争前,他跟随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前后两年。当时就立志:“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绝不许从我手里让日本人夺去!”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而庚子年在保定府等地亲眼目睹日本人
惨杀中国人的情景,以及《辛丑条约》签订后,拆除大沽炮台的经历。这一系列事实无不激发他早年的爱国御侮思想。因此,“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来,这股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油然而生。同时,更加坚定了他的两个信念:一是要同国内军阀恶势力斗争不息;二是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不息。
冯玉祥当旅长之前,可谓一帆风顺,升迁极快,仅仅18年便由一名士兵升至将军。这当然与他娶了陆建章内侄女,得到陆的扶持分不开。在北洋军阀内部,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司空见惯,冯对陆也一直怀有感恩之意。但冯玉祥毕竟与那些军阀有所不同,他不会随声附和,不会趋炎附势。他很快就对陆建章的所作所为产生不满,而且与日俱增。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陆搜刮和运销烟土。陆建章督军陕西后,为大量搜刮烟土,常常动用武装,四处查搜,然后将查没的烟土。远运京、津一带贩卖,牟取暴利。上梁不正下梁歪,督军署内的大小参谋、副官,也三五成群私自查搜烟土,再将其贩卖,中饱私囊。二是结党营私。督军署上上下下,任人唯亲。腐朽不堪。因陆为安徽蒙城人,于是督军署参谋长是蒙城人,副官长也是蒙城人,因而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后来索性公开求用蒙城人,造成陕西督军署内成了清一色的蒙城籍。
人们用“口里会说蒙城话,腰间便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
三是姑息养奸和收受贿赂。陆建章就任陕西督军后,大量招收门生,而且接受部下贿赂,毫无收敛。陕西一旅长为讨得陆的欢心,一次便将二万两烟土奉献,以为拜仪,而陆欣然笑纳。
此事传出去后,在军中震动极大。陆却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冯玉祥对陆的种种做法,极力谏劝,非但陆置若罔闻,反而招致陆建章左右的嫉妒,时进诽言。于是陆也逐渐对冯产生不满,甚至不愿再见冯的面。
在这外患内忧之际,个人前途渺茫之时,冯玉祥遂产生摆脱陆建章羁绊之意,想寻找机会离陆独自发展。1915年春夏之交,这个机会悄然降临。
转战川陕
袁世凯早有控制西南的主意,借口川变,于1915年2月由心腹陈宦取代地方将领胡景伊为四川督军。但陈宦在统治四川时,却遭到四川省各界的抵制。于是袁世凯命陈宦率重兵入川,以防不测。陈宦率领李炳玉的第一混成旅及任祥祯的中央混成旅入川。袁又令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川北,以这三个混成旅作为陈宦的武力支柱,控制四川局势。但陆建章则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为敷衍陈宦,陆命冯玉祥将其十六混成旅的大部主力仍留在陕南,仅率第一团于1915年夏初入川,驻节阆中县。
这时,冯玉祥在陕甘一带驻节已近两年,陕甘各方面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首先,这里地域广阔,军队迂回的余地很大,在军阀势力相互错综交叉之时,易于保存自己。其次,这里虽说自然条件艰苦,可西北民风淳朴,军民之间关系容易相处。再者,西北远离统治中心,便于发展自身势力。本来冯玉祥可以在这里有所作为,至少能较快地发展起来。但此事却使他不得不离开陕西,亲率一团兵力驻扎川北的阆中县。
离开陕西的冯玉祥,随着北洋军阀造成的混乱局势,转战南北,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北京等驻节,厮杀于军阀混战之间。沉浮于大大小小的宦海仕途之中。由团长升任旅长之后,八年之间再未升迁。冯玉祥所率的十六混成旅在饷项给养方面也由于北洋政府的阻挠,经常受阻。冯曾在1921年1月9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饷项奇绌,目兵仅以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冯为饷项经常寝食不安。
为何北洋政府要克扣十六混成旅的军饷呢?曾跟随冯玉祥20余年的王赞亭认为:“自冯玉祥当旅长之后,在许多事情上违背了北洋军阀首脑人物的意志,如冯在四川响应护国军参加讨伐袁世凯之役,在河北廊坊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役;在浦口按兵不动反对援闽;在常德不听吴佩孚命令,不参加直皖战争;与南方护法军取得联系,擅自北撤,等等。”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这些做法
无疑向北洋政府表明了冯玉祥决不是一个附首贴耳的奴才,自然也损害了军阀们的利益。北洋政府认为冯玉祥一贯不听命令,而且与南方革命势力暗中往来。因此,早已不把冯玉祥及十六混成旅当成自己嫡系成员,便采取排挤和压制。不仅不再提升冯玉祥的职务,不允其再扩充兵力,而且时时克扣军饷,使冯的部队经常陷入困境,以为这样便可将其逼垮,置十六混成旅于死地。
面对此种情况,冯玉祥气愤不已,曾在部下面前表示,我们决不能坐等饿死,北洋军阀政府虽不把我们当做国家的军队对待,但我们仍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一定要撑起这副穷骨头干下去。冯玉祥这时抱定了一个信念,要依靠这支军队。为国为民有所做为。但此时的冯玉祥对北洋政府仍抱有幻想,即企盼得到中央的重视,希望中央有一两个“贵人”相助,使自己的部下饷项充足,装备精良,成为一支具有较高战斗力的军队,能担负起拯救民族的重任。然而在军阀统治的国家里。现实一次次地使冯玉祥的企盼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
这时南京的孙中山先生却对冯玉祥十分关注。1921年夏,北洋政府内传出一种信息,十六混成旅有移驻陕西的说法。孙中山当即致信给冯:“陕西在中国北部,形势重要,将来建立革命基础,扩而充之,则革命事业,可告成功。”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47页。
孙中山敏锐的眼光,炽热的鼓励,无疑给早已具有在西北地区建功立业之心的冯玉祥以莫大的鼓舞。他决心回到西北,到那个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去成就一番业绩。
直至1921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北洋政府撤换了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以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接任。陈树藩拒命不交军权,阎相文准备用武力接收,除率领本师人马外,调吴新田的第七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随同前往。冯玉祥在转战数年之后,从河南信阳率军西移,向陕西迸发。
陕西督军陈树藩,安康人,陆建章任督军时为陕北镇守使,后因反对陆建章举行兵变,推翻陆而取代督军一职。为了个人地位,陈拜段祺瑞为老师。他虽非北洋系军人,由于以师生关系依附段祺瑞门下,并加入了段操纵的军阀团体——“督军团”。在“府院之争”和直皖两系的斗争中,一直充当段祺瑞的工具,“统治陕西五年,极尽搜刮盘剥之能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202页。地方积怨较深。阎相文率部入陕,调十六混成旅为先锋,驻灵宝,取渑池、陕州,直逼潼关。
此时的陕西,军队林立,武力庞杂。大致分三支势力,一为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多貌合神离,真正能为其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二为省长刘镇华所属镇嵩军,本为盘踞河南嵩山的匪首王天纵部下,民国初年被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且刘本人对陈树藩口是心非,只图借机发展自己势力。三为渭水北岸的于右任、胡景冀的部队,驻扎三原一带,虽归属皖系,但早有驱陈之意。
冯玉祥率先头部队抵潼关时,便采取分而治之,瓦解陈树藩部下,并从陈部驻邠州的郭金榜处,掌握了陈各部驻地、人数、装备的重要情报。于是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纵队,分别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梯次进发。由于陈树藩军中有诸多弊端,部队缺乏战斗力。冯军到来后,大多如惊弓之鸟,虽有少数如困兽犹斗,但兵败如山倒的总趋势不可逆转。冯军第一纵队先败陈部姜宏谟于阳郭镇;第二纵队又击败陈军于灞桥;第三纵队再败陈部姚振乾于蒲阳镇。并在韩信塚与陈军主力激战一昼夜,迫使其退入西安城内。冯玉祥亲率第三纵队的炮兵连,指挥炮击督军署。陈树藩不得不在四面楚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放弃守城,化装成一商人,乘乱逃出城外,先落脚咸阳。冯率骑兵追击,陈部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景翼收编外,其余逃往陕南山区。
经过这次战役,阎相文十分赞许和感激冯玉祥及十六混成旅。屡次致电北京的曹锟,称赞十六混成旅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此战役中功勋最显。并电请北京政府将该部扩编为师。曹锟、吴佩孚因对冯早有戒心,对扩编的电报置之不理,阎相文穷追不舍,连发电报八、九份,曹锟才下令批准将冯的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任命冯玉祥为师长。
曹锟虽同意改编冯部为师,但为限制冯,附有不加饷不增枪的两个条件,实际师仅为一个空名,兵员及战斗力仍为旅。
然而这毕竟给冯玉祥势力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混迹北洋军阀队伍20余年,升任旅长后也有9年之久,冯深知此种机遇的重要性,抓不住便会后悔莫及。遂将所属部队迅速编为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为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兵营长,委任门致中为参谋长。这样,原模范连的骨干均被委以重任。作为军阀部队里的一员将领,冯玉祥有了这支雄师,便有问鼎国事的实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