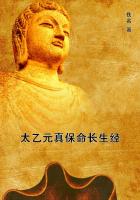那对桃花坠静静躺在妆台,象牙上所錾的桃花灼灼,流光溢彩,幽幽诉说一段段璀璨流离往事。我被蛊惑似的戴上桃花坠,万千红尘里蝶舞翩翩。
天边月正弯,夜凉如水,鸾镜里的女子,恬淡的面容,肤如凝脂,而眸子,沉静如千年深潭。久久凝望,再无眠。
我趿鞋推门,踏月而行。微凉的月光,细细落落地零散苍穹当中,夜沉沉,皇宫无语,如同一座囚牢,将我身心囚住。形影孤独,若有一壶桃红,能否将千古伤心事酿入酒,凭月而醉?
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到了何方,只知月凉随我,洒了一路相思。忽然,步子顿住。眼前宫殿巍峨耸立,大气磅礴的宫墙尽是飞檐走兽,宫门上九十九颗铜钉硕大圆润,令人生畏。正殿匾额上是开国皇帝离茂然亲笔所书的“凤鸾殿”,沉沉让人生怵。朱红色殿门紧闭,如数年不曾开启一般。
怔怔望眼前的凤鸾殿,思绪万千。
隐隐间见得偏殿后有些薄烟不时飘起,我正心里生疑,便听到宫里惊传起,“走水了!凤鸾殿走水了!”这深宫如同被惊醒的猛兽,慌乱中发出怒吼。一群黑衣宫侍也顾不得不许人进凤鸾殿的规矩,启开了这沉闷紧闭的殿门,冲了进去救火。我亦趁乱潜了进去。
待得火势扑灭之后,离诺殇才匆匆赶到。见凤鸾殿中狼藉满地,脸色铁青,“凤鸾殿中素来小心,如何走了水?”
前方一名黑衣宫侍低头答道:“回皇上话,奴才已经查过一番了,宫中一切都无异样,并非人为!”
“并非人为?”离诺殇怔了一下,缓缓轻咳一声,我隐身在宫墙下,听闻他这一声轻咳,几分失神,曾几何时,未离歌也是如此。恍惚望那缥缈烟云,心神游移不知所在。
离诺殇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那是何原因引起?”我望他后背,竟有轻微的颤抖。他缓缓反剪双手于身后,袖口龙纹狰狞。
那宫侍嗫嚅了几句,却支支吾吾地说不成话。
陈冀在一旁喝道:“有何支吾的,万岁爷面前,只管直言!”
“是……是……”那宫侍支吾了几声,却还是颤声不敢说出来。
“说!”离诺殇只一字,也未厉声,只落于人心里,有说不出的压迫感,便是随在身后的我,也不禁后背起了寒意。
宫侍扑通一声跪地,“皇上饶命,奴才也是听人说的……”他颤音说着又偷眼看离诺殇,没察觉离诺殇的神色有任何变化,便又壮胆子说了下去,“他们都说今日是华瞬皇后忌日,皇后当初也是……”
还未等这宫侍说完,陈冀脸色骤变,蓦然似暴风雨劈来般的话涌出:“住口!没眼的狗奴才!”
我凝眸静静望离诺殇,一丝轻蔑的笑意如那早消散的薄烟,幽幽再度滑过唇畔,只无人察觉罢了。
离诺殇冷冷地道:“宫中传播谣言,其罪当诛!”
那宫侍早面无人色,听得离诺殇这般凌厉的话语,更是瘫作一团,便由侍卫们架了出去,连半分挣扎也没有。
我手心沁出薄薄凉汗,慢慢缩回袖中。离诺殇,果然不愧为冷酷之人,只一句话,便要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
殿门外似有人哭唤。
离诺殇问陈冀:“是何人在哭?”
陈冀急忙朝外而去,不多时匆匆便回来道:“皇上,是意嫔娘娘身边的烟纱姑娘哭着求见皇上!”
离诺殇不以为意,锐利的唇锋含着稀薄的关切,“为何事?”
“烟纱姑娘说是意嫔娘娘听说了凤鸾殿之事,又惊又惧,晕厥了过去。”陈冀小心翼翼近得君前方才低声道。
离诺殇眉头蹙紧,神色一时间也变得凝重,半晌过后,他问道:“可传太医瞧过了?”
他待意嫔并非无半分情意。我在一旁想,如若不然,又何必冒了天下人骂他乱伦之名,留她于后宫呢?
陈冀低声道:“已经传过太医了,太医说意嫔娘娘只是惊惧过度而晕厥,已经开了压惊汤药。”见离诺殇神色缓和了几许,便又拿捏着轻重仔细说,“烟纱姑娘说意嫔娘娘服下压惊汤仍不见效,梦魇里直喊着华瞬皇后闺名,烟纱姑娘请皇上移驾皓月轩。”
彼时雨已歇,月色晚来,清凉而朦胧的玉色笼在离诺殇身上,只因听陈冀说意嫔在梦魇里犹唤华瞬皇后闺名这一句时,本是冷毅的脸庞缓慢地柔情万种,甚至有了几许怜惜。
离诺殇深深一眼望向寢殿,似有依依不舍的留恋,那一瞬间,我甚至以为,他是真的痴执于凤鸾殿。
随宫门再度沉沉关上,那凤鸾殿,又成了一个无人之处。
我站在凤鸾殿外汉白玉石阶梯上,抬首眯眼望向那座宫殿,琼楼玉宇终究不胜寒。纵是刚刚那般烦乱又如何,现如今,一切归于平静。仿佛那不久前的一幕,不过是一场梦。这一地,再也无繁华,只我一人孤幽幽伫立萧瑟寒风中。月色零落成尘,冷云徘徊。
步下玉石阶,发上钗环撞出清脆的响声,伴着幽草间寒虫断断续续的低吟,如泣如诉的凄切悲沉。转过凤鸾殿,树影婆娑,细碎的月影落到我身上,仿佛摇落了满身花影。
“卿墨!”
这一声,突然在身后传来,唬得人骤地惊起。
我顿足,不再往前,却也不回首,就那样伫立于幽森树影之下,任身后那人步步近我,淡雅的一缕幽兰香沁入鼻端,悠然胜过千般风情。
“果然你便是卿墨!”
亦如幽兰的声音缓缓送入我耳中,我回首,见那人身着浅碧色锦缎抹胸,下系白色曳地胭脂荷花裙,外披件淡霞色纱衫,褶褶如雪,月华流动轻泻于地,一头墨色的发丝绾挽成青丝鸾云髻,髻鬓间并未有任何的钗环首饰。
当目光落于她面容之上时,忽的脑中轰隆一声,我不自觉地退后两步,却不料狠狠撞上身后的树上,后背硌在树干上,一阵刺骨锥心的剧痛将我打得清醒。我失态了,在这个女人面前失态了。
恍恍惚惚,我用笑意掩盖自己的尴尬,“不知贵人是?”缓移步福身行礼,心里隐隐约约已经知道她是何人。
我常爱读《桃夭》,总不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女子当是如何的明眸善睐,而她,却不由令我明了何为桃夭,何为灼华。如是那般妩媚纤弱,如是那般顾盼生姿,如幼时所见的画里款款走下来的曼妙仕女一般,令人难以移目。
“你未曾见过我,我住伊影阁。”
伊影阁。
我心沉下去,已然知了,除她还有谁?
“卿墨见过白夫人。白夫人安好。”急急行礼,也许在她眼中看来,我仍是镇定自若的,可我心知,沉静了多年的心绪,在今夜里,真正掀起了波澜。
白夫人居伊影阁,是这宫中除却妤妃之外最得圣宠的女子,她虽是位级六品,却是连妤妃都忌惮几分的主儿。
白夫人,我一直想知道的人,原来是她,原来她容貌如此。
怪不得,那日里我问离落凡白夫人是何许人时,他会怔住许久后才答我一句,寻常宫妃。
怪不得,最初我问徐媪白夫人的事时,她会犹豫再三,还带了几分哀痛与我说,他日里,等我见了白夫人,自然就知了。
而今,我亲眼见了白夫人,自然,我知了。
悠悠然,心里冷笑,笑得连自己都不禁战栗,眸子微转,便一眼瞥见衣袖轻轻颤动了下,心思转圜。
“夫人好兴致,也喜独赏月色。”我莞尔而笑,说话时眼眸却在她衣袖那边游移不定。
白夫人淡笑不语,只望我面容,深深打量。
我的笑缓凝在唇畔,“凤鸾殿刚刚突然走水,夫人可受了惊吓?”夜已这般深沉,凤鸾殿突然着了火,而她白夫人会这样出现在凤鸾殿外,难免让人猜度。
出乎我意料的,白夫人只微变了神色,微抿如花般娇柔的唇瓣,“你果然聪明,怪不得端木青妤会失了算。与其成为他人棋子,不如自己另开一局。”
我颔首,“夫人有心,却到底成全了意嫔娘娘。”白夫人与意嫔之间的利益瓜葛,那一日在关雎宫中意嫔主动向离诺殇提及白夫人身子不适之事时,我便知了几分。只那一时,并不知意嫔为何会与白夫人结成联盟,今日见到这白夫人倾世之容,便明白了。再联想那一日撞见意嫔与云映夕走得近,白夫人为何在此出现,心间了然。
白夫人高深莫测地笑了,眸子掩去了几许精明,“卿采女倒是知道得不少,不似寻常采女那般只知一味争宠。”她手仍在衣袖里,却不再颤抖。她静笑若空谷幽兰,走至我身边,低声叹息,“过分显露山水,不该是你的作风!”
“既入了这宫廷,哪里半分由得了人?便如意嫔娘娘,虽与夫人素来交好,却总难免有几分私心,夫人您说,不是吗?”我如此说话,心里却叹,这个白夫人,也算是位作壁上观的人,虽少出伊影阁,宫中人事诸多变幻却都不曾逃过她眼。
如是这般,这宫里可是有不少热闹可看了。
“是吗?”白夫人似笑非笑,轻拂衣袖,一态自然。她转身走前,而我紧随其后,只听得她淡淡地道,“楚意如若非因她是华瞬皇后的亲姑姑,又如何能在这深宫中待得长久?”
我心中忽的一紧,脸上却故作惊诧,“原来,意嫔娘娘是华瞬皇后的亲姑姑?奴婢愚钝,这层关系竟是如何也想不透的!”
“虽她楚意如与华瞬皇后是姑侄,但年纪较华瞬皇后不过是长四五岁罢。昔时她为先皇所宠的楚昭仪,便与还是殇亲王的当今皇上私交甚深。而殇亲王初识楚氏阡陌——也便是后来的华瞬皇后——便是由她楚意如所安排的,殇亲王对楚阡陌一见钟情,非卿不娶。而后来,先皇驾崩,传位于殇亲王,殇亲王想立楚阡陌为后,楚昭仪一力促成此事,皇上感激她,便留了她于宫中,也便是民间所说的弟娶兄嫂。”
我忽然得知离诺殇初识华瞬皇后以至立其为后,都是意嫔一手安排的,顿时心里泛起了无尽的恨意,原来,都是她!
唇舌间漫起了腥甜味,我狠心咽了下去,只随白夫人的话轻轻叹息,“原来如此。”细细思量,便又低声问,“皇上对华瞬皇后之情,是否真如传说那般?”我与白夫人虽并不熟识,此回初见,我这般毫不顾忌地问她关于离诺殇的事,倒也是一种缘分。
“华瞬皇后,是这后宫中的谜。”白夫人苦苦一笑,清丽的面庞尽是嘲讽,幽幽浅笑,却又道,“我能受宠,你可知是因何原因?”
我摇首,只作不知。
“你看我生得如何?”白夫人含笑问我。
我垂首答:“夫人容貌倾城,气若仙华。”
“你倒是会说话。”白夫人暗暗敛了眉,“皇上宠我,无非是见我的模样与华瞬皇后有一两分相似罢了。他人不知,而我却心知肚明,这宫中,任谁与华瞬皇后有几丝的瓜葛,都将被皇上看重。而你,卿墨!”她凝睇于我,直看得我后背阵阵发凉,“你敢否认,以你之姿色,能入宫为采女,不是借你的名字音近于华瞬皇后闺名?”
她是如此直接,半分不曾委婉。我有些许愣神,继而含笑道:“原是沾了这等光。”我自嘲于心,只步随其后,也不知走了多远,转了多少回廊,眼见得前方宫殿是君仪殿时,微顿了步子,缓了下来,轻声道,“今夜与夫人相谈,获益颇丰。卿墨在此谢过夫人了。”我心思忽一动,便又道一句:“看来今夜里,皇上不会回来了。”
夜风拂乱了她的发丝,她抬手轻抚去额间细碎的落发,眸子幽幽望向君仪殿,黯然垂首,“是啊!”她喟然长叹,“你所言不错,终是我成全了她!”
我岂不明白她的意思,心间一缕恨意莫名地泛开来,“意嫔娘娘吗?”她么,先是利用华瞬皇后楚阡陌得以留于宫中,如今又利用白夫人与妤妃争宠,这后宫之中,明里她是最不得宠的,可暗里,就如同离诺殇所言,她性子还是那般的,连新入宫的女子,都不放过!她便是爱斗的女子。
白夫人倾世的面容上幽幽绽出一抹凄绝媚笑,“卿采女,今晚,本宫不曾与你见过。”见我颔首不语,她那一抹笑悄然凋零,“你想保得安好,本宫自会如你所愿。”
保得安好?
心间笑意愈发得冷漠凄厉,我又何曾不愿安好一世?只这人世间的无情狠毒,已将我所有的天真烂漫毁于一炬。所谓的安好,不过是无知孩提时代的最美好愿想罢了。
我噙一缕绵绵如春日暖阳的笑意,款款福身,“奴婢从未见过夫人!”白夫人满意转身而去,我心田里的恨意却如那夜凤鸾殿的火势一般,一发不可收拾,熊熊窜向九重天。
心像被谁狠狠揪住,那样的疼,而面上却拼命地笑着,笑着一步一步走回采薇宫。墨云峭寒起,这夜里竟忽然下起雨来,一脚重一脚轻的,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长长的裙裾拖在泥水里,似是要拽住我,不让我走下去。
仰头,雨倾如注地朝我脸上打来,步子一踉跄,摔倒在泥水里,满嘴的泥沙。视线模糊,可白夫人那张倾世容颜却清晰地闯入脑中,如此讽刺!
雷声轰鸣在耳边,嗡嗡作响,却掩不去白夫人那一句:“皇上宠我,无非是见我的模样与华瞬皇后有一两分相似罢了。”
“哈哈哈……”我放肆狂笑起来,如撕裂了自己一般。
心里的苦涩泛滥开来,将我所有理智吞没。我挣扎着爬起来,寻回去的路,狂风雨夜里,已经迷失了方向。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只见得前方隐隐约约有个亭子,因隔得远了,看不真切。
一笑,却也顾不得那许多,只跌跌撞撞朝亭子而去。
进入亭子,我一身早已湿透,发丝紧贴面庞,一缕一缕的,滴滴答答淌着水,钗环早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发髻乱作一团。恍惚记得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狼狈的。
转头见亭角有一丛花木,我踉跄地走过去,藏身其间,我的狼狈又怎么能让别人瞧见呢?抱膝坐在石板上,听亭外雨声,淅淅沥沥漏了一地的伤疼,悄无声息地蔓延开去,是这一季的风流。而我心,早如一寸一寸的龟裂土地。
抱着自己,感觉身子瑟瑟发抖,我好累,好冷。可不过一会儿,就觉得身子发烫,眼前的事物也一阵模糊,一阵清晰的。
“她既要死,便成全她!”梦里不停地听到这句话,那样冷漠无情的话如同吐着猩红信子的蛇,狠狠噬咬我心。
我哀哀地哭起来。
似有人在亭子里说话,听得不太真切。
“皇上还在想凤鸾殿走水的事?还是想到了华瞬皇后?”
“华瞬?”男子的声音好熟悉,“朕总怕想她,怕想起她,就会陷入无尽的悲痛。楚阡陌的心,太狠了!”
“皇上……”
“她毁了朕所有!朕便毁去她最爱的楚府桃源!”
楚府桃源?
梦魇里突然听到这四个字,如同被毒蛇狠狠咬一口般,痛不欲生。我想躲,想逃,却无处可去。
头胀得欲裂开,想开口喊却徒劳。雨声、雷声,乱哄哄一片。
我浑浑噩噩感觉身子软绵绵的,似有人抱起了我,像是离落凡温润的关怀声,“墨儿,可好?”又像是未离歌温暖的怀抱。
春风拂过,如那年三月。我折枝桃花冲他盈盈而笑,“你长得真好看,我以后便要嫁你这般的男子。”
他是那样好看的男子,那样深深烙在我心头。
零零落落的雨打在亭外,弹出一曲大珠小珠落玉盘。身上似暖了起来,我像是被谁紧紧抱住,有些透不过气来。
夜雨飘摇,我极力启开眼眸,想维持自己的清明,用了好大的力,才微微睁开沉重的眼,落入眼中的面容,那样冷漠,那样无情,好陌生。心忽的一颤,一直往下坠落,沉入万千深渊里。
我拼命地想抓住什么,可是挥舞着手,总是抓一片空。幽黑的深渊像是永无止境一般,飞快地坠落,又被墨色吞没。我不想这样一直坠落下去,我张嘴想喊,可什么都喊不出来,明明已经张开了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不要,我不要这样!再坠下去,我不知道会陷入什么样的万劫不复里,我不要!斑驳的人世里,我还有舍不得的,我还有没做完的事!
魂魄似要挣脱开我的身子,任我怎么想拉回,都无济于事。
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皇上……怕是不好了……”
听得不真切,只知周边一切纷纷扰扰吵闹,却分明地感觉到有一双手始终将我环抱,任是如何都不肯放开。那手,如烙铁般,极烫。
昏昏沉沉的,所有的挣扎都抛弃了,终是坠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