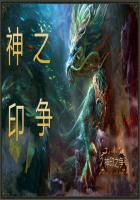我将三千青丝剪断,一地墨云铺洒倾开,华裳丽衣铺在猩红的地毯上,锦绣如画。铜镜晕开昏黄的光彩,渐渐模糊了镜内的面容。金剪仍握在手中,一缕发丝纷飞起,黝黑黝黑的颜色,却承不起女儿家最美的年华,只无力地坠落于地毯上,上演一场结局。
窗是紧闭的,外面的风很大,因为寒冬已经过了。春光明媚,但不属于我,花颜姣好,也不该是我的。
我看着摊了满满一个妆台的金簪宝钗,华胜步摇,玉环翠珠,夺目生辉,顾盼生姿,任是女儿家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一两眼,而我只是淡淡一笑。
并不是自负貌美,不必用这些饰品来给自己添色。只不过是长得太普通,面容太过平凡,连自己也不愿多看自己一眼罢了。
门,被人很不礼貌地推开,铜镜在阳光下飞尘流光迫我偏过了头,转移了眸光,看清了来人,我自椅上起身,沉眸敛眉,淡淡地望他。
他咳嗽了一下,一袭白衣胜雪却没把他衬托得如仙般,反给他平添了几分的苍白与羸弱,略显清瘦的面庞上,一双漆眸透着与世无争的精明。
他看到我手上的金剪时,稍愣了下,笑声却自他喉里低沉地溢出,“又想不开了?”他拿过我手中的金剪,低叹一声,“女儿家的头发是很珍贵的,不能老是去剪的!”又执起梳妆台上的玉梳子,缓慢地帮我梳理零乱的发丝,很温柔,像水一样柔软的手指滑过发间,那种感觉我很依赖。
“离歌……”我轻唤他名字,无意识地抿紧了唇。
“跟你说过很多回了,我复姓未离,名歌,不是离歌!”他略有不满地截断了我的话,他叫未离歌,可我总是喜欢叫他离歌,很多很多回,他都急着纠正我的错误。可我每回都忘了。
“离歌,如果你是女儿家该有多好,那样我入宫就可以带上你了!”
我微笑,眸子沉静如水,回头看他一眼,他像是在憋着咳嗽,苍白如玉的面庞上透着绯红,多了几分可爱,他的寒星墨眸正盯我,一片莫名的怜惜让我浑身不自在,我不由得转过了头。
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药香味,我的心滑过一丝悲伤,这就是未离歌,世人皆知的天下第一神医,妙手回春,再世华佗,却鲜少有人知,他便是有再高明的医术也治不好他与生俱来的病。
他缓俯身近我耳畔,低叹一句:“墨儿,为什么你的眼里,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露出那样深沉的哀伤?”他的手指在我发间时,总是很温柔的,可覆于我眸前时,却让我总有种不真切的感觉。
我握住他的手,嘴角勾出一抹浅笑,“我连你都骗过了,不是吗?”我的眼里,哪里还会有哀伤?
似笑非笑地拿下他手来,他已经帮我梳好了发髻,绾得有些随意的芙蓉髻,却很精致。镜中人儿头上斜插一支点绛唇步摇,额间花钿亦是富贵之花。人靠衣装,装扮出来,平淡如我居然也有几分可见人了。他细细审视,瞳子渐变得幽深起来,他怜爱地抚我的面庞,呢喃:“若当初不曾……”他轻抚着,另一只手却不由地拿袖掩了唇,又低低咳嗽了几声。
我脸色骤变,狠狠地将他的手甩开,用力扯落耳上的玉坠子,耳朵生疼起来。
“未离歌,没有当初!”我朝他吼出,推开他,然后跑到窗子前,撞开那厚重的窗子,跃了出去。
窗外长着茂密的荆棘,我曾几次跳出窗子在那里受过伤,可是,我总是会忘了疼。有些疼,是自己给的,不会记得。可有些疼,这一生都记得。未离歌什么都可以跟我说,就是不能跟我说当初的事。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我闭目,等待又一回的遍身伤痕。
可是,我没有落到荆棘丛中,却落到一个温暖的怀抱里,似有若无的暗香拂过我的鼻翼,如一片轻柔羽毛,抚慰我的心,让我渐渐平静,不再狂躁。
暖风煦阳,十里杨柳青翠依然,芊芊柳枝舞着柔软嫩腰,春光极好。
自我头顶传来极好听的声音:“三年已过,还是如此?”这声音于我,有如天籁。我安静下来,任他放下我。他未见过我这副精心打扮的模样,只转身走向前院里,我亦趋步紧紧跟随,生怕一不留神被他抛下得太远。那一袭青衫,我盼了太久。
桃树下,一把瑶琴,两盏桃花酿。流莺舞蝶,殷红片片点莓苔。
他走到树下,举起一盏酒,轻浅酌,略沉思,方才回头看我一眼,风起拂过他宽大青衫,发丝飘舞,却并不乱,反有几分萧索。飞花翩舞,乱红如雨。
看这一场碧桃攒云般的桃花雨,我情不自禁吟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我喜欢桃花,尤其喜欢他喝得微醉在桃树下的模样,落英缤纷,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而他举盏答春风,感流年。
花树下,他有几分无奈地看我,渐渐眸子微眯,像总是这样一般,可只有我知道,他在外人面前,不是这般的。他在外人眼里,是个极为谦卑,甚至是懦弱的男子。而此时,虽是微凝眸看我,却暗里藏了锋芒,敛起的剑眉让我心里不安。我低垂下头,不敢再在他面前有什么举动。
“你……”他唇锋略扬起,坚毅的下巴倨傲地一扬,“不错,可入宫!”他吐出的字让我心寒,从来,他说话从不会超过十个字,就像现在这样。
我扬眸看他,一丝苦笑不自觉划开。
入宫,并不是我愿,可是我也不能不入宫。
“是吗?”我疑问,歪头看他,不用想,其实也知道这是肯定的答案。
朝清三年,皇帝离诺殇下旨采选,令天下各地官员举荐十四以上二十以下才貌双馨之女入宫应选,充盈后宫。
当今皇帝登基三年,还算是年轻有为,锄贪臣,诛恶势,政吏清明廉洁,疏通南北运河,平定几场叛乱,甚至还在登基之年亲率大军出征西南,一改离氏王朝几朝来的不振之风。他作风凌厉,手段狠辣,朝野上下皆惧于他。
他应该算是个好皇帝吧!只不过,在民间,他的名声并不好,因为,有人传说他的帝位来得不光明正大。先帝体弱,长年卧于病榻,太子年幼难当大任,于是朝中大事便都交由皇弟离诺殇来处理,渐渐大权落于他手。先帝驾崩,留下遗诏,不是立太子为帝,却立了他这个皇弟。曾有不少老臣因反他为帝而遭满门抄斩。更有太医说,先帝是中毒而死,这更坐实了他帝位非光明正大得来。谋权篡位,杀害兄长,欺凌幼侄,这些才是民间对他的评价。
而那个废太子,便是此时站于我面前的青衫男子,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离落凡。在我眼中,他人也正如他名字一样,是个落入凡尘的仙人。皇帝为昭显自己的仁德,封离落凡为靖陵王。离落凡这些年小心翼翼地卑微地活着,渐渐已经被人遗忘。
我接到这采选诏书之时,嗤之以鼻,这世上,想入宫的女子不过是贪慕荣华之辈罢了!
离帝后宫,倒也有些耳闻,他登基之年,立楚氏为皇后,但楚氏命薄,新婚当日凤鸾殿一场大火焚尽了她红颜一世。离帝伤恸不已,追封楚氏为华瞬皇后,一年未宠幸妃嫔,后宫也未进新人。后来,先后纳了几位妃嫔,后宫也便不再那般的冷清。众妃当中,民间传说是最得圣宠的是妤妃,而最不得圣宠的是意嫔。民间有秘传,这个意嫔侍了两朝帝王,想来也不容小觑。
几声琴音将我自思绪中拉回,零星的光影斑驳落下在离落凡的衣上,给他的身影添了几分孤寂。
“靖陵王!”
未离歌自屋内出来,“你是来接墨儿的?”未离歌微笑着问,又掩去了几声咳嗽。
离落凡颔首,看我一眼,低声道:“三日后入宫!”
我迎上离落凡的视线,想从他眼神里看出一丝一毫的温情,那样我至少能感觉到我不是被当成他的棋子。可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我是非要入宫不可的,不为他,也得为我自己,这是我发的誓,此生都不可能违背了这誓言的。有粉嫩的桃瓣飞落到我丝履上,恰如其分地点缀了平淡的丝履。我本是喜欢桃花的,可是这时,我却有些嫌恶地跺了脚,踩了那瓣桃于脚下。
“卿墨!”他略有不满,唤了我的名字。
我怔住,痴痴望着他,三年了,三年来,他从未叫过我的名字,仿佛叫起我的名字于他而言,也是一种伤痛。甚至于,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我叫什么。
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不是吗?
他的唇抿得很紧,瞳子漫上了重重的阴翳。我等他生气,等他冲我发怒,这样能证明他对我有几分放在心上的。
“若不愿……”
我等了许久,却盼到他这一句话,心陡然跌至谷底。
“我要入宫!”
我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这该是我认识他到现在,第一次敢大着胆子打断他的话。他的“若不愿”,或许是真有几分想放了我,可是,我不愿,不愿被他放了,我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
他瞳子笼着淡淡忧郁,怜爱地伸手抚向我面庞,我阖眸,静享他冰凉的温柔。“沉稳些,莫再这样!”他修长的手指忽然在半空停下,顿了顿,终收了回去。
我启开眸时,他已经转身远去,桃花无声地坠落了一地,他走得毫不留恋。
我用力冲他身影喊:“靖陵王请放心,卿墨记着了!”他回头看我一眼,眸华若玉般温润,泛着淡淡的忧伤。
默默地我记下了他的话,沉稳些,莫再这样。沉稳些,这世上的人,最沉稳的,便是他吧!可他的沉稳,近乎于隐忍。青衫玉立,他如那一抹最苍凉的夕阳,却叫我心疼。
“遇着他,你总是会沉不住气。”未离歌的声音响起,“墨儿,你已经十八了!”他轻叹。
我抬眸看他一眼,“以后不会了!”如他所言,我已经十八了。
“离歌,为什么你会这样尽心助他呢?”我想帮他,成为被他利用的人,只是因为我想让他开心,不想让他这样忧伤。而未离歌呢?他又是为什么这样尽心帮助靖陵王呢?
未离歌这回忽略了我对他的称呼,望向远方若有所思地道:“他曾救过我的命!”
我浅笑,看了未离歌一眼,轻幽幽道出一句:“你也救过我的命!”转身入屋,我要去收拾入宫的物品,还要收拾自己破碎的心情,我要面对的,可说得上是这一生最不愿面对的。
入宫的前一天晚上,月色静好。
未离歌与我一道在桃树下赏月赏花品酒品人生。他待我极好,似乎是没有目的地待我好,从那年救了我回来后,他便一直伴我在这远离尘世的山崖。月隐在墨云之后,渗出些如水的光,倾泻而下,山崖桃花碎碎落影,或浓或淡,如一泼水墨卷。清泠泠的月色下,浮动着暗香,沁人心脾。
淡淡间,未离歌拂落我衣襟上的桃瓣,纤长指尖若花蝶轻舞,他幽幽地笑了,“布了那么久的棋,终要开局了,还有些舍不得落子呢!”
山崖风吹起这一地的桃花,似工笔细绘的一幅画。
我看着他,不发一言。这一局棋,是离落凡布了三年的,自离诺殇登基那一刻,便开始布局了。如今,以我开局。
可在我眼中,这并不是一局棋,而是一幅画。一幅要画下如画江山的画,他们研墨三年,我是点墨之笔。疏、密、聚、散的布局,一如画者的心怀天下。
如藤蔓的月爬上了桃枝,折一枝春华,明年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