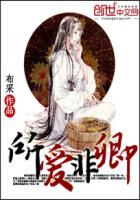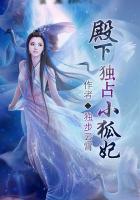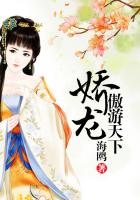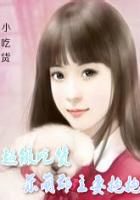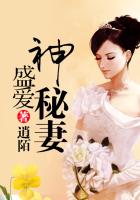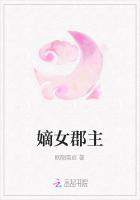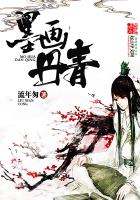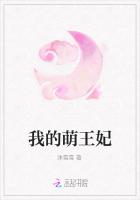少女失踪案过后,钱塘县内被绑架的少女均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百姓门前往县衙想好好谢谢这位父母官,王清没有接受任何一家的谢礼,而是诚恳的向百姓们道歉,他认为是自己的失职才导致了城内这几日的人心惶惶。在小小眼里,王清的确是古之清官的代表,为民请命,两袖清风,刚正不阿。
这千年前的日子,到也是平实无奇,除了看些古籍,打发时间,却也无太多事可以做。好在这来自千年之后的叶絮本就是个自持清静喜好阅读的人,在这的日子,也权当是悉心研学了。而秦夕言则是继续追查案发当日家中的内应。
那位寄宿在小小家中养伤的男子,在这期间,到是与萍儿有说有笑,也许是萍儿这份纯真直爽的性格,让他感到实在的美好。
一日,男子走出房门,见萍儿正在捧着《诗经》坐在院内,轻吟道:“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平时性格活泼的萍儿安静起来的样子,到是温文可人。
“萍儿姑娘也喜欢读诗么?”男子笑着问。
萍儿放下书,见是他,起身扶起他坐下,“起初到也是不喜欢,只是小姐常教我认字,而且叮嘱多读些诗书,久了就发现慢慢喜欢上啦。”
那男子拿起《诗经》见上面还有些人为注释,字体清新隽永,便问道:“姑娘所说的小姐,便是苏筱公子吧,这想必也是她的注释。”
这男子到也是颇有眼力,萍儿也不闪烁其词,好奇的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男子看着这注释,满意的点点头,回道:“其实那日第一次见到便知道啦,哪有生的那么俊秀的男子呀,而且看这屋内的摆设,清新淡雅,颇具灵秀,又怎会是男子的居所呢。看这山水诗画,她定然是位极有文学修养的女子。”
萍儿见这男子的分析,到也是不禁笑起来,话锋一转,便问,“看你好像对诗蛮感兴趣的嘛,快给我解释解释这首《饮酒》!,小姐说陶渊明一生几仕几隐,是因为一直活在矛盾之中,那他最后的归隐,是不是一种逃避呢?”
王清接过书,看着“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静静的说:“在魏晋的文人之中,无论何等拥有清风瘦月之情,都或多或少会有仕途的一面,这是千百年来,对知识分子价值判定的唯一途径,然而这条是难走的,难几乎看不到尽头,甚至不知什么时候会掉下万丈深渊。在无数个路口的抉择之后,才会选择不失去自身风骨傲气,潇洒的离去。若是陶潜仕途顺利,想必也不会有这般对淡泊的向往了,许是最后到了南山,才明白世间繁华不过梦里烟云,秋菊才是他一生的归宿,这正是几经辗转之后才选择的皈依,没有对错可言,更无须以成败论之,只因他终得以自由。可话又说回来,则其中又有历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弄清楚,什么叫真正的隐。陶潜说‘心远地自偏’,是因为心静则万色清宁,既然如此,红尘与山林便无异,又何必执著非寻一个南山呢?若真要有一个因由,我只能说,他一生的恪守,都抵不过一朵菊花的清淡,若魏晋玄风,清静无为。
看着这男子的思绪如此清澈悠远,萍儿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淡淡的问道:“你也希望这样对么?”
男子没有作答,静静的笑了。
二人拿着书聊了许久,无论萍儿问哪一首,这男子都能应对自如,丝毫没发现一旁的小小已经看了好久,见萍儿在这男子的带动下,到也不忍打扰。
萍儿抬头看了看没有月光的夜晚,星辰显得灿烂无比,若有所思,轻轻的说:“要是能见到眼下的著名诗人谢眺就好了。”那男子听到这名字,竟惊诧了一下,随后又恢复平静,便问:“姑娘喜欢谢眺的诗?”
萍儿满意的点点头,轻快的说道:“那是自然,像他的《游东田》、《治宅》等,诗句清俊,把自然的美感展现的淋漓尽致,想必他一定是个爱好山水自然的无忧墨客。”这萍儿说起自己心中的敬仰之人,到也是头头是道,想那时,谢眺的诗为无数人所爱重,更是在极大程度上推进了文风的发展。
那男子却未起多少兴趣,只是看着深邃的夜空,略带叹息的说:“可惜他不自由啊。时间也不早了,萍儿姑娘早些休息。”说罢,便转身离去,却突然见到小小静静的站在门口,面容素雅,二人交换了个眼神,相互轻轻一笑。
小小只是心里想着,这位男子将谢眺一语中的,他一生最大的悲哀便是不自由。
转眼伤已好的七八分,皇帝寿筵之期将近,那男子便打算即刻启程去建康。
人间四月天,桃花争艳,西湖水暖,小小与萍儿去山中古寺上香归来,看着男子在湖畔盯着对岸往来人群,亭台楼阁,感慨的吟道:“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萍儿到是快人快语,跑上前说:“对着这么好的春色,你怎么会吟出这般苦味的诗呀。”小小看到萍儿这直爽的性格,到是笑了笑,对着那男子说:“公子既忧虑宦海浮沉,又何必要泥足深陷呢?难道不能放弃仕途,只做个潇洒自然的红尘墨客么?”
说这话时,一位极其英武之人踏马而来,观其面色,凛然正气,那男子对着谢眺做揖行了马上之礼,说道:“前方均已安排妥当,大人,我们出发吧。”
男子对着小小与萍儿说道:“这是我的好友鲍仁,特来护我去建康的。”随后上了马,转身对着二人说:“小小姑娘之意,我又何尝不曾想过呢?我本有心向自然,奈何根生不得闲,既然已走到了今日,也就必须把路走完,小小姑娘多保重,萍儿姑娘,多谢连日来的照顾,希望我们还能再见,谢眺告辞了。”一言毕,便策马而去,萍儿望着那渐行渐远的男子,看了许久,只是迟疑的说出:“谢眺……”。
小小推了推萍儿,说:“人都走远啦,看来我们家萍儿也有坠入情网的时候呀。”萍儿听到这话,脸不自觉的红起来,忙解释道:“哪有,只是相处半月,目送一下。”想不到那日自己救的正是名满天下的文人谢眺,这实在是难以置信。
小小看着前方的路,心有所思:这就是南齐赫赫有名的谢脁么,那位李白一生终最敬重的南齐文学家。既舍不得放弃衮衮公服,又想远离血的现实,仕隐之路,多么难走。这难道就是魏晋风度吗?他们谈玄,却不以为隐遁山林就是淡泊宁静,也许他们的道,就是在仕途中得以超脱。嵇康如此,阮籍如此,陶渊明如此,谢脁亦如此。他们不求显赫人生,但却要不枉人间走一遭,他们不避世,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也许这就是不求一世,只争朝夕吧。
人间四月是繁华的也是优雅的,左岸“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右岸“一曲自幽山自绿,此情不与白云知”,萍水相逢,尽是镜里云烟。
这位与谢灵运齐名的南齐文学大家回到朝中后,并没有受到齐武帝的嘉许,只因他与荆州刺史萧子隆走的太近,而这萧子隆虽说是皇室一脉,但却属旁支,在朝中并不得志。加上早年因为与长史王秀之政见不和,结下了恩怨。谢氏家族在南齐的威望甚高,王秀之恐怕萧子隆会因此而培养自身势力,便早想对谢眺下手,因此派才派出府中得力的卫士前去劫杀,不料失败而归,只得采用下策。这次谢眺延误了送《兰亭序》正好给了他一个做文章的机会,皇帝本想降罪于谢眺,又念他才学出众,便让他留在建康,不得返回荆州。这样一来,王秀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谢眺自己却是觉得如履薄冰,他既无法明白自己的选择,也不能潇洒的选择离去,伤神之余,也只是饮酒消愁,这建康的日子,过也算清闲,皇帝没给自己派什么差事,自己到像是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小小既为谢眺此行担忧,却又无可奈何,只是兴叹这黑暗的政坛,也许昨日还是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明日便是亡命天涯。叹气之余,也深深明白谢眺的选择,他的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功名抱负,也是整个家族的未来,纵然他才华横溢却不得不行官场之道,纵然他有心归隐却不得不越陷越深,他的道是危险而优雅的。
思索良久,小小终以自己是这南齐的过客来安慰自己,只因一切早已注定,非人力可以改之。
已是午后,想起几日不见潘莲,突然有学习音律琴乐的想法,便回家换了身素妆,打算出发去找潘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