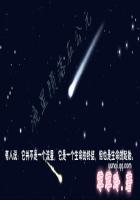月娥去上房请安,秦老爷碰巧也在,月娥朝父亲丢了个眼色,秦老爷何等精明,立刻明白,朝炕桌对面的季氏道:“夫人,知县老爷提及娥儿入王府为侧妃的事,娥儿大了,这事还是要她知道的好。”
季氏敛了神色,口气坚决地道:“不行,侧妃也是做小,上面有嫡妃压着,日子怎么能舒坦,我秦家虽出身低贱,姑娘也是当小姐养,不能由着人糟践。”
秦老爷眼风瞥向月娥,月娥走到母亲身边,挨着母亲坐下,撒娇地嘟着嘴道:“女儿想去京城,女儿打小没出过远门,想去京城见见世面,做王爷侧妃有何不好,金尊玉贵,女儿就要过风光日子,求母亲答应吧!。”说吧,扳着季氏摇晃。
季氏恨声道:“你以为王府是那么好呆的,王爷就你一个侧妃?没有旁的姬妾,后宅争斗,几时休过,你还想过清净日子,想得美?”
月娥扭动身子,佯作赌气,半是撒娇,“男人的心思在我身上,有多少妾又有何妨,男人的心思不在我身上,不纳妾也还不是一样日子过得不舒心,母亲嫁给父亲,秦家当年倒是寒门小户,又怎么样,父亲还不是照应纳妾,母亲这些年日子就舒心了,好过了,但凡什么事没有绝对,与其像母亲空守这些年,还不如趁着年轻享富贵日子,倒好过母亲这样活法。”
“住口,你为人女的,说的是什么话,竟敢当着母亲的面,编排你父亲,拐着弯的数落你父亲。”季氏半是含酸,半是生气呵斥道。
秦老爷的笑容僵住,神情尴尬,又不能绷脸训斥女儿,女儿歪缠,是为说服季氏,自己少不得忍气配合他,于是脸上讪讪的,“夫人莫责怪女儿,是为夫做得不好,不过娥儿说得也有道理,就是嫁贫寒人家,相公一旦出息了,还不是一样纳妾蓄婢,男人喜新厌旧,不在高门不高门。”
季氏态度和缓,叹口气,“娥儿嫁门当户对,好歹也是正妻,这是做妾,我不答应。”
月娥反驳,“富人妾也强似穷人妻,再说,女儿即便是委屈点,也值得,王爷庶出子女,也比平头百姓尊贵,毕竟皇家血统。”
季氏不禁狐疑,娥儿这孩子出身不一般,为何执意与富贵荣华,难道她真的是……”
季氏毕竟见识有限,又有块心病,低头思想,月娥察言观色,知道母亲态度已松动,故意撅嘴,“母亲若不答应,女儿终生不嫁人,留在家里陪母亲,女儿说到做到,母亲若嫌女儿累赘,女儿剪了头发,当姑子去,就静心了。”
说吧,伸手抓起炕上针线笸箩里的剪刀,就要往头上比量,秦老爷故作慌张,“快拦下她。”
唬得季氏忙一把夺下,恨得使劲捶她两下,叹声,“既然你父女都愿意,我说不过你们,就由着你去吧。”
说吧,手指用力点点月娥额头,“不过将来不许埋怨娘,别说娘没拦着你。”
话是这样说,终究还不是不放心,对秦老爷道:“娥儿去王府这事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京城人生地疏,身边没个亲人。”
秦老爷开解道:“我寻摸在京城买几间铺子,等你生产后,打算举家搬到京城去,这样你大可放心。”
秦老爷边说边瞅瞅女儿,女儿的演技逼真,思维缜密,知道从哪里入手说服季氏,抓住季氏弱点,女儿跟自己提的四个条件,也是抓住他急于求成的心态,软硬兼施,谈判桌上,几乎没有筹码情况下,谈下最大利益,就凭着这点,他认定女儿是块可造之材,因此,他说出搬去京城的话,不是敷衍季氏,是真有这个打算,如果可能为女儿做个援手,毕竟女儿与秦家休戚相关,王府宅门深,可他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些年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拿银子办不了的事,但是最终还是取决女儿自身,能帮到她的,最主要的还是她自己。
父女各怀心思,
季氏缓和脸色,一家三口,商量月娥进王府的事。
季氏被迫答应女儿,心里却不舒坦,秦老爷心明镜似的,为讨好妻子,把陶氏搬出秦府的事告诉她,并许诺说,“我这些年在外,挣了些钱,都放在陶氏屋里,陶氏掌管,除了留出慧姝嫁妆,和天佑俩兄弟娶妻所需的银钱,都归你掌管,即使我早你先走,善待陶氏母子,我深信你能做到,另外,陶氏一房每月的月钱,还是从秦府出,日后一应所需,按妾身份供给,族谱你一个嫡妻,其他同妾,一般无二。”
季氏听了这番话,感动得泪光莹莹,又惭愧道:“妾身的性情老爷是知道的,日后陶氏生的三个子女,妾身权当亲生看待,不枉老爷相信妾身,只是,妾身没为老爷诞下嫡子,实在是有愧秦家列祖列宗,万一肚子里是女婴,岂不是辜负老爷一片厚爱。”
秦老爷听季氏的话得体,心中满意,季氏厚道,说到就能做到,对陶氏母子他也大可放心,搂住季氏,安抚道:“夫人肚子里若是女,你从庶子中挑一个养在膝下,到老了也有靠,这个取决夫人的心意,不用太过内疚。”
季氏含泪笑了,依偎着秦老爷,小声道:“妾身这一生得嫁老爷,年轻时独守空房,从没后悔过。”
男人这一生被一个痴情的女子眷恋,自尊心莫大的满足,秦老爷周身一热,身下火苗窜起,夫妻亲热,小心云雨一番。
秦老爷不愧办事精干,短短五六日,就把月娥说的打听明白,月娥看秦老爷给她誊写纸上的内容。
秦老爷又解说道:“简王是先帝十三子,先帝十几个儿子,就当今和简王是一母同袍,为太后所出,简王年前大婚,娶的是当朝许皇后亲妹,也是武平侯、镇北将军的妹子,国舅武平侯许章,战功赫赫,为皇上宠信,皇帝对许家一门格外厚待,钦赐许章之妹为简王妃。”
秦老爷停顿一下,脸色有点沉重,“国舅许章,据说为人低调,常年在外带兵打仗,将士多拥戴他,可就是……”
秦老爷想想该怎么说,月娥道;“事已至此,就我父女二人爹爹但实话说不妨。”
“就是许侯之妹,将门之女,骄纵跋扈,至今未选立侧妃,足见此女道行,简王和王妃同为皇室至亲,半斤八两,简王为人倒也尊礼守法,就是一点,好女色,简王势大,下级官员,不乏讨好巴结之辈,听说简王府姬妾成群。”
秦老爷说到这里,瞅瞅女儿,月娥面色如水平淡无波,像是听别人事,这男人好坏与己无关。
秦老爷接着说,“先皇后已逝,许皇后是继后,虽说不算得宠,但皇上看在许家功勋份上,许后又为人颇贤惠,帝对皇后颇敬重,许后无子,只有一位公主,太子是先皇后所出。”
关于简王的情况就说完了,秦老爷指着月娥手里的纸张,“这是上元县选送的其她三个女子,信息都写在上面。”
月娥道;“女儿拿回去,仔细看。”
秦府短短一月,陶氏母子搬出,月芸出嫁,月娥收拾行囊,准备赴京。
秦府一下子空了许多,季氏省心不少,安心养胎,惦记月娥,母女即将分离,时不时的心酸哭上一场,月娥下死力劝说,方好转。
立冬,上元县官道驶过四架马车,第二乘马车一只素手掀开毡帘子一角,月娥偏头,望着熟悉的街道,惆怅。
“姑娘,别看了,徒增伤心。”云珠体贴地道。
“姑娘,老奴方才看见后头乘轿子坐的那位梅姑娘像是手捆着塞进轿子里,前面那位韩姑娘看着倒是挺乐意,紧后面的车子里的唐姑娘好像也不大高兴,估摸心里不乐意。”说话的是她奶娘姚妈,月娥本意是不要她跟来,安排姚妈留在秦府,享清福,可这老婆子非要跟来,大体是不放心姑娘。
月娥心想,“姚妈有年纪,阅历深,能看出些事,带上她对自己有好处,就是苦了姚妈,京城山高水远,一路颠簸,到王府不知是什么局面,若有什么差池,愧对她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