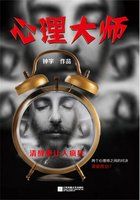吉丫:“西弟小漾也不知哭了多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哭得这么痛快。因为受这一顿暴打的惊吓,那些猪也安静了许多。于是西弟小漾就一直靠在小耳门上坐着,死了似的。
“黄昏,她在楼上的风口站着:‘改变我命运的信,你在哪里?快给我指引——’下面秋水塘边又发生了争吵,是两个大男人的争吵。起初还是很正常的争吵,很理性的,没有骂人,但不知是谁先开了个头,双方都很大声地叫骂起来,一个上前,一个被家人拉着向后,然后是另外一个上前,另外一个被家人拉着向后。但无论是谁向前,都捧着自己的生殖器的部位叫嚣着做着猥亵的动作,点名骂着对方的妻女,似乎不把对方家中的老小女性奸污个遍誓不为人。而他的那些家人,那些女人,除了气愤耻辱地阴沉着脸,又能怎么样?
“‘为什么受糟蹋受侮辱的总是女性?为什么我要是女人,是人?’
“气愤灰心之余,她认为整个人类都是肮脏龌龊、丑陋无比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逃避性,既然性在人们的诅咒之下是那样不堪入耳、低级下流,那么谁又是干净的呢?谁不是他的父亲母亲生?可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只诅咒的是女人,性成了男人高高在上耀武扬威恃强凌弱的武器,却成了女人不可改变的悲哀耻辱的象征。这是怎样不对等的一种关系。如果她的潜意识不受到干扰,她本以为性是两个相爱的男女之间最和谐愉悦的事。可是现在,没有什么是美好的,一切都变成了耻辱,她只有逃离这种耻辱,除此之外,没有退路。”
欧阳建辉:“这样的争吵,在中国市井农村,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叫骂,在大小男人或男女之间时时都有。女孩子从小就知道骂不过男孩子,男孩子从小就知道骂什么样的语句最伤害人,就连女性骂女性也是,就如西弟小漾的母亲大声地诅咒西弟小漾时。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却不能和别人一样接受和适应这样的粗鲁,将会很痛苦,西弟小漾和我以及许多的文化之人就是。可是,和西弟小漾相比,幸运的是我不是女人,我有一个非常文明和睦的家庭,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当然也还有一个好的父亲,在她的带领下我们自觉抵制了低级粗俗下流的恶习,也不惧怕黑势力。可是西弟小漾就不一样了,她就像是一朵娇嫩的白莲,错生了家庭,错生了环境。从小到大,她受过多少伤害啊,外面人对她的伤害,她自己母亲对她的伤害。不管她如何抵制,耻辱对她的印记都是那么深,她无法忘记也无法改变。这就是她逃离的原因。”
吉丫:“第二天早上,很早,她就听到了邮差送邮的丁零声。她接过邮件一看,是她姨表哥的信!她拆开信来看时两只手都是发抖的,她知道决定她命运的信件到了,她就要离开这儿了。果然,她把那么大的一个信封拆开来看,里面什么都有:毕业证书、介绍信,还有她姨表哥的信。她的母亲沈惠娘问她是什么东西,她说:‘这是我要去贵州支教的证件。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
“沈惠娘愣了愣,什么也没有说。她知道这是命里注定的,西弟小漾就要离开这儿了,她早有预感,只是她并不明确,所以她早一段时间还那么暴躁不安地折磨她,昨天还那样地打骂她。‘难道是我也希望她出去,不再影响自己的声名?’她疑惑地问自己。但是不管她是否希望她出去,西弟小漾都已经认定她和她没有什么关系了,她要去哪儿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沈惠娘现在唯一害怕的就是她出去了后再也不回来。她想和西弟小漾好好谈谈,可是西弟小漾根本不愿意和她谈,她离开了,去了自己的房间。
“西弟小漾一整天基本上都是沉默的。在这离开的最后一天,她想得最多的是你。下午,她口袋里揣上你给她的那把山&平原之家的钥匙,借口找猪菜,绕狮子山脚下的溪流一圈到了山&平原之家——你所称之为你们共同的家的庄园里。她在后面果树下的菜园子里找了一些猪菜,然后就拿钥匙开了山&平原之家的大门,再虚掩上,环视一下大厅四周,上了楼。她站在过道尽头的窗户,望着远处的溪流,想起了你说过的话:‘我要亲眼看到深圳的那些高楼大厦有多少是用我烧制的红砖砌成,然后等发展到一定程度,我再改行做房地产,用最后一批砖在我后来不断扩充的原砖瓦厂的地域上建起一栋栋花园别墅式楼房。’她知道你说的不是梦,你很快就会实现,因为她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成功者的素质,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她认为,虽然你们彼此相爱,但实际你并不需要她,因为从某种比较现实的作用和意义来看,她并不适合你,或者你并不适合她,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她坐在你们共同睡过的那张床上,仔细分析你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为今天终于拥有到了你而感到心满意足,就好像是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大任务,虽然这任务我曾经那么不确定过。’认为你们是上辈子牵挂着,这辈子还惦记着,你要借这种方式还给她。
“末了,在她要离开的时候,她说:‘建辉哥,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你有你的路,我也有我的路。你的路是在蓬勃发展的城市,你要亲眼看着那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我的路是在艰难曲折的乡村,我不知道我是为什么,但我知道那是我一定要走的路……’
她环顾四看,用她手里的钥匙在前面窗户旁的墙上刻下:‘如果可以,我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够回到这里。’”
欧阳建辉:用手指了指前面窗户下的那几个字,说:“这几个字,在西弟小漾刚离开的时候,就被我母亲发现了,因为她看到西弟小漾进入我的庄园,而且奇怪的是她发现她竟然有我的钥匙。她一切都明白了,知道我早一段时间回来就是为了和她在一起。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她离开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到这里审视这个房间时就发现了西弟小漾留在墙上的这几个字。除了我、我的母亲,谁都以为这几个字是我自己刻上去的,就连我的妻子和孩子也是。我至今也记得我第一次带我的妻子和孩子参观这里时,我六岁的孩子说:‘爸,爸,这里有几个字!’然后我妻子说:‘这是你爸爸刻下的,说他希望他以后死的时候能够回到这里。’我点了点头,说:‘是。’”
吉丫:“黎明前的黑夜,她再一次喊着:‘建辉哥,再见了!’然后天亮时就收拾好了东西下楼,她的母亲慌里慌张地,说:‘西弟小漾,你等一会儿——’然后不由分说往外面跑去。”
欧阳建辉:“她是跑去向我的母亲借钱。四弟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说:‘西弟小漾要走了,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西弟小漾要走。那天早晨,西弟小漾的母亲跑来向我们借钱,说西弟小漾要一个人去贵州支教。我们看到沈惠娘在后面追赶着,把钱递给她,然后大叫着哭了起来,说:“西弟小漾啊,我的女儿,我打了你、骂了你,你千万不要记恨我啊!你知道的,你母亲这么多年不容易,一个人拉扯你仨孩子。你出去后千万不要忘了我,千万不要把我丢下不管!”好像生怕她以后在外面发达了不认她……’”
吉丫:“西弟小漾在水塘镇坐上去濂溪县的汽车,到濂溪县后又坐上去永州市的汽车。虽然一路都在晕车,但到底没让自己吐,也没让自己不省人事地昏睡过去。下车后,她买好票,不敢去住旅社,和那些外出打工的民工一起在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确信自己没错后,她随拥挤的人群挤上去贵阳和昆明的火车,头脑里闹哄哄的,仿佛现在的自己已不是自己。
“火车上的气味很不好闻,到处都是人,各种各样的行李包裹吃的丢的食品垃圾。因为没有座位,累极了的人们随便在地上坐着躺着就睡着了,有些甚至让幼小的孩子睡到别人座位的下面。西弟小漾本以为会比在汽车上好一些,没想到更糟糕。开始她被挤到过道的中间,但是坐在过道中间的人说:‘你能不能站过去一点?’于是她又被挤到过道的旁边。因为站立不稳和实在难受,她把头靠在一个人的后座上休息。这样,也不知浑浑噩噩站了多长时间,直到有人下车了,她才得以挤坐到过道的中间。但是坐在过道中间也不是什么好事,总有人喊让路,总有餐车推过。困极了的她,一动就恶心想吐极了的她心里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下车,什么时候才能舒舒服服地睡下?’仿佛这趟车要把她带往的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地方,而且永远不会天亮。
“那时候,西弟小漾唯一的感觉就是:坐在这辆车上的不是人,没有人的待遇,而是被德国兵押往集中营的犹太人。一路上她吃不下任何东西,一点点体力都在这无休止的运动中消耗殆尽。她想象那些在毒气室里被窒息致死的尸体,仿佛车到尽头,她也将这样被抬出去。不过就在她以为此行永无尽头,她就要被窒息在这闷罐子车里的时候,她听到一个声音:‘平铺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下车。’
“她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到了,睁开眼睛勉强站起来时眼睛因为受不了光线的刺痛流下两行泪水。不过就是这两行泪水又使她活了过来。她似乎清醒和振作了许多,和所有那些成功抵达目的地的人,下车,跨过铁轨,然后又踏上十多级的台阶。面前是一个草坪,低洼处有一座小山,最后一抹夕阳刚好透过小山照在晚归的人的身上,一条水泥路通向不远处就是人居住的平铺化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