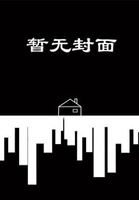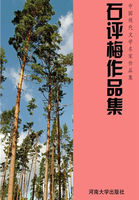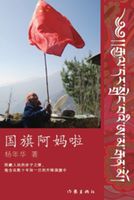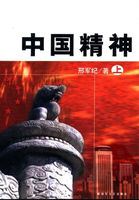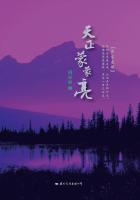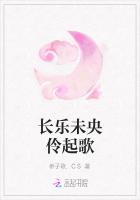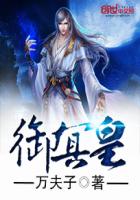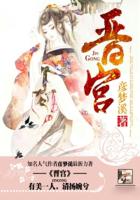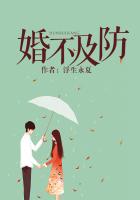五十六、首都之繁华
这次到北京,最令我有感触的是,北京与外地城市太不一样了。
当时北京被国人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神圣得不得了。那么,当时的北京,“革命”气氛是否比外地更浓呢?在“文革”的头两三年,可以这么说,但到了1972年再看,气氛上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
那时的穷乡僻壤,土墙上都写满了“革命”标语,大喇叭也一天三遍地播社论,北京不见得更“革命”。
当时北京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首先是物质极大丰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糕点、饼干,是不要糕点票的,有钱有粮票随便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城市,奢侈生活不容易表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过年过节能买几斤水果糖、奶油糖,给孩子或客人享用。此外,隔三差五的买半斤糕点,给小孩解解馋,这就是奢侈了。
能享用这些的,大概仅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平民还是舍不得。在北京以外的大部分“外省”,好糖果基本没有,只有劣质的水果糖,黄黄的一个硬块,包装糖纸很低劣。糕点也很粗糙。但在北京,大商店的副食专柜琳琅满目,各色糖果要让小孩子发疯。糕点也都很精美,闻所未闻。
姥姥有点儿钱,我带她从良乡进了两趟城,她也很激动,“血拼”了一通,从食品到日用品,每天购物都在100元左右,堪称空前绝后地奢侈。
她听说四川物资供应紧张,吃嘛嘛没有,就想多买些东西给孙儿孙女。
不说别的,就北京的汽水和面包来说,就与外省大不相同。
汽水,如今市场上没这玩意儿了,当年那是高等饮料,水里掺了碳酸汽,有小泡泡的,喝起来微辣。北京有名的冰镇汽水,牌子叫“北冰洋”汽水,加了橙汁(也可能是黄色颜料),极为有名。住在外省市的人,就只配喝无色的糖精汽水了。
北京的面包也堪称一绝,尤以长方形的“水果面包”为最佳,口感蓬蓬的,里面有果脯碎粒。包装是彩印油纸,图案之诱惑,让你想不买都不行。这样的面包,在外地休想看到,我们那儿的面包,20年一贯制,圆形的,吃起来发酸,包装是一个白纸口袋,上面用单色的红色印着一个戴斗笠的老农,抱着一捆麦子,这图案设计分明还是解放初的。
别小看汽水和面包这两样东西,一般人家,还真舍不得享用,只有小孩子郊游时,家里才狠狠心给孩子买。那时候,形容“资产阶级生活”,就说“天天喝汽水、吃面包”。这个吃法,要是搁到现在,那纯粹就是虐待了,关塔那摩的囚犯也会抗议的。
解放初期的时候,商店里有卖铁筒饼干的,质量不错,到我们懂事时,这东西全面绝迹。这次在北京也看到了有卖的,真馋人。那时候,我们那儿的饼干,也就两种,一种是“动物饼干”,把饼干压制成小动物形状,硬得能咯掉牙,啥滋味儿没有。我后来上大学时,天天早餐食堂还吃这玩意儿,外加一大碗“玉米面糊涂”玉米面熬的稀粥),寡淡无味。把我们恨得,立马想革食堂管理员的命。
另外一种就是奶油饼干。听名字好听,其实一点儿奶油没有,就是面里加了增白剂,烤得松软一点儿,也是啥滋味儿没有。
我那时在北京百货大楼里转晕了,好比刘姥姥进了法国“老佛爷”的商店。
那时候,我国人民的总数不多,也就7个亿,乡下人比例又大,再加上知青下乡,平时上班时间,城里大街上看不到几个人。可是在北京的闹市,永远是熙熙攘攘,也不知道“革命年代”里怎会有这么多闲人,还这么“趁钱”富裕)?
北京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女人太漂亮。那一年我20岁,已经很懂得审美,平时在农村,看不到什么像样的秀色,就是城里,美女也不多,适龄的都下乡锄大地去了。这次到北京一看,敢情全中国的美女,都在北京呀!
北京的美女,素质明显比外地高,也许是文艺团体多,真有美如天仙的,看得我晕晕乎乎。
那时节女人不兴化妆,拼的是本色,美女都是货真价实的。
我当时那身行头,还有举止神态,一看就是外地人,看见美女,真是自卑,又忍不住想看,估计在人家眼里没少出丑。
北京令我激动,但只是令那时的我激动。当年中国大都市究竟什么样儿?光凭记忆还真不行,去年我买了一张碟,是意大利名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这才看见了真景象。安东尼奥尼是左派导演,片子的拍摄地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又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不大可能丑化。
当年的情景,现在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无论北京还是上海,满街的人都表情麻木,除了军人,没有一个人是穿着得体的,衣服不是长就是短。街景之简陋、寒酸,不比现在的喀布尔强多少。安东尼奥尼在那时被我们的媒体批了个臭够,说他是丑化了“文革”,可是,秃头上的虱子就这样,你让他老人家怎么美化呢?
这幅暗淡的景象,就是我过去心目中的繁华北京吗?要不是摆在眼前的纪实画面,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出了错儿。
北京尚且如此,那我们那旮旯呢?
——真不敢细想啊!
五十七、《卖花姑娘》重磅催泪
在良乡,我还遇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就是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的公映。
对这部影片,民间早有传闻,北京最早上映,我沾了个光。这部片子,跟我们的《白毛女》差不多,是讲述旧社会穷人命运的苦情戏,不过《卖花姑娘》是先进的彩色片,女主角漂亮,音乐也好听,所以在中国甚为轰动。
放映是在良乡的一个广场,露天电影,不要票。满场的人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以至于民间传说的“要带着手绢去看”成了真事儿。
影片里的富人,真是极端的恶,穷人是极端的苦。看到动情处,无人不动容,全场抽咽声一片。中国的影片,被压迫群众不可能像朝鲜电影里那样哭哭啼啼的,因此也就没有那种感人的力量。
电影插曲也是一流的,非常抒情,听过就不忘。在《卖花姑娘》还没有公映的地方,人们早就在传唱了。
《卖花姑娘》在中国大获成功,全社会轰动,有如后来我们的电视剧《渴望》在朝鲜。
这电影,片头有一条说明,说是根据“伟大领袖”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时期创作的剧本改编的。那么,金日成早年从事秘密工作的地方,据说就在我们县的一个村庄。他从吉林毓文中学毕业后,在我们县那里做过一段乡村教师,看来《卖花姑娘》就是他那一时期的业余创作。
几十年后,我还知道了,原来电影《卖花姑娘》是金正日同志导演的,怪不得!
《卖花姑娘》引起的轰动,无疑是给了当时的“帮文艺”一个冲击。相比之下,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太过苍白了,傻瓜也能区别出两者的高下。
“卖花呦,卖花呦……”这个婉转的旋律,我从北京一路听人唱到四川。
到四川后,我见到当地的知青,在聊天中,必有一个话题,就是他们问我《卖花姑娘》究竟怎样。
我不吝赞美之词,特别警告女孩子:去看,一定要有哭个稀里哗啦的心理准备。
等我后来返回东北,在《参考消息》上看见《卖花姑娘》在维也纳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得了一个金奖。我大感惊奇,特别跑去问王兄:资产阶级也喜欢《卖花姑娘》?”
王兄沉吟一会儿,说:人性,都是相通的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
五十八、有钱就是大爷
这一节,我来专门讲讲那时候农民和一般民众的价值观。
北京之行,我因为看到了物质极大丰富而深受触动(1967年武斗之后就没见过这么多商品),多少动摇了我原来的观念。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主流意识形态就在不断宣传“贫穷是美德”,我是在那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那时候的少年,不怕家贫,就怕露富。我上了初中后,个子蹿得很高,父亲的一些旧衣服可以穿了,从此就很少穿新衣服,青少年时期穿的几件新衣服,是有数的。
那时候,穿上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心里就很舒坦,而一旦穿上新衣服,就会觉得浑身别扭。
时代风气如此,谁也不能免俗。我上初中后,中午不回家,要自己带饭去学校,学校有锅炉房,可以热饭。那时的盒饭,用的是自家的铝饭盒,装的也是自家做的饭。别的同学都带高粱米饭、窝窝头什么的,我家是南方人,从1963年起就不吃粗粮了,不可能为了我的一顿午饭,专做一锅高粱米呀。可是,假如天天带大米饭到学校去,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怎么那么趁钱!
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姥姥就提前一天给我买好两个豆沙馅包,装在饭盒里,当我的午餐。
但这豆沙包也是细粮,是白面的,而且还是买的,这不是更奢侈!没过几天,我就感受到了来自同学的压力——“非我族类”吧。于是回家抗议说,“这么带饭可不行!”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琢磨出来,我的中学同班同学,起码有三分之二是家庭条件很好的,不说吃山珍海味吧,每天一个小炒那是没问题的,可是一掀他们的饭盒盖,都是一模一样的贫苦相。
我家里没招儿,只好专门给我弄粗粮,还特别去买了东北的咸菜大疙瘩,切成丝儿给我装上,看着有点儿像穷人的饭食了,这才带上。
讲究清贫,是对的,但这样子用心也未免太矫情了。
我受此事的刺激,一直对富裕生活很警觉。
下乡后,我更有理由穿父亲的旧衣服了,直到穿得补丁摞补丁。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儿,一位中年农民忽然对我说:你把你那件破衣服给我扔了去!”
我一愣,马上明白他是说我节俭得太过分。农民子弟还每年一套崭新的黑棉袄呢,我这副样子,不是装穷?
渐渐地,我观察,原来农民没有不嫌贫爱富的,人人都渴慕富人的生活。
以赤贫为美德,原来并不是穷人的观念。
从我记事那时候起,无论是电影还是连环画,里面讲的民间故事,都在抨击富人,“为富不仁”成为一个定理。我也在很长一个时间内,以为在历史上,民间的观念就是这样。直到1992年,要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了,才看到报刊上说,从一份出土的草莎纸文物上看,5000年前的埃及人就知道“有钱才是大爷”。那份文献,是一位不知名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他谆谆教导说:做人一定要有钱,否则会很可怜。
原来,这才是没经过文人加工的民间故事。
我在那个年代,偶尔也有享受奢侈品的时候。一次,母亲给我买了一双比较好的翻毛棉皮鞋,浅黄色的,很耀眼。我穿着进城,抽空到澡堂子洗澡,一位中年师傅看见我的鞋,很惊讶,问我:这得20块钱一双吧?”
我说:是。”
他会心地对我点点头,无限尊敬的样子。
原来民间也是爱财的。
我这次送姥姥回四川,我妈知道我这一趟要穿州过府,穿着劳动的衣服不合适,就给我做了一件灰蓝色制服,好歹充个城里人。这算是我记忆中比较像样子的一件衣服了。是正牌中山装,衣服口袋吊在外面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