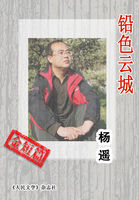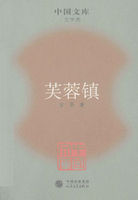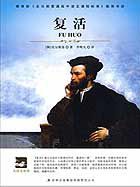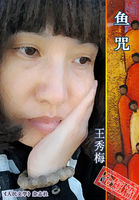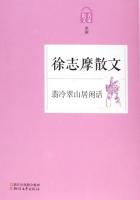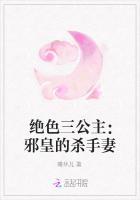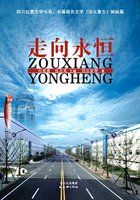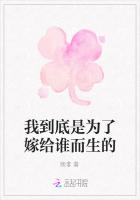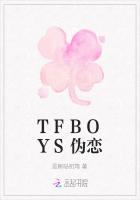太平村穷得可怜,村风却好得可以。所谓村风,无非是指村里人的民情民性民风之类,用句眼下的时髦话,也就是文明的程度。
太平村人善良、厚道、淳朴、节俭、友爱、和睦······总之,不说天下,至少中国祖传所有的美德,仿佛全让他们给“承包”了。
这好村风确实历史悠久。老辈人说,从前清到民国,村里就没出过一个歹人。解放后多次斗争、运动,这儿也均太平无事。即便“文革”,外乡几乎村村都闹造反,太平村却无甚波澜。到后来,村里最大的当权派实在过意不去,主动挨家挨户求“批判”,可家家都说:
“支书,你不让我做太平村人还是咋?”
直到多年之后,地区报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想写一篇在“文革”中和林江集团斗争的典型,但东调西查,终觉得难以下笔,因为这典型实在太不“典型”了。于是只得作罢。
田分给各家种以后,不少地方常发生抢水争化肥之类的纠纷,也免不了会有赌博之类的邪气。太平村却仍安之若素。即使有些小难题,譬如逢年过节,上面为了表彰这里的村风,支援一些物品,人人心里都想要,多要,但最后总是平分或抓阄儿,皆大喜欢。倘有哪个刁佞之徒,做出有损村风的事来,定然会引起全村共讨之的。近朱者赤,在众多硬身板的正直人中间,驼背也被夹直了腰。
于是,就像村前溪滩的沙石越积越高一样,村里的风气也越来越好。乡里(以前是公社)年年评文明村(以前是文明大队),总忘不了太平村。难怪外村有人说它是“文明专业村”。
为此,村里人尤其是老一辈人便引以自豪,时时事事,总不忘把“村风”两字挂在嘴上。干部们把每年得来的奖状挂得高高的,擦得亮亮的。村民们也心里甜甜的。虽然穷,但大家都互相勉励或自我鼓励:
“穷?村风总富嘛!”
可惜的是近几年,这村风渐渐地显出颓败的端倪来。先是村里有些年轻人,偶尔间也会明里暗里发几句对现实不满的牢骚,但终究被他们的父亲,或者他们父亲的父亲管教住了;接着是前些年极少数被村里人一致认为是“硬被夹直腰”的“不同村见者”,也渐渐地歪起身子来,背地里谋划着想去山外干有损村风的勾当,但也到底慑于村风的威力,未敢付诸行动。直到陈书礼家来了个外乡女婿,太平村才真正显得不太平起来。
陈书礼在村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在人们的目光中,他是个“归村华侨”。作为村里惟一的地主的独子,十四岁时候,乃父送他到城里读书,后来干脆在那里做学徒。此事曾引起村人极大的惊诧。因为在此之前,他那地主老子曾先后介绍村里几个最穷人家的子弟,包括后来做了几十年村最高领导,直至现在仍一身兼村长书记两职的根土在内,到城里去做学徒,结果终于没得逞,有的中途逃回,有的干脆硬顶住没去。庄稼人再穷也不能到外面去“吃人家饭”,受城里人欺侮。可后来,陈书礼居然去了!这便奇了,甚至引起村人的愤懑:太平村首富的公子居然也去“吃人家饭”!岂不是煞了村里的名声?直到解放,听土改同志偶然间说,幸亏陈书礼出去,不然也够评上地主,而且话语中还有几句佩服老地主有点远见的意思。但村人们却不以为然。至少,若是陈书礼留在村里,地主家土改后也可以多一个人头,多留三亩保留地呐!
至于后来的事实,更证明有远见的还是村人们。
陈书礼解放后一直在城里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本来倒也安生。不料“清阶”时期,他作为“逃亡地主”被清了出来,很是斗了一阵。妻子病死,两个大点的子女去了边疆,他和小女儿被遣送回老家。这可吓坏了他。城里尚且不讲政策,到了家乡,落在那些以前深受其父剥削压迫的人手里,不被整死才怪!哪知村里人非但没动他一根毫毛,还把父女俩安顿得好好的。全体村干部还登门看望,亲切慰问之后,支书根土说:
“就怪你爹!好端端太平村人不做,让你去城里吃苦头。城里我也去过二十天,那味道我也尝过!”
热话暖心。陈书礼差点没流出泪来。到底是家乡人好,掌握政策。当下便涕泪满面地说了一番感激话,且联系其父,说当年他老子剥削村里人,今日乡亲们还这么好待他。可那根土听了又说:
“地主咋啦?家抄了,地分了,老地主死了,还要把你这小地主逼死不成?那还算是太平村人?”
陈书礼听了心里冷了半截。原来他们并非掌握政策,而是也把我当做“小地主”?但又待我这么好!这是咋回事?过后又想:管他们把我看做谁,没亏待我总是好嘛!
以后的日子也确实过得安耽。陈书礼活儿都不用干,只给村里记工分。所以他从心底里感激太平村人,也从心底里绝了回城之念,只想在这太太平平的太平村做个太太平平的太平人。直到一年多后厂里落实政策,允许他回去,他也毫不犹豫,主动要求退职,留在村里。他更想为村里出点力,以报答村里人对自己落难时的不弃之恩······
谁料就因为此,却引出麻烦事来。弄得他愧悔不巳,且还得闷在心里,对任何人都说不出,也不想说包括对自己的女儿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