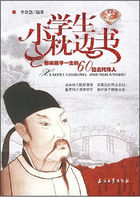雷伯莱希特真想在千岛之城威尼斯城停留一下,关于这座城市,他不知读过多少书。他想看到威尼斯公爵,据说,从国家角度和衣着方面看,他是个国王;从权力上看,他是个议员;在城里,他是个囚犯;出了威尼斯,他就是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然而夏天已经过去,城里没有什么盛大的活动要举行了——譬如公爵与亚得里亚海结婚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公爵要乘上一条豪华壮观的大船向海里驶上一段,从他座位的一个开口处往海里投一枚金戒指,同时嘴里说“Desponsamus te mare,in signum veri perpetuiqueDomini”。因为鲁伊特格修士和阿尔巴尼教授都急着赶路,所以他们没有进城,而是从它西面驶过,开往离威尼斯有八个小时车程的帕多瓦。
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交通相比,在意大利的地盘上旅行意味着要冒更大的风险,邮车线路之间的连接很差,准时更谈不上,尤其是道路上隐藏着的危险:遭到路霸的袭击是家常便饭。因此,见多识广而富有旅行经验的罗马教授建议不再乘坐往来城市之间、始终被强盗团伙盯着的邮车,而是改乘商人的车继续前进——意大利的商人习惯于在旅途中带着武器装备,时刻保持警惕。
在众多重要商路交汇的帕多瓦,阿尔巴尼找到一个第二天将由两个武装骑士护卫、经佛罗伦萨去罗马的香料商。他愿意以每个人两个斯库多的车费带上这几个旅客。
鲁伊特格在本笃会位于绿谷广场的修道院过夜。这个广场很大,没有铺石头路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这里都有牲畜集市。其他几个人则在一个与修道院近在咫尺的旅馆过夜。旅馆在一个小胡同里,客人主要是商人和行旅。
雷伯莱希特和玛尔塔一起住进了二楼的一个房间,看不到什么风景——几乎伸出胳膊就能够着对面房子的墙——但至少保证他们俩单独在一起。雷伯莱希特关上房门,两人便快乐地哭着投进了对方的怀抱。此时此刻,他们卸下了几个星期以来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的紧张、痛苦和不安无定之感。
“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变好了。”雷伯莱希特断断续续地说,边说边吻遍了玛尔塔的脸,“你不用再害怕了。”
玛尔塔仰起头,闭着眼睛,享受这个为她所爱的男子的嘴唇。
“我是多么怀念这种感觉啊!”她悄声说道,脸上迟疑地掠过一丝笑意。
雷伯莱希特不知自己有多久没有看到玛尔塔这样微笑了。这期间他们经历了多少的恐惧和不安啊!他们的身体轻柔地偎依到一起,小心翼翼地,似乎需要重新习惯彼此一般,每个人都小心地、几乎是充满敬畏地摸索着对方的身体,渐渐地,那从一开始就标志着他们关系的狂野激情又回来了。
玛尔塔喘息着,雷伯莱希特将膝盖顶到她的双腿之间,两手捧住她的头颅,用舌尖爱抚着她的脖子。玛尔塔发出愉悦的轻喊,令雷伯莱希特狂喜不已。她交出自己,任由他做一切,令他急切地动手脱起她的衣裳来。他剥开情人的衣裳,就像剥开一只甜蜜的果实,露出她洁白的躯体。
她的胸脯急切地贴向他,雷伯莱希特则将舌尖贴上去。他撕扯着玛尔塔的内衣,直到她完全赤裸着站在他面前。接着他便跪到地上,将头埋进她的怀抱,像要以此忘却整个世界。缓慢地,像一棵被伐倒的树一样,玛尔塔让自己倒在地上,对坚硬的石头地面毫不在意,飞舞的手指摆弄着他裤带上的结。
他终于也赤裸着跪在玛尔塔面前了。他享受着她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要我!快!”玛尔塔低语,而雷伯莱希特根本用不着她多说。
这一夜,帕多瓦尽可以被西班牙军队攻占——玛尔塔和雷伯莱希特反正是什么都不会觉察到的。他们用前所未有的激情爱着对方,因为藏猫猫的游戏终于结束了,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令自己的感情自由奔涌了。
一直到天快亮了——至少远处已经有公鸡在啼叫了,他们才结束了他们的激情游戏。他们紧紧地攀住对方,似乎害怕失去彼此,然后便像两个孩子似的睡了短短的两个钟头。
他们醒来时是星期天的早上,而这,只有听到二十六座教堂、二十三所女子修道院和二十二所男子修道院的钟声同时敲响的人才能判断出来——帕多瓦就是有这么多的教堂和修道院。重叠在一起的钟声刚落,全城的大街小巷和广场上又响起大声的呼喊,四面八方都有人疯狂地喊着“Qui va li?Qui va li?”意思是“这是谁来了?”这句呼喊是帕多瓦的大学生的标志,他们以高傲和狂野著称,就因为这一“战斗口号”他们被人们称为“这是谁来了”一派。
他们在方济各会教堂聚齐准备上路时,鲁伊特格已经做完了晨祷和弥撒。在这个教堂里曾展示过圣安东尼奥的遗体,但并不包括舌头和下颚,这两样被认为在虔诚的祷告中有特殊的效用,所以被单独锁在法衣室里。
去佛罗伦萨的道路要穿过亚平宁山脉,对车夫的要求几乎赶得上过阿尔卑斯山时的情形。不过虽已上了年纪、显得却很年轻的香料商对这条道路很熟悉,他很有把握地引着车驶过那些陡峭山路上狭窄的弯道。
香料商说,继续赶路之前,他得在佛罗伦萨逗留一天,解决一些重要事务。几个旅客觉得和他一起赶路不错,便同他约好了第二天会齐。这很合雷伯莱希特的心意,这样他就可以和玛尔塔一起探索佛罗伦萨了。他师父卡尔瓦奇不知给他讲过多少关于这座城市的事。是的,他甚至有留在这个城市的想法,虽然还没有跟鲁伊特格说起过这个计划。因此,修士也不知道雷伯莱希特和玛尔塔到达当天就去找卡尔瓦奇了。
雷伯莱希特以为卡尔瓦奇肯定是在大教堂的建筑工棚——他还能在哪儿呢?于是,他们便从位于阿诺河岸边、离老桥不远的旅馆走了出来。骄傲的佛罗伦萨人即使在工作日也穿着华美,超过任何地方的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里布料贸易发达、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原因,毕竟也和人们的审美趣味有关。
佛罗伦萨的主教大教堂绝不会被佛罗伦萨人自己称为“大教堂”,他们称它为“鲜花圣玛利亚大教堂”。找到它并不困难,因为城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看不到它,要么是它的穹顶,要么是它的钟楼。不算上三十六厄尔高的塔尖,穹顶本身就有一百五十四厄尔高。与其相比,四方形的钟楼倒没有那么高,才一百四十四厄尔。
大教堂会让初来乍到、刚刚踏入大教堂广场的访客晕头转向。
此外,建筑本身色彩鲜艳,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教堂的单调色彩相比,它简直是五颜六色的:卡拉拉的白色大理石、玛莱马的红色大理石、普拉托地区的绿色蛇纹岩。
雷伯莱希特从大教堂的一个管理员那里得知,大教堂的建筑工棚早就解散了,他也不认识叫卡尔瓦奇的石匠,这个城市有数百个石雕艺术家呢。但如果有这么一个石匠在佛罗伦萨工作,那他就一定在市政厅那里注了册。
市政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由保皇派风格的长方形挑楼护卫着,让人觉得它在防卫能力上还要胜过匹提宫一筹。雷伯莱希特从一个长发、穿着鲜艳长袜的年轻书记员那里得知,一个名叫卡尔瓦奇的石匠师傅曾在巴托洛梅欧·阿玛纳蒂的手下工作过——后者是受委托建造政府广场上的喷泉的建筑师。没过多久,两个人就吵翻了,这之后,卡尔瓦奇就离开了佛罗伦萨。
“您说吵翻了?”雷伯莱希特笑起来,“听上去就像是他,这只老斗鸡!”
喷泉的施工地点位于大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几个石匠正在加工大理石石块,碎片像火花一样四处飞溅。他们中有一个气呼呼的老头儿,下巴上长着海神雕像式的黑色短胡子——这就是阿玛纳蒂。
对于雷伯莱希特提出的问题,这位大师不愿多说什么。直到玛尔塔走上前来说,卡尔瓦奇欠了他们钱,他们非找到他不可,阿玛纳蒂才显得好说话了一些。他将他的小圆帽向后一推,用衣袖抹抹额头,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用低沉的声音说:“卡尔瓦奇是个好石匠,甚至是个非常好的石匠,但可惜他没法儿和人共处。他比别人都强,知道的、会的比别人多。依我看,米开朗基罗还得跟他学艺呢!”说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您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玛尔塔小心地问道。
“卡尔瓦奇?我当然知道他在哪儿——他经常提起嘛。世界上所有的石匠都争着要去罗马,为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出力。”阿玛纳蒂走近雷伯莱希特,注意不让他的伙计听到他的话,“说实话,要让我在波纳罗蒂和阿玛纳蒂之间选择,我也会像他那样做的。
虽然伟大的米开朗基罗据说已经老得不行,只能拄着拐棍走路了,可他的人都拿他的每句话当福音书——除了卡尔瓦奇。他们很可能已经在吵个不停了。”
他说话的当儿,一群半大的孩子走近了工地,他们齐声喊起来:“Ammanato,Ammanato-che bel marmo hai sciupato!”
闻听此言,大师抓起一块石头,朝那群孩子甩了过去。孩子们像受惊的母鸡一样四散开去,他冲他们背后喊着:“你们这帮没教养的,对艺术一窍不通,以为海神还得像古希腊时代的样子一样呢。”说完,他往地上啐了一口。
雷伯莱希特这才发现,阿玛纳蒂在石像造型上并不遵循传统风格,他把人体拉得非同寻常的长,跟整体和谐要求的比例相比,胳膊和腿都显得太长,而脑袋却较小。
阿玛纳蒂注意到了雷伯莱希特批判的目光,用头向市政厅宫殿方向示意——那里,入口旁那座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大卫”像在夕阳中发出光来。“您看看那件艺术品吧!一个艺术家如果看过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还能有什么艺术创作呢?”
“我的上帝!”雷伯莱希特结巴起来,抓住了玛尔塔的手,“我竟不知道那原来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在这座城市里艺术品太多了!”
阿玛纳蒂咧嘴笑了起来,用夸张的轻蔑口吻答道:“那您说说,您是从哪儿来的,年轻的朋友?从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德意志熊居住的地方吗?”
雷伯莱希特尴尬地耸耸肩,玛尔塔则觉得这个佛罗伦萨人的话很不得体,便安慰一般偎依着情人,轻轻抚摸他的手。
“我到意大利来,是来学习的!”雷伯莱希特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到艺术,德国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我们那儿,艺术家仍然指靠着教会过活。我自己就在侯爵大主教那里领了十年的薪水。”
阿玛纳蒂用手指指向那座石雕说:“你要知道,这一个可不是随便的艺术品,像这喷泉似的,不过是城里众多喷泉中的一个。这就是艺术本身,是大自然的赐物。佛罗伦萨人早就不按耶稣降生的时间纪年了,而是按‘大卫’被造出来的时间。”
“那么,米开朗基罗为什么创作了这么大的一尊大卫像呢?我是说,如果人们相信圣经里的说法,大卫应该是矮个子。”
“确实如此。”阿玛纳蒂回答,“而米开朗基罗的秘密大概永远不会揭开。事实是,米开朗基罗是惟一愿意加工那块由卡拉拉运来、在大教堂的建造过程中派不上用场而白白放在那儿的大理石的艺术家。伟大的多纳泰罗,人们一向供给他长形石块,可就连他也拒绝加工这块大理石,说它没有比例,就连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不能赋予它和谐的形式。最终,羊毛纺织行会委托了米开朗基罗,让他用这块石头随便雕出个什么来,并答应两年之中每个月付他六个金古尔登……”
“对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来说,这可真算不上丰厚!”
“绝对算不上。可波纳罗蒂当时才二十六岁,在创作大卫的两年半期间,还有其他的订货要完成。再说,钱对于他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他拥有的此生此世根本用不完。这跟我们的另一位天才列奥纳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米开朗基罗说他愿意像个穷人一样生活,列奥纳多则穷尽奢华,住得像个国王。Quid nonmortalia pectora cogis auri sacra fames?”
“您不太喜欢他,阿玛纳蒂先生?”
“没人喜欢列奥纳多,米开朗基罗顶不喜欢他。他傲慢而变化无常,要求所有人跟着他的指挥棒转。现在请您原谅,我得告辞了!”
“还有一句话!”雷伯莱希特请求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从德国来的石匠在哪儿可以过得更好?在佛罗伦萨还是在罗马?”
阿玛纳蒂放下手里的凿子,用评判的目光又打量了一下陌生人,然后说:“年轻的朋友,这个城市的伟大时代过去了,就像沙漏里的沙。人人都涌向罗马,不满的农民、雇佣兵和小贵族。自称智者或艺术家的人登上舞台,推倒从前的人奉为神圣的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人在罗马生活而不是在佛罗伦萨。所以您若是问我——未来不在阿诺河边,而在台伯河畔。据说,圣彼得的建筑工棚就雇用着两千五百个劳动力。全世界虔诚的基督徒用他们买赎罪券的钱助长着历代教皇对权力的欲望。这些教皇,一位接一位地为自己修建永恒的纪念碑,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昂贵。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是属于罗马的——除非你是个新教徒。”
“上帝保佑!”雷伯莱希特装出气愤的样子喊。是向阿玛纳蒂道别的时候了。现在,对雷伯莱希特和玛尔塔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要去罗马,去那里寻找卡尔瓦奇。
三天后,也就是他们启程后的第三十七天,几个旅人抵达了罗马。人民门——罗马的北城门下,邮车、马车川流不息,排成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