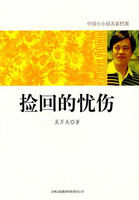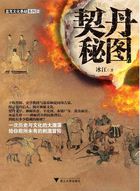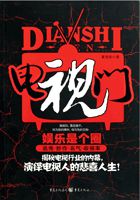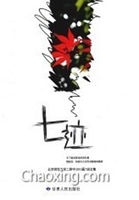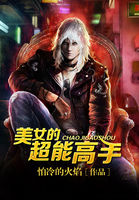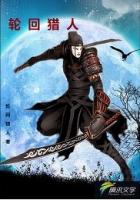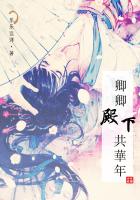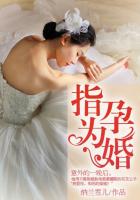1934年10月,青岛大概绝对没有现在这样气派繁华,但在文人心目中,它还是一块了不起的圣地,那里不仅有欧洲风光、异国情调,还可以自由创办刊物,允许各种追求的青年在那里栖身活命。当萧军、萧红两个来到青岛时,心中还没有明确往哪里去的意向。是在生活发生窘困后,因为朋友们的鼓动,才给鲁迅写信。想不到,这封信竟成为与一个划时代的文艺家建立忘年交的开始。
在鲁迅晚年书信中,给两萧的信是比较多的,而且每写起来都比较长,情感真挚,以诚相待。但看信的内容,多半还是在跟萧军说话。因为萧军实在是个可以交心甚至可以托付性命的人,他的火一般的热情,生命中的活力,令鲁迅感到快活起来甚至于年轻起来。所以,三天一封信,两日一封信,充实得不会空虚。
萧军是属于真有男子气的人,大约力必多也是很旺的。所以萧红一看见他,就觉得爱上了他。萧军的真人我没见过,但照片是看到的,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那是穿一件尖领的白衬衫,二分头,看起来肩膀上肌肉发达,腰很细的样子,阳刚气十足。这与许多文艺家软绵绵、病恹恹的样子大相径庭。当他第一次出现在鲁迅面前,我相信,是令他极其喜爱的。
萧军的刚性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有时近于侠客之风。在口合尔滨办《国际协报》时,收到一个女子的求援信,说将要被人卖掉。得信后,萧军与几位青年同事立即跑到事发旅馆,向老板出示记者证,然后警告说:不许虐待住在二楼那位女子,要照常供她伙食。然后又来安慰女子(萧红),要她放心住着,他们会来救她。就是这样演出了一场现代的英雄救美故事。
鲁迅逝世后,萧军哭得最伤心,直到鲁迅逝世一年后,他仍未完全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就在这时,“华蒂社”文人张春桥、马吉蜂在小报上挖苦、讽刺、嘲笑萧军,令萧军大为光火,一时性起,上门下战书,要求在徐家汇决斗。
晚上八点钟,徐家汇的菜地已经一片漆黑,在双方证人见证下,萧军与马吉蜂开始交手。萧不仅接受过军事训练,而且一直在习剑练武,马吉蜂怎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都被打翻在地。
文革中,萧军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地写作了,说话也不方便了,但在打手面前,他绝不示弱,嘴巴不说话,动动手上的拐杖,就让那些底气不足的家伙躲得老远。
牙齿落了,舌头还在,意思是,不必锋芒太露,不必过于要强。这是鲁迅到了人生的晚境,总结一生教训得出的结论。他本意并不是颓唐消沉,只是不希望年轻人也像他一样碰得遍体伤痕。他是表示一种大爱,就是对于青年的爱。
而一生追随他的萧军,却偏偏要以硬碰硬,即使舌头掉了(不能随便说话),也要留下铮铮铁骨。正因此,才能看出他不愧为鲁迅嫡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