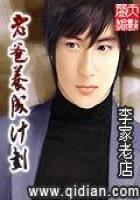她拉开抽屉,取出我的那顶鸡冠一样的红布帽和那把子弹壳做的小刀。我说:“这顶帽子取开就是一块红丝绸,送给你当一条纱巾,拴住你别跑上了岔道。”
“小刀应该属于男人。”她说。
“钥匙应该属于女人啦。”我说。
杏子不哭了。
有人敲响了大门。杏子问是谁,门外人说他是来赶羊(牧羊)的,杏子说今早不放羊了,待会再来。
今早的太阳太奇妙了,自我懂事似乎没有一天能躲过太阳出世的情景。只要太阳出来,就能欣赏或者审视到夺目的光芒。而今早初升的太阳比平时的大,比平时的柔和,隐去了往日的灿烂,波光潋滟似航行于水。如果将苍穹比作一张潮湿的纸,太阳就是蘸着水画上去的。风往什么方向吹,阳光就往什么方向染,虚洇的光里像藏了许多的未知与变幻。或出或入皆由自己去握舵了。
奥妙就在于入得进去能否出得去。
我与她商量之后,她家所有的羊和财产全归村中穷人所有。没想到劫富济贫竟如此简单与偶然。
放羊的又敲响了大门,杏子隔着门让去叫村里的人。
太阳继续渲染着那颗有光无辉的紫色球体。
杏子敞开了大门,那几只狗摇头摆尾绕着她的身前身后转。它们也像猜出了什么,隐隐地流露出一种惜别之情。
村子里的人匆匆忙忙地赶来了。他们怯气地走进大门,睃着几只狗,慢慢地走到屋檐下,看不出他们想什么心事。
放羊的在杏子的耳畔说了句什么,杏子看了一眼站在院子里的人。
“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事,我要走了,我的家产我带不走,你们给我出出主意。”杏子说。
村里人互相瞅,好像杏子说的主意,就在他们的眼睛之间。
“姑姑要走了么? 你要走你就走吧,剩下家产我给你照看着,什么时候你回来什么时候还给你。”放羊的说。他说话的口气像巴不得马上就让杏子离开。
“我的意思,我的家产还是分给大家好,都在一村住,许多事都麻烦过你们,谁一人得了去,是不合适的。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护住这份家产的。”杏子说。她说话时放羊的在她身边转腾,她停下不说时,放羊的扔掉了身上的雨毡,他像要跟谁打架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杏子。
“你们家的羊是我一手放的。”放羊的说。
“你可以多赶一些回去。”杏子说。
放羊的嘟囔着什么,从人群中往外走。
杏子没有理睬他,杏子对着大家说:“谁能拿走什么东西你们就拿走什么东西,你们拿吧。”
院子里的人们开始骚动。
放羊的向房的后面走去。他往后院里走,双臂张开,把往前面走的人拦在身后,他张开的双臂像一只力图护住小鸡的麻母鸡,他身后的人像要叼走小鸡的猫。他的嘴里磨叨着:“羊是我的,羊是东家的,羊是我的,谁往前走,我……”
他先走到了后院。
“日他妈……”放羊的在后院里骂着,院子里乱哄哄地嚷成一片。
杏子倒像轻松了,她似乎什么都不想管了,平静地观看着院子里的人。
从今早起,在我往后的日子里,就有个名叫杏子的富人家的姑娘跟一个名叫借生的穷小子去闯世界了。我看看我们的穿戴和梳妆,就像一个穷少爷拐骗了一个阔小姐准备私奔了。
杏子的身影被阳光拉斜了印在房檐下的墙壁上。面对这么浩大的一座庄院,她就像一棵大树上的枝,要想把她从这个庄院里起出来,移到别的地方去生存,她的根系总是朝着这个庄院的。就像影子物体光源相互存在的关系一样,现在杏子的影子是沉重的,自己的分量都压在她的影子上。
圈在院子里,目光略往上一眺,高高的山,就悬在空中,看得久了,山像要倒入院子。山是苍黑的,凝立在院子的上面,墙再高只不过是聪明人吓唬聪明人的一种障眼法而已。
天空飘来一朵白云,像马。
我看云走心急呢,看不走的杏子也心急呢。
云走了杏子不走,她的大一旦回来,我便是拴在槽头上的马了。
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才能使一切变得活起来。走是愉快的,走是艰难的。人一辈子的光阴是在走动中得到的,又是在走动中抛弃的。最终只有信念跟随自己到老到死而不分离,信念是人一生最有价值的追求。就像影子要追逐光一样。
可是,我们不能“走吧”了,杏子的大他早晨回来啦。
杏子爹牵了一匹枣红马,背了一杆长筒土枪,站到院中的时候,村邻们谁也没有拿杏子分给他们的东西,悄然地离去了。望着这个矮汉和那匹大马,我看杏子,杏子很吃惊,我卡住了枪柄。杏子爹若无其事,这一切像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笑容满面。
杏子走在前面,我跟在杏子的后面。杏子紧走几步,我停住未动。杏子扑进矮汉的怀里,我依然停往未动,我的手松开了枪柄。杏子在她大的怀里狂嚎起来。
“是不是这个小杂种糟蹋了你?”矮汉说。他的双手扳住杏子的双肩,使杏子软溜溜的身子挺立起来。他斜背着的土枪枪管显得那般长。他满脸虽然充满了笑意,但在每一条笑纹中都潜藏着惟我独尊无所畏惧的傲气,谁遇见谁都会胆怯。我的手又攥住了枪柄。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是个英雄。”杏子说。
“那你哭啥事情?”
我的手又松开了枪柄。
“昨夜来了一伙土匪。”
我的眼神友善地瞟过去。
“土匪? 土匪把我女儿吓着啦,别哭,爹回来你就不怕啦。”
我看着矮汉的大巴掌抚摸着杏子的头发。
“爹,你是怎么回来的?”
我看出询问的眼光,掠过杏子的肩膀与矮汉的眼光相遇的一瞬我面对着阳光他面对着我。
“轻车熟路,该怎么回就怎么回。”
我的目光掠过他们父女在院墙上面流浪。
“土匪说把你捉进山啦。”
我的目光才落到矮汉的脸面上。
“土匪连我的汗毛也逮不住。”
我的目光又移向他身后的马。
“杏子,把爹的马拴了。”他说。他把手中牵着的马缰往马的脖子上一撂,杏子绕过父亲牵到了马缰,枣红马跟着她走。
杏子爹扫视了一眼乱麻麻的院子,他说:“以为我死了,就想分家产了?”他说话时像对着杏子说又像对着村人说又像给我说。
“是我叫他们来拿的。”杏子说。她往槽头上系着马缰绳。
“你想跟他走吗?”杏子爹说。他凶狠地盯了我一眼,又凶狠地去盯杏子。
“你回来我就不走了。”杏子说,“爹回来我就不走了,爹回来了。”
“知道爹回来了就好,爹怎么能回不来呢,爹走多远都想着回来的。”杏子爹说。他的心事像没有了。
我的目光从我的脚面举起来,矮汉微笑着走向我。我正思考着用怎样的礼节来见他,他头顶的影子已触到了我的膝盖。我看见的堡门的轮廓已被他很宽的身子遮堵住了。
从他右肩上斜长上去的枪管的影子阴在我的左眼上,于是,我的左眼轻松地睁着,右眼极不舒服地鼓着劲。他伸出的一只手已将我的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是伸了出去收了回来又伸出去才被他握住的。我闻见他的身上有一股既强烈又醇香的酒气。
“娃娃,小伙,男人,我儿。”他说。他是一个热心肠好心肠的老头。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说。我心存的惊恐消失。
“谢啥谢啥,睡好了吗吃好了吗杏子没有欺负你吧?”
他说。他的手拍拍我的肩膀拍拍我的头又拍拍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手就停在我的肩膀上。
“我的命是你送给我的。”我说。我听到了杏子走来的脚步声。枣红马被拴在墙根的转槽上,正抡着尾巴嚼着草料。
“嗨,哪里这么多的臭话。”他说。他松开了我的手,从我肩膀上收回了他的手。他使我恢复了知觉,勇气倍增。
“杏子,给马添的是豌豆么?”
“嗯。”
“杏子沏茶。”
他说。他向房门口走去。
“爹,昨夜你去哪儿啦?”杏子说。她和我并排站着,我转过脸盯着洒满阳光的她爹的后背。
“我也不知道谁把我引到什地方去啦。”他说。我们看着他那副不以为然的后背。
他跨上房门口的台阶,转过身来,红色的面孔神采奕奕。他的嘴角斜斜地发出微笑,神秘地从怀中掏出一个扁扁的玻璃酒瓶。他拧开瓶盖,凑到鼻子下闻着。“好像今早才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方。”
“你醉啦还没有醒。”杏子说。
“没有没有没有,是酒神用浪把我接去的,酒仙又用气把我渡了回来,我连马都没骑就到家了,我不会醉的吧,你们看。”他说。他并住双脚又从台子上跳下来。
他把瓶盖拧到瓶口上扔给了杏子,把背着的枪取下来扔给了我。
他下了两次腰,返身一个纵步跨进了房子。杏子爹背的枪很沉很长,我横端在手中。
杏子把扁酒瓶放到房门口的台阶上,里面空空的。说她去打水。我把枪立到房门旁的墙上,拐过房子的跨墙走到房子的后面,顺着墙根滋了一泡尿,咝咝地响着钻进土里。我隔着一道低矮的墙看见了站着的卧着的山羊绵羊。我沿着房墙拐回来时,杏子提着一木桶水走到了房门前,她拾起酒瓶跨上了台阶。她的身后有一串浅黑的水点,从她的脚下一直洒到井口上。我操起立在门旁的土枪,随着杏子走进了房子,发现墙上有根大木橛,我把枪挂到橛上。挂在橛上的枪就像拴在槽上的马,什么心事都不会在这个时刻出现的。
杏子的父亲坐在炕边的中央。两条腿被二尺八高的炕墙悬吊起来。我看他的时候好像看的不是他,而是在破解一种未知的物体。他的大脑虽然进入睡眠状态,两条小腿虽然像提在手中的一双旧靴子,但他的腰身大腿和胳膊构成的三角支撑关系,说明他坐的是稳当的。用什么事实证明什么条件或根据什么条件证明什么事实,我手中惟一的条件就是用我的两条腿如何跨出这个庄院来证明走的事实。走的事实是过程的事实,走的过程是接近目标的过程。而在他的大脑中不知给我算计了多少道数字,这是未知的。现在让他睁开双眼说出套数已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除非让蜜蜂蜇他。
杏子招呼我去帮她,我帮她把她那个三角状的父亲拉直,让他如意地躺到了炕上。可杏子看了我一眼,似乎强调着我们早晨的鲁莽行为,泄露隐情后的红色已柔和地爬上了她的双颊。她向我噘了一下小嘴,快活的笑意像充满了早晨的青春般的气息。
我打了一个十足的喷嚏。
我看见了我心灵的影子。杏子虽然红着脸把嘴抿得紧紧的,但我现在只欣赏她那丰茂的一头秀发。这样我会将事做得自然的。若不这样,我会陷进她那潭水一样的眼波中淹死的。我心灵的影子不是我刻意追求的,女性的恍惚后面藏着敏捷,羞涩的前头露着果敢。我有苦恼,但苦恼不是这时候发生的。
心灵的影子明白地告诉我:就那么两扇大门,关上它,不该进来的就进不来,敞开它,不该关住的就出去了。
鹰有胆气,因此它才是潇洒自由的。
“眼馋吗?”杏子父亲说。他品足了茶,懒洋洋地解开了衣襟,腰间露出了两条子弹袋。黄灿灿的子弹在我眼前头发亮。
“多多多。”我说。我知道这是我这把枪玩的东西。
“娃娃。”他眼缝中的笑显得很深。
“用子弹里面的火药生炉子,也能烧些日子的。”我不以为然的说。
“哎,啥有啥用场。我专门给你搞的。”他的面孔严肃起来。
我隔着炉子上的烟火,瞧着杏子在他爹面前装出的那副害臊的样子。
“枪就是那个耍鹰人玩的东西,给那些日囊生也只是个烧火棍。”他说。
我知道我的那句话刺伤了他。伤他面子的目的是让他不要对我抱什么希望。我怕他让我当他的儿子,掌这个家。
“小当兵的,枪玩得怎么样?”他说。他的话中带有明显地挑逗性。
“他打得很神,昨晚来的土匪他总共放了两枪,一枪一个,打死了两个。”杏子说。她在她父亲面前夸赞起我来。
我心里一阵紧张,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种紧张。
我看了一眼杏子,杏子没有再看我。我感觉到将有某种事情发生。
“什么什么?”他说。他瞪圆的眼睛盯着杏子。“打死了两个?”
杏子看我,我看杏子,谁也没有回答,就像我们俩之间没有了空气似的。
“神了,看到门前的血迹,看到杏子红肿的眼窝,我觉得有些蹊跷,不想发生的事到底发生了。”他说。他坐直身子,两只拳头和两只脚跟撑起身子从炕上挪下来。手和脚往前时他的屁股朝后,他的屁股朝前顶时他的手和脚撑在炕上不动。“娃娃,你闯下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