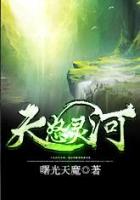时间走得真慢,我们望了望天,太阳亮晃晃的,还明亮得很呢。西边桑树地里的成千上百只麻雀还在开会,还在议论今天的太阳何以迟迟不肯回到黑夜的老窝。麻雀的叫唤声织成了一张密集的网,罩住了那片渺无人烟的桑树地。渐渐地,太阳一厘米一厘米下沉到地平线以下了,麻雀们的聒噪也骤然停歇。小队长毛老虎敲响了铜锣——收工了,人们放下手中的活,陆续回家。夜宁静地笼罩了消瘦的乡村。村民们洗了身,洗了脚,卸下了一身的疲惫。河埠头,深秋的水在微风中皱了皱眉头,又无声地归于平静。村民们赶紧吃晚饭,因为接着他们要赶赴生活的另一个主题——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听得木桥头的大喇叭里传出六和尚又尖又细的本地官话:今天晚上塔鱼浜村放映电影,放映的影片是……六和尚人长得比《三打白骨精》里的白骨精还要精瘦可怕,但是嗓音清晰得就像门前河浜里的水,流淌在我们的心里,十分的受用。他大概知道,这个时候,永丰大队所有的村民都放下了碗筷,竖起了耳朵在听他那只女声女气的细嗓子。话每每说到这个时候,他就卖起了关子,总是要顿上一顿(大约一秒钟),然后报出电影的片名,《小兵张嘎》。一部老片子,已经看了不下五遍了。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呕”了一声,互相对了一回眼,这个“呕”,既是惊喜,又是呕吐。但是失望是暂时的,我的肩膀上早已扛起一只阔长条凳。我们早早来到了电影场上。大队里来的放映员来得还要早,正在神气活现地指挥小队长毛老虎摆桌子。放映员嫌桌子没摆平,撮出嘴巴,正絮絮叨叨个没完。最后,他打着手电在道地上找来了两片碎瓦,弯下他那尊贵的腰,亲自垫在了桌子脚下。然后,“啪嗒”一声,将两只重重的漆成了绿色的铁箱子摆上桌面——那里面就是盘得满满的几盒电影带。我们惊讶地看着他取出,理顺,手法利索地装在放映机上。机器上刺眼的白炽灯灭了,连同灯光熄灭的还有满道地(屋前空地)的小儿哭声、咳嗽声、打情骂俏声。放映机开始转动。一束强光打在白粉墙上(这堵墙白天已经用石灰刷了一下)。墙上一个四四方方的白块,在黑夜里真是突兀得耀眼。电影带经过放映机时发出了“吱——”的声音,绵长而又耐心,很有磁性地安慰着我们贫穷的童年。在这种“吱——”的声音里,好人和坏人依次登场,人世的悲欢离合逐一在这堵白粉墙上显现……说真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偷偷地羡慕电影里的那些坏人,因为他们的饭桌子上总是摆满了鸡鸭鱼肉,通常还冒着丝丝的热气,还有酒,常引诱得我们口水直流。好多年里,我为我心里头的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惶恐不安。
轮船的速度就是那个时代的速度。从没有快速到有令人晕旋的感觉……在轮船里,我感到了时间流逝的缓慢,也感到了身体成长的缓慢——我曾抱怨这种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