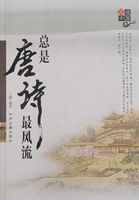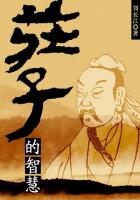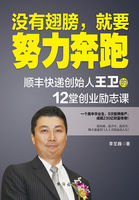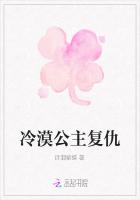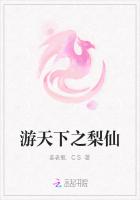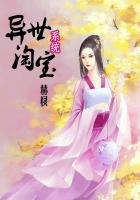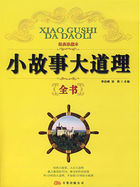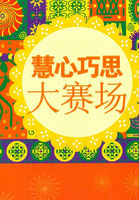二十、读书的日子
昏濛的雪天的礼拜日,在图书室里我有时会两眼茫然地看着窗外飘舞的雪花发呆,想母亲想家想千里冰封的北国想童年少年的往事。这时候来借书的人会少很多,图书室会升起一盆温暖的炭火,尹老师会在炭火上烤几个红暑或是馒头,那烘烤的香味会弥漫整个图书室,这时她会叫上我,让我也尝一尝那热气腾腾的美味,这对于15岁就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我来说,在那一刻的感动是刻骨铭心的。
一间平房,红红的砖墙,红红的机瓦。几列书柜,长长的坐椅,长长的几案。这是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沙棉的图书室,一个万人大厂的文化场所。
从女单身宿舍到厂部去要经过生活区内一条宽敞的马路,在马路旁就有这样一间图书室,从上午到晚上,里面永远有两位女同志坚守着岗位。我那时刚由前纺车间调入团委,团委在五楼。也正开始跟着电大做旁听生,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往图书室多跑几次,就获得了一本借书证。
我每借了书,一定准时还了去,从不误期,借还的次数多了,又极守信,跟书室里的几位老师便熟悉了起来,她们是尹老师、田老师、彭老师和舒老师,图书室隶属工会管理,负责的人是一个男同志,极有修养,难得的好人,名叫孙斌。
那时沙棉女单身有5栋楼房,全是四层楼,用一个红砖墙围住,全厂所有的女生都住在这里,每一间寝室住8到10名女生,大约2000来人。早、中、晚下班时嘈杂极了,我那时除了和同学李淑平向女单身的负责人要一间二楼放扫帚的贮藏室共同学习外,我还有团委办公室,读书的环境好了许多,大多时的晚上就消磨在书里,电大正式考入的同学都已脱产学习,所以对于我这个旁听生来说,所用的时间只能是晚上,除了规定的磁带,大多配套的内容要阅读。那五楼的灯光,常燃至深夜。这是好多年后,人们见着我对我说起的事。现在想来,沙棉那时候虽是生产经营的黄金季节,但毕竟常常在开展厉行节约、开源节流的活动,长夜难眠的灯光,竟无一位领导来对我进行干涉。安静的环境、宽容的氛围,让我得以在一张安静的书桌前静心苦读,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而今想来,对沙棉的领导,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我在图书室借书,一开始按规定只借一本,往返的次数多了,图书室的老师就给我开了绿灯,其他职工一次只准借一本,我呢可以借到2至3本,我一本本看,按三本规定的时间准时地归还,再换几本来,这大大节省了我的时间,因为每一次借书,对于一个上万人的大型纺织厂来说,是需要排队借阅的。
我每每抱了那些书回团委,总是贪婪地阅读,至夜深从五楼下来回女单身,脚步总有些踉跄,一路上,人还沉浸在书里,就如醉酒一般,似乎有些失去控制然。有一次在回家路上遇到一伙社会上的小混混,分左右两边向我包围而来,我竟全然没有发觉,来者一共四人,待他们贴近我身,开始动手动脚,我方惊醒。正待挣扎反抗,却听其中一人小声地说:“别惹这人,她救过青儿。”这句话真管用,这伙人一下子就跑了。青儿是沙棉一个老职工的孩子,很调皮,有一次团委举办活动,他们在活动室门前打起架来,青儿被人用一块砖头拍了脑袋,血流如注,在那儿还在叫骂,却没人管他,是我拖起他,叫上他的几位同伴,将他送到三医院,将手表押在急诊室,请求大夫先为他处理伤口,又回厂筹钱,才让他脱离危险,想不到一次善举到那天竟为我避免了一次灾祸。那许多年我差不多总是夜深了才回寝室,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可惜青儿若干年后还是死于非命,他是半夜被人枪杀的,他的父亲,一个受人尊敬的七级电工,白发人送黑发人,实在叫人伤心。
边学边读边写,我的文章开始陆续见之于报端,在极枯燥无趣的单身生活里,读书成了我最大的乐趣,那图书室也成了我开心的乐园。
图书室里的尹老师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她很瘦,但眼睛却极有神,一脸的微笑给人以十分和善的感觉,她的口音似乎是下江一带的,讲起话来慢条斯礼温柔又和气。到礼拜天,每是尹老师值班,她会允许我进入图书室的书架内选看,这于我是一份极大的恩赐,因为在那儿选书,比从图书室卡片上选书要直观的多。我一进入那书柜的行列,就在故纸堆里深深地吸一口气,仿佛那已陈旧的油墨书香能让人饱餐一般,放人进入里间这在图书室里是没有先例的。尹老师不仅放我进去同时还给我做其他几位老师的工作,使我得以拿到进入图书室的“绿卡。”有的读者看见我进入里间,也要求尹老师们放行,尹老师就笑着解释,说我是厂部派来查相关资料的。为了不让尹老师们为难,我选了靠窗子的一行书柜,用几本旧杂志垫起来当板凳,极乖地躲在里面翻读。读到开心时,痴痴一笑,读到动情处,涕泪滂沱,在那狭小的过道里,我踡缩着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礼拜天。呵!那些读书的时光是多么单纯多么快乐多么的怡然啊!
昏濛的雪天的礼拜日,在图书室里我有时会两眼茫然地看着窗外飘舞的雪花发呆,想母亲想家想千里冰封的北国想童年少年的往事。这时候来借书的人会少很多,图书室会升起一盆温暖的炭火,尹老师会在炭火上烤几个红暑或是馒头,那烘烤的香味会弥漫整个图书室,这时她会叫上我,让我也尝一尝那热气腾腾的美味,这对于15岁就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我来说,在那一刻的感动是刻骨铭心的。
我在图书室读书的日子是伴随着电大毕业、恋爱、结婚而渐渐结束的。生活让一个人必须完成人生赋予的职责使命,在特定的阶段完成特定的作业。从此,马路边的图书室,我只能投以它留恋的一瞥,静静坐下来读书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再去图书室竟不见了尹老师,人们告诉我,她得了尿毒症,呆愣着我久久无语。奔到一医去看望她,人瘦得不成样子,微笑却还是那样温暖,可恨苍天无眼,在死神面前,现代医术也无力回天。
出殡的那天,我特地买了一挂鞭站在厂大门口的马路边为她送行,记得是易斯易老伯帮我燃放的,鞭炮炸响的一刻,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哀乐伴着尹老师缓缓走过北京路,我知道,这位在我的学习生活中给过我无数精神食粮的敬爱的老师,这一辈子我是不可能再看见她那温暖的微笑了。
即使此刻,挥笔的我也是饱含热泪在怀念那个在大雪飘飞的日子里给过我烤红暑的人,那是在我生命中不可忘怀的一个好人。
我早已离开沙棉多年,那间图书室业已变作一家餐馆的所在了,一柜柜的书籍不知现在何方?厂部是否为它们找到了新家?这是我每每想起那间图书室时所想到的事。
2005年5月5日
二一、一生的财富
在学习知识的道路上,永不言弃;在自我修性的过程中,选贤为师。我没有进过真正的大学,是我一生的的遗憾;我也进过真正的大学,是我一生的荣幸。在这一所大学里,那赠我对联的是我的老师,我的知音;那鼓励我前行的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所有的磨难成为我一生的财富。踏平坎坷,直面人生,扪心回首,我心无愧。
(1)
高中毕业后,我只考了个省纺织技校。
我毕业的天门卢市中学,在县里又名八中,地址在十三窟。80年参加理科班的学生是全区10多个班级通过预考后留下来的,共两个班,一个班称七班,一个班称六班,七班的学生更优秀,成绩更好。我在六班,预考成绩在班中排第11名。全班58名学生仅两名女生,58人中复读生有51人,我是在级生。预考后的复习中我的状况很差,由于竞争太激烈,常常顾此失彼,导致最后在高考中以4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因为当年中专不算英语分,我连中专也没上成,那时我只想早点飞离父母,所以毫不犹豫上了技校。。
技校毕业后,我分配在沙市棉纺织厂,无论当初有多么大的雄心,但是生活却让我当了一名纺织工人。那时候想中学时代的一些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幻想,老老实实地与纺车打交道吧,但是贼心不死,心里总是寞寞的。心里只想这纺纱的事不是自己能干的,尽管自己工作十分努力,操作速度与水平总是不如人。纺织女工的生活是十分单调的,除了上班,大多要做的事就是睡觉、谈天、看电影、织毛衣。
这时候在我居住的学校宿舍,有一个厂部举办的电大班在我所住的那栋楼的四楼,因为每到夜晚灯火通明,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去探个究竟,想不到我一上四楼就被吸引了,那是一间教室,一个叫潘瀚的老师正上着语文课,(潘瀚老师现主编大型杂志《今古传奇》),我便躲在教室外听课,后来一位叫李淑平的天门老乡,也是技校上一届的同学叫上我,我们两人开始在电大的教室里旁听。那是1982年的隆冬。
(2)
旁听后没过两天,班上就开始报考考试科目,我开始接触“学分”这个概念,知道只要考及格就能算学分,规定的科目满了学分就可拿到大专文凭。但我打退堂鼓了,我跟的这一个班是文科电大,全班21人,连我算在内有7名旁听生,大家都是从当年的9月份开学起就在此上课,已经整整学了4个月之久了。离考试仅仅只有18天的时间,而我又是理科高中毕业的,根本就没有文科基础,加上我上四班,(在纺织厂,早、中、夜班各上一个星期,当中休息一天叫上三班,后来为减轻劳动量,改为上四班,即两天早班,两天中班,两天夜班,两天休息),而且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书本。
我真的要感谢李淑平,她激将我,她说报考一门科目只要3元钱,一共才9元,试试吧,你若是没有钱,我给你先垫上。玩笑中她已给我报了名了。
正当我处于犹豫与矛盾中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赠我一幅对联,上写着: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三楚能亡秦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百越可吞吴反复吟诵这幅对联,我下决心参加这场考试。
寄信人不知道,这封信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奢侈品。
(3)
当年要考的科目为翦伯赞的《中国通史》,张志公的《现代汉语》,还有一门是古典文学,从诗经开始的文典文学。我没有书,一位叫陈国明的同学(他后来留学日本)对我说如果没有书可以看看范文斓的书。但是当年的考纲是根椐翦伯赞的书列的,我将范文斓的书翻了翻,内容不一。这时候,我请一个叫叶茂英的同学将教学大纲借给我,我向她保证只借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一定还给她,那天我正好下了夜班,回寢室收洗了一下,就开始抄大纲,从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早上,我抄了整整一夜,除了吃晚餐,上厕所,我坐了十六个小时,眼睛看着书,笔在本子上不停地写着,凌晨七点多终于将一本大纲的要点抄完了,八点欠一刻,我将书交还给叶茂英老师后回宿舍呼呼地睡了一大觉,算起来我已有31个小时没合眼了。
18天的时间我要看完三门功课的全部内容,仍然在上四班,那18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日子。我首先将18天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规划,每一天24小时做到分秒必争,除了起码的休息和生活,我几乎全身心地放在了学习上。我把所有的科目分解在18天的各个时段,规定自己在限定的时段内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
上班路上我会准备3至5张小纸条,那上面是一些名词解释和填空之类的题,如果从女单身宿舍到进车间的这段路程我未能记住这些内容,我会在车间外停留几分钟,直到记住后将这些纸条扔进纸篓。在车间的工作中,在手背上我写满了一些大论述题的要点,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可根椐一些要点在心里将这个论述题进行全面思考,同时我还准备了一些类似时间、年代、人物、事件等难记的重点难点题,在落纱(纱锭在纱线绕满后要换一次纱管,一般一小时左右落一次纱,落纱后要做皮辊、纱锭、走廊的清洁,要换棉条桶)的间隔,我会拿出纸条看一会儿然后放入衣袋里,有一次在车子后换棉条桶,拿出一张纸条正看着,有人大叫:“喂,你的车子开花了。(指棉条经过皮辊时打结,或因棉条的接头不规则造成棉条在纺成粗纱时打结,此时如果不及时发现,这些棉条会淤在一起成为一堆棉花,一个挨一个的纱锭会受了牵连开成一片白花)”这是最影响落纱时间的,你必须停下车来处理故障,操作员在车间不断地巡视,这种状况是要扣分的,扣分就会影响奖金。当月在拿月奖的时候,我的同学史立慧拿着奖金条很是生气,她说她有次实在太困了便坐在车头打了一下瞌睡,不想被那个讨嫌的操作员扣了分,24元的奖金扣了她一角钱,只给了她23.9元。我赶紧去看我的奖金条,却发现我只得了一角钱而扣了23.9元。
那时候学习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地方,我在报名后没两天就按厂部安排从技校学生宿舍搬到了集中的女单身宿舍。一间宿舍挤8个女孩子,分上下铺,上千人的女单身不时有笑骂声、吵架声入耳,根本不可能安静地看书,我只得逃到在春天的时候常去的郊外那片小树林里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