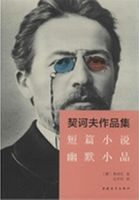跟晖哥熟识大半年,这是第一次见他真的对我板起脸来。我无话可说,默默地看他拦了辆的士。的士一路开到女生楼下,我回到寝室里,上床躺下。一觉酣眠,醒来已经是下午五点,我给班干部们群发了一条短信,表明我最近身体不适,除了团支书分内的工作,其他工作请他们自行安排。然后,我丢下手机,背起书包去自习室。
现在想想,我的改变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或许开始于在药房大汗淋漓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健康比某些事情更为重要;或许开始于坐在的士里回校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应该生活得好一点,而不是成为四处应付他人要求的万能胶。而改变一旦开始,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地、彻底地在我的生活里朝不同的方向哗啦展开。
不过,这些是后话了。中暑过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图书馆复习功课,接到晖哥的电话,他说:“来操场跑跑步吧。”
我说:“我马上要考试了。”
他说:“别懒!你真的要锻炼了。”
我想起前几天的事,无话可答。挂了电话,我换上跑鞋,去了操场。晖哥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米白色衬衫掖进黑色运动裤里,显得他腰部特别瘦。我有很久没有好好跑过步了,三圈之后,就已气喘吁吁。晖哥自己冲刺了几圈,回来找到我,和我一起在操场边上压腿。
“年轻人,身体是干活的本钱。要记得多跑步,多锻炼身体。一般来说,每个礼拜锻炼三次,跑个六七圈,然后压压腿、拉拉单杠,就行了,把体质练出来,再搞别的事。”
“晖哥,”我忍不住说,“你跟我说话的口气,真是……老气横秋啊……”
“是吧,因为我比你大很多啊。呵呵呵……”
我坐在跑道边上,两手撑在地上,仰头看天上的星星。操场边的探照灯今天没有开,身边的法国梧桐成了蓬蓬松松的暗影。跑步的学生不多,没有人注意到坐在一边的我们。我开口问他:“晖哥,你们什么时候离校啊?”
“二十三四号吧,还有半个月。”
“还是签了北京那家公司吗?”
“是啊。”
“那你马上就要走了?”
“嗯。”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没想到晖哥只回答了一个“嗯”。平常,以他的性格,肯定会絮絮叨叨地说很多“学长给你的建议”,可是现在,竟然冷场了。我想了想,干巴巴地说:“晖哥,学校这些师兄里,数你人最好。”
晖哥没有吭声。我隐约看见他脸上有笑意。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冒出这样一句话,却又收不回来,只好费力地解释道:“像你这样愿意帮助别人、愿意把时间分给别人的人,我见过的很少。师兄很多,却没有人和你一样,你是一个真正的师兄……”
晖哥仍然不吭声。片刻,他笑道:“陈子楠,师兄马上要毕业走了,你要记得向前看。”
我听到这句话,心里一沉,低下了头。确实,他马上要毕业走了。那个最终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而我,却要留在这个并不喜欢的校园里,无亲无故,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我鼻子酸酸的,两滴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在夜色里,我想他并不会看见。
“你要向前看。你现在所见的东西还有很多拘束,等你长大了,还会遇到很多真正的、如你所说的好人。那时候,你的眼界就跟现在不一样了,可以做的事也就不一样了。师兄一直希望你不要只和我一个人玩,希望你多交朋友,不要封闭自己。外面的世界没那么可怕。”
“其实这些话,我应该早点跟你说的。”他忽然改变口气,换成了自言自语。
我没想到晖哥会突然说这些话,这样真实,这样无可回避。我的眼泪一颗接一颗地流下来,我担心地想,脸上肯定在反光,晖哥会看出来了。我更担心的是,我十九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挫败感,像现在这样难看。我很希望一切都好起来,可是,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我不知道。”我忍住抽泣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到合适的生活,以后你又不在……”
“一定会有的,只要你敢于往前看。以后你交到了男朋友啊,还有结婚啊,这些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他又说。
我努力不让身体颤抖,泪眼模糊地看着他。
“不要压抑着。”他说。
我终于哭出声来。这并不是我这一年里第一次哭,但和晖哥在一起总是比较快乐,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哭过。我两手捂住脸,哭得很丑也不管。想起很小的时候,爸妈一吵架,我就哭,但我不明白人为什么会有眼泪,便一边哭一边对路过的大人说:“俺脸上有水,俺脸上有水!”这一刻,我很想跟晖哥全盘说出父母离婚的事情,说他们为何要把一切安排得那么理所应当,使我找不出对他们愤怒的理由,那些愤怒最终都指向了我自己。我想跟他说,那一天,也是在这个跑道上,也是这样的夜晚,我在逃避中认定我再也不要对类似的场景涉足。但是今天,晖哥帮我抹去了这一块阴影。虽然他不能一直拉着我的手走,但是,至少他帮我释放了这样一个夜晚全部无辜的星星。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和晖哥提及我的父母,因为我知道,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应该把时间留给轻松一些的话题。其实,晖哥也有很多事情没有跟我说,比如,对“女神”表白失败,还比如,他的换洗衣服为什么那么少,总是一件米白色衬衫穿了又穿,还比如,为什么他给我买零食吃,自己却从来不吃。这其中的原因,我没有问过,我只是在接过他递给我的巧克力与烤肠时,感到那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小礼物。
我哭的时候,晖哥就在旁边盘腿坐着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等我哭完了,他陪我一起去水龙头那里洗脸、洗手,若无其事的样子。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他陪我跑过两次步。唐僧一样反复督促我养成锻炼的习惯,再然后,我便要加紧复习期末的功课,我们没有时间再见面了。六月二十四日那天,大四毕业生全部离校,而我上午有一场考试,下午有一场考试。我不知道他是在我做哪一道题时离开的。等考试结束,走出教学楼,看到夕阳如旧投入这所校园的时候,我知道,校园里再不会有晖哥在某处等着我了,这个漫长的大一就要结束了。以后,我再也不会走进男生楼三楼向西的拐角,熟悉的门扉里,不会再有那个瘦长的身影轻快地打开门迎接我进去,让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然后,在暮色四起时,他带我出门散步,毫无理由地陪伴我度过十八岁时一切六神无主的时光。
但是,我会向前看的。每当经过男生楼的时候,向其他人喊出“师兄”的时候,夜色下跑得汗流浃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句“你要向前看”。一岁又一岁地长大着,从学妹变成学姐,变成毕业生,变白,变瘦,每经历一些新鲜的事情,我都会再去想一想这句话,一点一点地明白着这句话的意义。我想晖哥是了解我的,了解我当初的脆弱,也明白我心中能够种出坚强的种子。自从那个燠热的夏天之后,我再也没有晕倒过。虽然仍有冷、热、苦、辛,可我的躯体一直能够支撑我的行程,再也没有忽然倒下去。
这本是一场普通的婚礼,普通到有些随意。我看见新娘和新郎的很多亲戚的敷衍了事,倒是我们这一桌本科同学,一直认认真真地拍照、鼓掌、叫好。有些闹哄哄的瞬间,我在新娘的浓妆下面,依稀看到了初为人妇的端庄与喜悲。这个时候,我还是很感动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但仍然令这喧嚣的婚宴有了珍贵的光彩。
我也不时去看看另一个角落的晖哥。酒宴的氛围不适合起身去找他,他的眼神也没有向我们这边扫过。多注意他一会儿,就能发现因为入世多年,晖哥的举止还是变化了很多。比如此时,他向旁人大笑劝酒的样子,在我眼里就有些陌生。不过,我自己不是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吗?晖哥从未见过我踩着高跟鞋的模样,也未见过我与同学言笑晏晏、毫无心结的样子。在他毕业后这将近十年里,我们靠QQ维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他从一开始继续解答我的各种问题,到后来联系的时候问一问近况,再到后来虽然有惦念,偶尔对话,已不太能说上什么,只是说“不错”“加油”。
最近一次和晖哥联系,好像是去年夏天,他在我的状态下留过言。此后,就没有任何动静了。如无数而立之年的男人一样,他已经戒掉了在网络上记录生活的习惯。而我,也开始体味到青春的迷雾如何渐渐散去,露出生活平淡的原野;体味到人与人之间,沉默不一定是断绝,如同相见并非就是彼此看见。
等新娘过来敬酒的时候,我指着远处的晖哥给她看。她眯着眼睛看了下,说:“是我老公的同事?我不认得他,他是咱们以前的学长吗?”
我说是。
在座的同学听到我们讨论他,也往那边看。有几个不认得,有两个人还记得晖哥。
“秦晖大三的时候可以竞选校学生会主席的,但是他最后没去。当时,我们辅导员对他寄予厚望,结果他大三和大四两年什么都没干。所以你看,人——”在座的一位同学拿起一根筷子,铿锵地敲着玻璃转盘,“没有上进心是多么可怕的事。”
我心里并不赞同,但是仍然微笑着。面前的这些同学,有些就是当初疏远过我的人。但是,这又如何?那时我们都小,我们都曾犯错。人性本是趋利避害,都更乐于接近快乐明亮的人,我自己也未必能逃过。晖哥待我很好,但这并不代表,其他未及晖哥深厚的同学之谊,就不值得珍惜。
参加过好几次婚宴,酒席总是结束得比我想象得快。菜刚上完,很快就有人离席,将红毯踩得斑驳。我们这桌也吃得差不多了,有人提议道:“跟新郎、新娘合个影吧,趁现在外面没有雨。”
我们疏疏落落地走到酒店外面,挑了附近一个花台。新郎的亲戚拿着相机,我们女生站在前面,男生站在后面。正在准备之间,我看见晖哥和几个本地人一起走出酒店,在门口站定了寒暄。
十年前,晖哥与我的第一次长谈,源于他在食堂的人流里蓦然看见我也在。于是,他端了盘子,过来与我一起吃。那顿四块五毛钱的食堂餐,我们吃了两个小时。饭毕,在食堂门口,他高高地站在我面前说:
“我是你的学长,又是你老乡,有什么不懂的事情就来找?我……”
那一找,就是一年。其实,那只是短短的一年啊,但是于我,那一年如此漫长。那一年,好像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照相的顺序终于排好,我站定在属于我的位置上。身后是个身量颀长、肩膀宽厚的男人,他把双手按在我的肩上,让我靠在他怀里。我抬起头向他笑笑,握住肩上那双熟悉的手。今年,是我们相恋的第五年。
也许晖哥会再次在人群中看见我。也许,因为我已长大,他无须再在我的生活中出现。看见,看不见,都没有关系的。那句话将永远留在我心里默默,保存如少年时的清澈:
“谢谢你,哥哥。曾经在我的生命里来过。”
慢慢地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的美与光彩,懂得如何接受应该承受的,享受可以拥有的,直到我遇到了将会钟情一生的事物,直到我遇到了将会钟情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