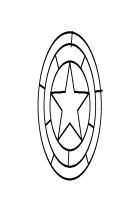当时,我是什么感觉呢?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并没有见到晖哥表白的样子或喝酒的样子,那个学姐我也不认得,这些都与我无关。我所认得的秦晖,心情一般都不错,很少生气,最多只是对我的烦恼太多,有些无奈地笑笑。有一次,他便说:“你啊,太敏感,又经常敏感得不是地方。”
我不喜欢听到这话,加上那天中午的例会布置了六七项任务,更是心堵。我斜了他一眼,梗着脖子不说话。
他说:“要适当改一改。”
“改什么!哪有时间!”我突然说。
晖哥不作声了。我说完也有点吃惊,毕竟从来没有学弟、学妹这样跟他说话,我也是第一次对他说话这么冲。说完,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缓和气氛。
就这样僵了一分钟,直到晖哥看着地上叹口气:“你的脾气,真的要改一改。”
“嗯。”我丧气地说。
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和平共处的。时间久了,客套与寒暄都不再必要,虽然待在一起,基本都是各行其是,我对着电脑忙活,他在另一张桌子上修改论文。有时,晖哥不声不响地走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根烤肠或一块巧克力,递到我面前说:“吃吧。”
我接过来,问:“你不吃吗?”
他摇头:“我不吃。”
这时,我就暂停作业,玩一会儿电脑,晖哥倚在一边看。那时人人网正时兴,我们一起看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哈哈笑着互相吐槽。有时,看电影或者美剧,就静静地看下去。
只要我不提走,晖哥是从来不会赶我走的,他宁可出门前给我一把备用钥匙,让我自行离开时把门锁好。在和他的交往中,我好像是受到了优待,又像是人与人常见的关系里,一个奇怪的意外。
并且,我们在一起待过那么多时间,他从来不会轻易碰到我,连衣服的擦碰也不会。
有一天晚上,在黄黄的台灯光里,晖哥站在我身边看电影。我悠悠地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是一种暖性的气味,像是什么植物被烘干之后的味道。有点熟悉,仿佛在家里闻过类似的气息。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波动起来,无心再看电影了。
我想晖哥抱抱我。
我悄悄用余光看着他的衣襟和衣襟里熟悉的衬衫。我的心思游移在电影之外,无意识地想着:如果这个人轻轻地把我抱在怀里,让我的脸埋在那米白色让人心安的衣裳里,我一定会非常快乐,会害羞地笑很久很久吧。
当然,我一定不会开口的,一定不会。我连“拉一拉我的手吧”这样的话都没有说过,怎么会叫他抱抱我呢?我这么经常来找晖哥,占用他的寝室,一有烦心事就要他陪我聊天,这对于一个学长来说,已经是十分打扰了,哪里还能想更多呢?
但是不久之后,我的心愿就实现了。
那时已经是翌年五月下旬了。武汉的天气,一过“五一”就会陡然燠热起来。五月,学生活动特别多,我忙得团团转。当时,班里一个集体活动需要定制统一的T恤,我辗转联系了街道口一个做文化衫的商铺,定在这天下午去店里看样衣。
我找到文体委员,希望他去街道口看衣服。他微笑道:“支书,这个礼拜我有两门课要考试呢。我看你还是自己去吧。”
这个礼拜,每个人都有两门考试啊。我心里想,但是没有办法说出来。我已经太熟悉这样的表情和语气了。相比其他谈笑风生、进退得体的支书,我这个沉默而迟滞的女生,早已经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班干部了。我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默默地等待着,等待学期结束,假期到来。
吃过午饭,我发短信对晖哥说:“天气好热啊,可是下午还要去街道口,无奈啊!”
几分钟后,晖哥回道:“下午可以一起出去,我要上街注销一张银行卡。”
饭后,我本可以小睡片刻,但刚一躺下,就有同学找我询问奖学金的事情。学校关于这类事的规定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我只能听着她的愤愤不平,干巴巴地劝说几句。等她走了,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洗了把脸,打着哈欠在校门口等晖哥。
晖哥见到我一脸困倦,说:“又没精神?年轻人,记得晚上经常跑跑步,活动一下。”
“又来了,好像你不是年轻人似的。”
“反正比你老很多啦。哈哈。”
晖哥比我高三届,但是比我大不止三岁,因为我念书较早,他念书较迟。但是,这也不至于让晖哥说自己老吧。我想打趣他几句,但忽然想到,晖哥一个月后就要毕业了,心里又有些黯然。
这种黯然,从开春就开始了,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在我心里弥漫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在晖哥面前,我总是装作并不在意这一点的样子。
在这种黯然里,我跟晖哥等来了公交车。武汉的公交车以疯狂拥挤著称,我们当然没有座位。晖哥帮我挤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我站在他的胳膊下面,脸离他的胸口只有几厘米远。晖哥问我为何上街,我如实说了。他说:“挑文化衫,不是文艺委员的事吗?”
我不答。
晖哥摇摇头,也不说什么了。我心里一下子变得更加黯然。
也许因为心情不好,虽然挨晖哥这么近,却没有开心。加上车里非常的窒闷,更不爽快。车开不久,我就感到不舒服起来,头晕,肚子疼。我本来想忍一忍,但是没有过多久,肚子疼已经让我不能忽略了,我对晖哥说:“我想下车,先去一下厕所。”
晖哥有些意外,但他毕竟是男生,不会拒绝。车到下一站的时候,我匆匆忙忙地挤下车去。一下车,灼热的空气轰然扑进我的肺里,我本来头就晕晕的,一瞬间简直天旋地转,差点一屁股坐在路边。我俯身撑着膝盖,待眩晕退去,心慌地发现,胃里也开始不舒服了。
晖哥在我身后说:“是不是太热了不舒服?我们搞错了,不该在这个天气出来的。”
我想说:“我没有选择啊。”但张了张口,竟发不出声音来。
我们下车的地方是武汉那种飞沙走石的旧城区。一群毫无特色的水泥屋在路边组成毫无特色的小巷。我随便挑了一条地基破碎的小巷往里走,一般这种小巷里面,都会有虽然惨不忍睹但是标志明显的公厕。
但我没有走几步,世界就变了。一些奇怪的、黑色棉絮一样的东西从四面八方挤过来,很快就挤满了我的视野,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除了自己吃力的呼吸声,耳边什么也听不见。我用最后一点视觉看见身边有一个电线杆,伸手抓过去,想扶住它。也不知摸到它了没有,脚下一滑,就彻底跌入软绵绵的黑暗中。
等到我重新看见东西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一个小屋的门口,有一个人站在我身后,让我的头靠在他的腰上——因为我身下的板凳靠背太矮。我抬起眼睛一瞅,正碰上晖哥低头的目光。
“中暑啦,”他龇着牙说,“确实太热啦。”
我这才看见他的额头上全是汗。我却没有汗,还有些发冷,四肢像被抽走了筋一样软绵绵的。看看四周,恍惚之下,仿佛是在故乡的某条小巷的小屋里坐着纳凉。但很快发现并不是,这是一条不曾见过的小巷,这个小屋是一家简单的私人药房。药房里除了我俩没有别人。一台旧空调在屋角哐哐啷啷地工作着,但是我觉得这里很安静。
这是这一年里,最安静的时刻了。我什么也不想,踏实地靠在晖哥身上,闭一闭眼再睁开,以防这是梦。
片刻后,从门外走进来一个步履轻快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几瓶矿泉水,用标准的武汉口音说:“快热死!”
“可好鸟?”他对我说。
我木然地看着他。晖哥接过水,拧开一瓶递给我。我喝了一口,胃里却并不舒服,对他说:“我感觉我要吐了。”
晖哥正在大口喝水,听我一说,赶紧找老板要了个垃圾桶来。我对着垃圾桶看了一会儿,却吐不出来。这个时候,那肚子疼又来了,且愈演愈烈,容不得我再犹豫。
“我要上厕所,要拉肚子了!”我焦虑地对晖哥说。
晖哥问老板附近哪里有公共厕所。老板看看我,大声道:“还什么公共厕所哩,外头这样热,不如用我家的算鸟!”
说毕,他打开手边一扇门,露出后面一个小小的住家院子,指了一个方向说:“红色的小门哈。”
我看到了,想要站起来。晖哥已走到我身边,拉起我的右手,牵着我穿过药房后门,走进那个小院子。在红色的门前,晖哥放开我的手说:“进去吧。”
我坐在药房老板家的马桶上拉肚子,至少有二十分钟。其间,我大汗淋漓,从小到大我从未像这样出过汗,亲眼看着手臂和大腿上一排一排的汗珠渗出来滚下去,全身的衣衫都被浸透了。
终于收拾完毕,我恹恹地走出洗手间。晖哥竟然还站在外面,正盯着院中的地面出神。一瞬间,我有些尴尬,简直不知该说什么好。倒是晖哥平静地说:“好了?回去坐一会儿,喝口水。”
说罢,再次拉起我的手。
之前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反应过来,现在,我感觉手心有点发热。这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个白净、美丽、苗条的少女啊。可是刚才在洗手间里看自己,除了脸色苍白以外,并不美丽,也不苗条。对这一点我真是毫无办法。
晖哥一直拉着我进屋,让我在板凳上坐下歇着,就和老板聊起天来。晖哥问:“这个门面是你自己家的?”老板说是。晖哥说:“武汉夏天热,中暑的人多吧?”老板大声说:“中暑啊,常有的事!小时候我们去江边玩,作死地热,搞搞就跟她一样,上吐下泻!”
我喝掉一支藿香正气水,正在用矿泉水努力灌掉那古怪的味道,听见“上吐下泻”这个词,抬头看了看老板。晖哥倚着药柜站着,衬衫背后还有汗湿的痕迹,扭头看着我笑笑。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两条腿足够有劲了,就站起来对晖哥说:“走吧。”
晖哥说:“走哦?”我点点头。我们就向老板道谢,付了藿香正气水的钱,一起走出来。
一直到离开小巷的时候,我还有点木木的,对刚才发生的事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在巷口,我看见了那根电线杆,目测从电线杆到药房那儿有一两百米的距离。这段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的小路,在烈日下蒸腾摇晃着。我想问晖哥什么,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最后只说:“今天真倒霉。”
晖哥叉着腰走着,说:“是倒霉。”
我一愣。晖哥接着说:“回去吧,我们打车回去。”
我也想回去,又犹豫不决:“我还有班里的事,没搞完就回去……你的银行卡怎么弄呢?”
晖哥忽然生气了,皱眉道:“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