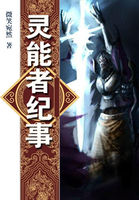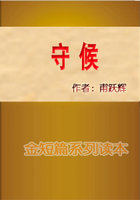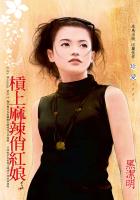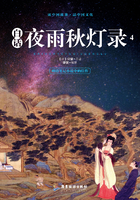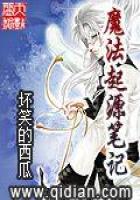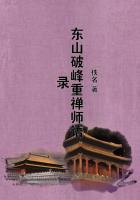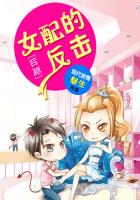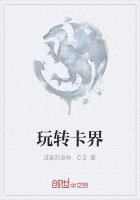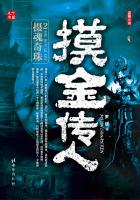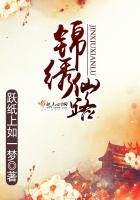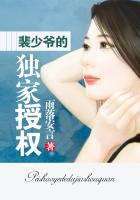1983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在中卫目睹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观。有人戏我:“人家都是拿名入抬自己,而你却拿名人抬故乡,为什么?”我说:“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后来我读到了宁夏大学一位老师的文章,讲的就是王维诗的意境与中卫的长河、大漠的实景。更奇妙的是1999年10月《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北京到新疆汽车拉力赛的车手们到中卫时,也亲历了王维诗的胜景。他们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自以为是最热爱故乡的人,但最近读张建忠散文集《长河云帆》,深为他对故乡的爱所感动,自愧不如地称他才是热爱故乡第一人。
张建忠生于斯,长于斯,故乡人民送他到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返回故乡,服务人民。他从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从县文联主席到地震局局长,又任吴忠市文联副主席。工作虽然多变,但他从没有停止歌颂故乡。他是故乡人民的儿子,他与故乡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散文《背盐》表达了故乡人民是怎样教育他过关隘,跳飞车、辨方向、涉沙海,走上人生之路。在路线教育中,他与山区人民坐在热炕上学习谈心增进感情,直到多年后,那里的朋友还让他带车去拉西瓜,不收一分钱,可见友谊的珍贵与深厚。
张建忠与故乡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小学起就担负起了沙漠边上义务植树的责任。北干渠的开挖,城乡道路的建设,哪样他都投身其中。他歌颂贯通欧亚大动脉的宝中铁路黄河大桥,告诉故乡人民这是国家为民造福的千秋大计。
中卫是宁夏有名的文化古县,浓浓文化熏陶了张建忠的心灵。《高庙》写出作者对中卫文化传统的独特思考。《沙坡头》、《老君台》等文,展现了作者对中卫文化名胜审视的新角度,表达了深邃思想意境。他把这些新见解介绍给来访的外省市领导、将军、作家、诗人等知名人士,受到他们的好评,这是从另一个侧面叙述家乡的山与水,为故乡添彩。
一枝一叶总关情。张建忠通过对故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丰富物产的描述,全方位、多角度地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再加上名扬西北的中卫小吃,更使许多旅游者回味无穷。作家张贤亮每到中卫总要品尝小吃,夸赞其文化特色。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张建忠如此热爱故乡,与他40多年人生经历有极大的关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用自己的双脚,无数遍地丈量了故乡大地,从而使他心灵升华,产生了人类最淳朴、最真诚的故乡情结。这种故乡情流动在他的血液中,充盈在他的灵魂里,自然地涌泻于他的笔端,激情满怀地写出了这部《长河云帆》,它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十分丰富。这本书对中卫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自然景观、民风物产有深刻见解与精彩描述,可以说是中卫的一本乡土好教材。
在提倡再塑中卫文化县的进程中,应该提倡人们多读读这本书。
《宁夏文艺家》2004年3月15日
第一章 月下旧影思故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暂居凤凰城的我,触景生情,任凭一颗自由散漫的心,飞还那峥嵘岁月。
50年前,我们即将初师毕业。几个小龄同学幼稚地问老师:“上哪个学校以后可以升大学?”老师说:“读中师有可能。”天真的我们以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岂不知“祖国的需要,才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
1957年夏天,我们十多个风华正茂的同学,满怀激情地步行数十里到沙坡头慰问修铁路的职工,他们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新月下的沙山顶上,指点江山,选认自属星辰,浪漫的年华终生难忘。犹如一位诗人所言:“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让我们去寻找光明。”
雏燕初飞,壮怀激烈,追逐理想,似乎眼前一派光明。可孰知社会风浪重重,雨雪交加,人生长路漫漫。我这个背包客上下求索,伴随日月,开始了“痛并快乐着”的万里征程。
那年,景洪市政府招待所的一位小车司机为我们三人办好了各种手续,拉我们走过了一个边防检查站。未几,来到境外一个小县城。街道旁到处挂着成都小吃、重庆火锅、百货公司等的中文招牌,的士司机是中国人,商店里使用人民币,中国四大银行的存款卡都可直接刷……司机还说,前些年这里荒凉偏僻,靠种罂粟生活。联合国委托中国政府,帮助这里的人改变生产生活条件,改变金三角毒品生产地的面貌。近几年这里也实行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利用本地翡翠资源大办加工出口贸易,在中国农业专家的指导下,种植水稻和经济作物等,使这里的经济飞快发展,才有了现在整齐的街道、楼房和金碧辉煌的佛寺、巨大的赌场和脱衣舞院等设施。
在一座小山头上,塑有一个巨大的佛像。前些年,这个佛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福祉,大量种植罂粟,不但祸害了自己,还流毒世界。如今对外开放,才有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欣欣向荣,穷佛换了金装,使我想起了高庙的玉佛和故乡那质朴的金色大漠孤烟,金色的黄河落日,金色的长城遗迹,金色的黄土沃野,金色的麦浪,金色的稻谷,特别是金子般的故人情谊,金色的故乡盛景,如丝如缕地紧系心头,是那样的美丽和谐,令人难忘。
家门外的世界,万紫千红,异彩纷呈。
站在玉门关前,我想起了故乡也曾是丝绸北路的通道。那“春风不度玉门关”、“大漠孤烟直”的空灵神来之笔,是怎样凝成了千古绝唱?
香格里拉有一种名曰血肠的食品,与中卫名小吃猪脏类似,我在别处未曾见过,据说是羌族特色。我想,是否与古代中卫地区曾留下过匈奴、羌、蒙古等少数民族饮马黄河有关。
曲阜的孔氏家族,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中国任何帝王家族所不能比拟的。站在孔庙前,想起小时候,因贪看家乡文庙祭孔大典而误了上课,差点遭受了一次皮肉之苦。
两次漫游平遥古城,我徘徊在城墙和街道上、高楼前,追觅为何此地文物历经浩劫,却能大部保存?一位医生告诉我:本地人文化积淀深厚,且又景仰尧帝及其遗迹,所以在“高贵者最愚蠢”的时期,他们反而“卑贱者最聪明”,想尽千方百计保留了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可中卫的古城墙却被一贯极“左”的人早早地毁了。我意识到:唯有有良知、衷心热爱故乡的人,才可能对古城、古文物的消失深感惋惜,对人为的破坏产生愤恨。
武威市雷台出土了汉代铜铸的马踏飞燕,被外国人誉为“艺术作品的最高峰”。武威文庙古称“陇右学宫之冠”,保存至今,被介绍为西北仅存的儒家古建筑之一。他们成为武威的两张历史文化名片,给当地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
站在武威夫子庙前,我触景生情,想起了中卫文庙,就其占地规模、建筑艺术、文化含量等方面,都高出彼庙一筹。这并非“月是故乡明”的偏爱。因为它与其他儒释道传统共同形成了地方文脉,成为故乡的精神支柱,教育和熏陶了一代代人的成长。它是烙印在我们灵魂中,熔化在我们血液中的精气神,任谁也割不断,取不走。因为故乡之爱,才成为我等游子长久咀嚼、怀念、梦萦的浓浓思乡情愫。
叹耶?痛耶?为什么文化古县留不住几百年来保存的文庙、砖包城、九寺十八庙、尊经阁、藏经阁、应理书院(学校)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呢?有青年说:“我们热爱故乡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富饶美丽、礼义廉恥的道德传统等,然而许多文脉载体都被20世纪50年代愚毁了,让我们传什么?承什么?”
乌苏里江边的虎头山畔,有座东方第一关帝庙,它以国内最早迎接日出闻名遐迩。记得小时候听人说高庙上关公的马蹄动了,便约了几个同学,用粉笔在楼板上画了印记。
登上虎头山顶,遥望彼岸俄罗斯隐隐约约的绿树红楼,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卫的学生们排队上街欢迎苏联专家,还把我们学校后面的图书楼(即文庙后的尊经阁)改名为“中苏友好大楼”。可谁知冰霜雪雾,使已经生长了70多年的大树,一夜间竟被连根拔起。原以为它长在山岩中,根深叶茂,却是历史所误。这是天灾还是人祸?甚或是自然法则?当时我没读明白。
我孤身一人,长久地坐在异常静谧的镜泊湖边,望着天上朦胧的月,水中微微皱起的波,思绪早已飞向远方:八月十五月儿圆,是中华民族各个家庭团聚的日子。可我独在东北,80有余的老父,却在遥远的西北,相距万里。第六感觉告诉我,他孤身一人正睡在冰凉的炕上,思念着远去的母亲。爱妻罗益群,刚生过小儿子才三天,便被叫去抢救难产,病人母子安全了,可她却落下了脚疼的毛病。我十分怜惜她步履蹒跚地新行在西天路上。两个儿子,也天各一方。月朦胧,水朦胧。触景生情,怎能不使我伤悲?善良的服务员提醒说:“老同志,中秋赏月可别受了凉!”一句话,触动了我凄怆感情的闸门,一股热泪夺眶而出……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连故乡都不爱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命运造就我这个背包客,还将继续旅游人生。无论将来我漂泊于楼群中还是江河畔,甚或是苍山茫原上,不变的唯有那故乡情结以及它背后的祖国,它将如影随形,如魔似幻地伴随我那孤独而流浪的心。
明月何时照我还?
选自《情系故乡》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