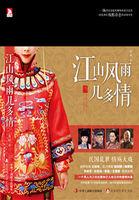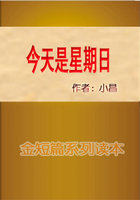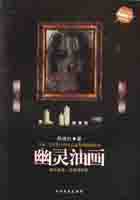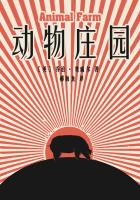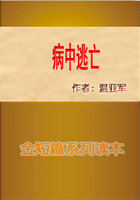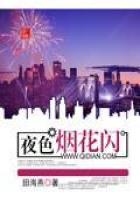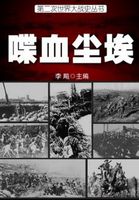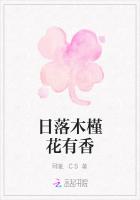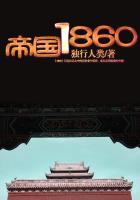银南地区“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加之大部地处河套平原、土质肥沃,有引黄灌溉之利,足以屯兵积粮,故而自秦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把银南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之一。我循着历史的踪迹,寻觅几位帝王与银南的关联。
据史料记载,秦惠文王于更元十一年(前314年),由长安到朐衍视察“游观北河”,“北河”即今宁夏银南地区,首开帝王巡察银南的先河。
秦朝建立后,始皇派他的皇太子扶苏为监军,蒙恬为大将,带领30万大军北击凶奴,一举收复“河南地”(包括今宁夏地区),后来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赵高合谋将二人迫害致死,由此阻断了帝王与银南的联系。
东汉永初二年(108年)羌族部落头领滇零夺取了富平(今吴忠的关马湖与金积镇之间),并在此称“天子”。只是11年后,羌汉人民大起义失败,短命的“天子”消失在战争的烽烟中了。
汉顺帝永建五年(130年)。他曾亲临富平等地巡视。
隋文帝杨坚,为了取得北部边界的安宁,曾任命太子杨广为灵朔行军元帅,驻扎灵州。后来杨广称帝,让银南为这位帝王的上台准备了一些条件。
唐太宗李世民在灵州接受敕勒九姓投降,此地曾被称为受降城,也可谓是一种辉煌。
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次年唐明皇出逃四川,太子李亨仓皇逃出长安,沿着泾河川到平凉,翻过六盘山,又沿着清水河来到鸣沙县境(今中宁县)。本拟北渡黄河,到丰安军(今中宁石空)凭借黄河天堑以自保。孰料风沙骤起,水急浪高,无法摆渡。众人劝太子不可冒险,遂辗转到灵州即位,布告天下。灵州便成了银南历史上的又一个王城。
李亨站在灵州城头,远眺黄河两条支流从城东西流过,城似一叶小舟,随风飘摇,恰似李唐王朝当时的江山。李亨心潮如河水起伏,那种惆怅、懊悔情绪无以言表。然而“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灵州美景,给他带来了暂时的慰藉,卷土重归的信念涌动着他的胸怀。“各地奏表战报齐集灵州,皇帝的诏命布告从这里达于四方。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干道有11条。”果然数月后,他挥师南下,恢复了李唐社稷。
宋朝国势渐衰,党项族人李继迁势力大增,被辽朝封为夏国王,后又封西平王。他是个胸怀大志的人,深知此处“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也”。于是他攻占灵州,于宋咸平六年(1001年)正月,改灵州为西平府,并在此建都。后来李元昊(继迁之孙)正式在此地建立大夏国,称帝17年后才迁往兴庆府(今银川市)。可以说当时银南的王气颇为兴盛。
宋夏对峙时期,西夏修筑了鸣沙城(今中宁县鸣沙镇),成为军需补给的重要基地之一。“国家兴亡自有时”。夏宝义元年(1226年)八月,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穿越腾格里大沙漠,先攻占应理(今中卫),并出没于鸣沙城。后直取西平府、兴庆府(今银川市),结束了西夏198年的统治。于是银南的中卫、鸣沙、灵州一线,为元朝铺垫了一段王者之道。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后,明军在青铜峡地区与西蒙贵族发生战争,明朝增加了戍边防卫。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为了永保朱明天下王朱栴到韦州就国,于是韦州成了银南历史上的另一个诸侯,分封他的第十六子庆靖王城。
韦州城在今同心县东北80公里处。这里南经下马关、预旺可达固原;北过惠安堡可抵吴忠、灵武;东经盐池到陕北;西穿罗山进入清水河川,它南通关中,北出塞外,再向西还可到达兰州、武威。正如明朝巡抚王越《过韦州》一诗所云:
停骖凭眺旧韦州,古往今来恨未休。
有酒不浇元昊骨,无诗可吊仲淹愁。
秦川形势通西夏,河朔襟喉控上流。
借问蠡山山下路,几人从此觅封侯。
韦州作为庆靖王的处所,与它的自然环境也不无关系。城东20余里有青龙山,在朝霞映照下,山势起伏,烟云翻滚,宛若游龙,是皇帝王气象征。城西30余里的蠡山(今名罗山)“重峦迭嶂、苍翠如染”,山上“多奇花异卉、良药珍禽”名为“蠡山叠翠”景观。两山之间是一片较为平展的大滩地,因沙多而被称为“旱海”,每遇大风,便有“青沙卷浪”的塞上独特壮观景致。另外还有“鸳湖澄碧”、“天桥霁雪”、“砖城朝旭”、“宫厅月夜”、“黑水回波”、“天台晚霞”等韦州八景,曾经兴盛一时。然而“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从长江之滨来到北国塞上“藩辅帝室”的庆靖王,总归忍受不住山中的寂寞,9年后,便将王室移居兴庆府。
朱栴生离属国,却魂归韦州。在韦州西北周新庄南二里许,有他的陵墓。陵墓北依蠡山,南临山水河,雄踞山麓,俯视韦州,有气吞“全国”之志。陵园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百米。陵墓形状上小下大,全部用夯土筑成,宛若蠡山缩小,显得非常稳定,并有左右二沟环绕,恰似“二龙戏珠”。地下墓室为青砖砌成,砖缝用铁水浇铸。共分五室,为前、中、后和左右室,尸棺放置在墓室中间,棺床以青石条砌成。
我站在墓顶眺望,韦州城及平川尽收眼底,联想随之而生。该墓虽不及秦始皇陵、汉茂陵、唐乾陵、明孝陵、清东陵等帝王陵墓的恢弘,但也不乏诸侯王的气势和风范。
1990年发表后曾被选入《塞上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