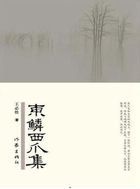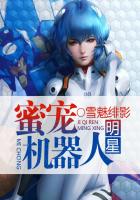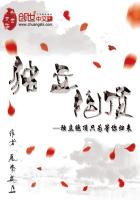2006年1月12日晚上9点,重庆市政府二楼会议室。
副市长一走进来就脱了外衣,对市政府副秘书长谭大辉说:“移民局的两位局长怎么还没来?”
市移民局发展扶持处处长黄道辉回答说:“徐江副局长正从万州区火速往回赶,已经快到重庆了;欧会书副局长正在市委开会,晚一点就赶过来。”
市监察局、就业局、财政局、劳动保护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在副市长到来之前就端坐在会议室。
晚上召开紧急会,就是研究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高金榜、宋原生带队到库区考察移民生计问题后,对后期扶持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前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要求重庆市在16日拿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向国务院三峡办报告。
移民搬迁后的生计问题、就业问题,是库区最为头痛的事,可以说不能拖、不能等、十万火急。因此,参加晚上紧急会议的各部委办局的负责人就显得有些惴惴不安。
偏偏这个时候,移民局这个唱主角的没到场,副市长对移民局办公室主任余棋林很是冒火地说:“快打电话催一催嘛,这么多的人等移民局,像什么话!”
会议通知太突然,徐江副局长接到通知时,正在200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区部署安置农村移民工作。而欧会书副局长也在市委开会不能脱身,原通知晚上10点开会,一会儿又通知提前到晚上9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该来的还没来。副市长有些不耐烦了,他一挥手说:“马上派人把欧会书叫来!我知道,坐在前排的是区、县长,他是坐在后排的。何蕾,快快去把他叫过来。”
看到市长发火了,在座的人噤若寒蝉,市政府秘书何蕾伸了伸舌头,撒腿就往外跑。
时间就这样难挨地过去了10多分钟……
“移民局的人到哪去了?”一脸愠怒的副市长,突然发现已到会议室的几个人也消失了,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原来,移民局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已不敢面对副市长的“脸色”,呆呆坐在会议室里不挨批才怪哩。他们全都蹲在门外,一个接着一个地给两位局长打电话。
要在平时,市政府开会迟到几分钟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得向全市公开通报批评。曾经,参加市政府会议迟到者,市长就叫媒体公开曝光。汪洋书记来到重庆工作,大抓会风,可以说在全市引发了一场“会议地震”。一次,市里召开全市性的一个会议,迟到、早退、稀拉、聊天、打瞌睡等恶劣的会风让人大跌眼镜。于是,没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个人得写出检查,迟到的和没参加讨论的也得写出检查,连参加会议、在会场上打瞌睡的人也记录在案,自然也逃不了写检查,作出深刻反省。这一次,全市就有几十个单位被公开点名批评。
拿着人民的俸禄开会,怎能马虎懈怠?
副市长也知道,移民局就只有两个副局长离重庆近一点。临时通知晚上开会,从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库区赶回来,迟到也是迫不得已的事。研究移民后期扶持问题,是库区安民、抚民之要,这一台戏,本来就该移民部门唱主角,“没有红萝卜还真不能成席”。
副市长发火不是没有道理,晚上开会先拿出个初步意见,明天晚上王鸿举市长还要主持研究一次,还要听取区、县政府等方面的意见,再做修改。
晚上10点,两个局长一前一后赶到会场,会议开始对三峡移民的后期扶持建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
市政府的会议一结束,两位局长又带着移民局的同事赶回发展扶持处办公室。欧会书副局长口述,向荣兵、董建平就打字,其紧张忙碌程度,有点像战争年代在战场上“口授电文”。徐江副局长抱来一大堆长江委的资料,他一边写一边按计算器计算。涉及到移民生存大计问题,几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一点不敢马虎大意。
当两位局长和同事们写完建议和汇报,已是凌晨3点半钟。
第二天,还是晚上,还是市政府那幢楼,会议室由二楼改在了7楼。市长王鸿举主持讨论了移民后期扶持问题。9个主要移民区、县的负责人谈了对移民进行后期扶持的建议和意见。再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写出正式报告。
这几天的时间是以半天为单位计算的。几经修改的报告,大年三十上午要送到市长王鸿举手中,正月初八,过年上班的第一天,市委书记汪洋要主持召开会议“最后定夺”,然后再报给国务院审批。这几天,重庆正在开“两会”,事情多得叫人心忧。副市长发一发火是可以理解的。白天要面对“两会”代表,晚上要研究移民的扶持生计问题。
一连几个晚上开会,研究问题都是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这几天的讨论我都参加了。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时,望着宁静的星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三峡移民才不叫人如此揪心和操心?什么时候百万移民的生活才会安稳下来?什么时候移民部门的同事才不会如此操劳?
三峡实施百万大移民,移民工作者肩负两大职责,一方面必须忠诚地推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必须做好安民、抚民工作,不得有丝毫的懈怠。
水库移民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项极富魅力、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在三峡库区,不少优秀干部、仁人志士或被“难题”诱惑、或被指派到移民战线工作,一干就是10年、20年。一个移民干部戏称,在三峡移民这个岗位干活儿,瘦狗也得熬出三斤油来。
在1997年大江截流前夕,市移民局把办公室移到了最前线。
那天,我清楚记得,当我拿着一叠材料,气喘吁吁地跑到移民局找局长,走遍三层楼,别说局长,就是处长和一般干部也不见半点影儿;推开打字室一看,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全都不翼而飞。正惊愕间,留守的吴德明处长告诉我说,全局的人都走了,办公用具拖了几车到最前沿去了。
在移民最紧张的时候,移民局办公楼静悄悄,这使我想起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谚语: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
因为,一切都在移民第一线紧张地进行。
大江截流之前,国家派专家到库区验收,这是真刀真枪对移民工作的查验,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虚假。重庆库区三个县要接受国务院三峡建委的验收,是真是假、是钢是铁,验收了才晓得。
市移民局长刘福银说,平时说三峡移民工作干得如何如何,也许没人与你论争,但国务院组织专家走村串户的验收,就是动真格儿,就像丑媳妇一样,你平时可以遮遮丑,但总有一天你得撩开面纱见见公婆。
在巫山、奉节、云阳三个一期水位涉及的县,刘福银佝偻着瘦弱的身躯,喘着粗气,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在江边、码头、移民家中挨门逐户地走访、查验。
他终于累趴了,可累趴了还得硬撑着,发高烧输液,就躺在担架上指挥。他嗓子变得嘶哑,说不出话来可还得说,实在说不出来他就写在纸上,或用手比画。
为治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其佳话流传千古而不衰。现在搞三峡移民,也是因为治理长江中下游的水患,库区的区、县长、移民干部多过家门而不入的事实在是不胜枚举,因为太多、太平常,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是大禹,这些平凡的姓名也不会流传千古。往事只能如烟,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三峡百万大移民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才会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在移民进入135米水位的紧张阶段,移民局规定:处级干部一年必须有120天在移民第一线——区、县、乡镇、村工作。处长们下去发现了什么问题,做了什么事,解决了多少疑难,叫基层签字、出证据,处长们回到单位凭“据”报销。
叫基层签字,这主意出自于重庆市一位市长的“拿来主义”。一次,市长接待世界银行的官员,结束时,世界银行的官员们拿出一张单子叫他签字,说是回去后才能凭据报销旅差费。这办法是世界银行的头头脑脑们为避免麾下走形式主义、走过场的一种好办法。市长就把这办法“推荐”给了移民局。
据统计,市移民局的几位局长1998年、1999年在库区一线研究解决问题都在150天以上。局长带头,处长们谁也不敢懈怠。
移民局后勤中心分管车队的副主任何伯泉告诉我说,移民工作的艰辛,驾驶员最有发言权。一辆吉普车,在库区一年就跑了7万公里,你算一算,平均每天要跑多少公里?
重庆市移民局副巡视员刘渝春,原在移民区当副县长时,就分管移民工作,干事总是心细如发,后调到市移民局当办公室主任。1998年,他统计了一组数据:全年收到文件2751个;发出文件200多个;编发《简报》、《移民要情》100期;仅局办公室就收发传真3000多(份)件;复印各种文件资料30多万页。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些纸张连起来,足足有84公里长。此外,移民局全年接待、陪同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中央各部委、各省市人员及其他各类往来业务人员近3000人次(平均每天就接待8-9人)。
这个数据太惊人了。如果其他部门,准会认为炮制“文山会海”,全国罕见,理应受到严厉的制止和批评。公正地说,这些文件,我也细细研究过,也认真“炮制”过,只有极个别文件可以省略,而绝大多数文件、要情、调研材料是三峡移民干部的汗水、泪水和心血凝成的。就因为库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作为代表政府机关主持移民工作的部门,对库区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必须做出“快速反应”。
刘福银说:移民工作如果慢半拍,就是历史罪人。
重庆市移民局有81人。有人开玩笑说,唐僧师徒携手去西天取经,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折磨,才见到了释迦牟尼,取到了真经;三峡移民搬迁要搞十几年,看来也要经过“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刘福银局长是“师傅”,处长是“徒弟”,“徒弟”偷懒,“师傅”就会念紧箍咒。
“只要一干上移民局长这活儿,就像‘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李善联今年50出头,在三峡库区的忠县干了近9年的移民局长,由于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谙熟三峡移民业务,且能言善辩,1998年调到市移民局当了信访处的头儿。他生性豁达,语言诙谐,由于与移民、农民有许多共同语言,处理移民群众上访也比较顺利。被库区的移民干部推举为“库区语言大师”。
他说:“当移民局长这些年来,我的感觉有四句话可以概括,就是:爬不完的坎坎坡坡,说不尽的酸辣苦涩,移民事业好事多磨,移民干部四面楚歌。”
在实际工作中,移民局长还得跑田坎,四处奔波,为水、电、气、路、土地求爹爹告奶奶,求左邻右舍高抬贵手,不要乱收费,多给方便。结果是常把周围的关系弄僵了。李善联苦笑说:“移民局长真是‘屎肠子做裤腰带——臭了周围一圈啊’。”
王海群是湖北秭归县移民局长,他说:“三峡工程是建设者的汗水,移民工作者的苦水,移民的泪水和烈士的血水共同铸就的一座无言的丰碑。”
移民工作实在太辛苦,从动员移民外迁到资格审查,从到外省市联系移民关系对接,到护送这些故乡人到“第二故乡”安家,每一步都有大量的艰辛细致工作要做。哪怕费尽心机让移民全家搬着家什到了江边,移民突然想起有些政策法规没弄清楚,就可以突然决定不搬了,要“说好了才上船”。
万州区副区长欧阳祖辉,高个子、大块头,满头青丝,给人一种虎虎生威的感觉。他当了移民局长后白头发就多了起来,当了副区长,还是分管移民工作。“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由于10多年来一直没日没夜地干移民的活儿,他的满头青丝很快消失殆尽,变成了一个早生华发、饱经沧桑的人!库区不少熟悉他的人都会背地里发出感叹:欧阳祖辉的头发,见证移民工作的艰辛苦涩。
从2000年开始,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就率队到外省市搞移民对接工作,为移民选取土地、选取宅基地建房。当时移民外迁还处于摸索、试点的紧张阶段,不能有半点延误,更出不得半点差错。如移民认为房子的选点高了或者低了,房子的朝向不对,有碍“风水”,只要移民一提出来,他就和接收地政府协商。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就可能使外迁移民工作受阻。把移民的房子、土地落实了,他又回到县里护送外迁移民。开县外迁移民多,已超过3万人。他一次次地把移民乡亲分别送往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以及重庆合川等地,行车里程超过40万公里。由于长时间坐车在省内外往返,他患上了极为严重的肛肠疾病,身上随时都揣有一大叠卫生纸,留下了终身的痛苦。迁出地的干部是这样地艰辛工作,而迁入地的移民干部也同样为移民煞费苦心。
山东省胶南市三峡办主任王利森为了使忠县204名移民到胶南顺利安家落户,曾先后6次到三峡。虽说是到三峡,但他迄今也没有去三峡或小三峡风景区好好饱览一下驰名中外的中华奇观。他到三峡是在忠县联系移民对接工作。在忠县甘井镇,他深入移民家中,耐心介绍胶南的情况,苦口婆心劝说三峡人到山东去生活,直到将移民全部安全地迎到了新家。
江西省永修县三峡移民办干部熊思文,从1999年从事移民工作,6年来永修县300多户移民的家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从生产生活、小孩教育、外出打工等,他为移民做过许多实事,移民们提起他无不交口称赞。
江西靖安县移民办副主任黄爱民,主管移民建房等技术性工作。他对移民建房质量精益求精,天天蹲在工地,皮肤晒得黝黑。他对移民怀有宽容的胸怀,不管大事小事,总是千方百计满足移民的要求,即使有的移民提出过分要求,一时解决不了,他也耐心解释,从不动气发火。有一次,一些移民到办公室又来反映安装自来水的事,这是一个提出多次但无法解决的问题。后来移民动手推搡移民办干部,黄爱民见状去劝解,脑门上挨了七八拳没有还手。他敦实的个头,要打肯定不会吃亏。他说,我不能出手,因为我是移民干部,他是移民。2002年,是三峡工程二期移民的决战阶段。向天文是巫山县巫峡镇枣阳工作站的总支部书记,负责辖区内三个村的移民工作。巫峡镇组织外迁移民到安徽考察,向天文为了说服移民乡亲搬迁,不知说了多少话,不知说了多少个日日夜夜。4月30日,他本已经说通了三户移民,并说好晚上9点在巫山码头上船出发,但一直等到12点,移民还没来。显然,移民“变卦”了。一同前往考察的移民干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天文二话没说,拿上手电筒,深夜赶往几十里外的东坪村做工作。
凌晨,他用嘶哑的声音从东坪村向带队人打来电话:“他们……同意了,我带着他们马上就来。”由于说话说得太多,从6月起,向天文感觉喉咙很不舒服,他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嘶哑,以至后来每天工作进展只能写在纸条上传递。同事李冬梅劝他到大医院检查一下,他说:“哪有时间哟。由于移民任务太紧,每位干部都是分片包干的,担子都不轻,别人想顶我的担子也顶不了啊。”外迁移民对接任务顺利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护送移民到外迁地。两个月来,向天文先后护送了三批移民远到广东三水、安徽长丰等地,长途奔波,辛苦异常。一次,向天文奉命送外迁移民的户籍资料到安徽长丰。火车到站时已是深夜12点,他独自一人抱着宝贵的材料在火车站坐到天亮。
8月底,最后一批移民外迁到广东省高明市,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仍坚持要送完这批移民。在家人的坚持下,他到重庆西南医院检查,经诊断是淋巴癌晚期。
12月的一天,弥留之际的向天文喃喃地对妻子说:“我负责的移民乡亲全都走完了,是不是……我也得——走——了?”
是的,移民们搬走了,向天文也完成了交给他的移民任务,他疲惫至极,合上了眼睛,他也走了,永远地走了,走向那不知有多么遥远的天堂……
库区移民干部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熔铸于三峡移民事业,不少人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为三峡工程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200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到库区视察移民工作。甘宇平向她汇报时,说到移民工作的艰辛很是动情:“重庆市移民局的一位副局长周金华双眼瞎了,局长刘福银得了晚期癌症,再也无法工作了……”
2006年9月7日,重庆市政府常务会上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授予刘福银“移民功臣”的称号。
消息在日报上发表之后,重庆库区移民部门的同志都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是一个活着的人,按照“盖棺论定”的传统习惯,一个省级人民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绝非偶然。
事情很快得到了证实,刘福银已生命垂危,在重庆新桥医院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之中。
9月11日,这是一个被世界标志为一场灾难的日子。凌晨,刘福银在极端痛苦中走向了永远的天国。
1996年重庆直辖之前,四川省的三峡移民任务全部交给重庆市。为保证移民工作的连续性,刘福银被指派到重庆市移民局担任局长。谁知他这一来就是10年,却无法再回到故乡。他那佝偻、瘦弱的身子,在各种重压之下终于倒了下来。
他才53岁,走得太早了。
我去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看到他在鲜花丛中睡得很安详、很沉稳。他不用再操劳了,10年的移民工作干累了,现在终于可以好好地睡了,永远睡了。
后来我才知道,刘福银根本不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更不知自己生命将尽,没给单位和亲属留下任何一句遗嘱,只留下无言的悲情。
一个热爱着生活的人就这样离开了生活……
开县档案局长陈显安,领受了负责一部分移民外迁的“军令状”之后,2000年带领外迁移民去接收地泸州修建房屋。那地方离城区较远,没地方住,就在窗户透风、屋檐飘雨的旧鸡圈里垫上干谷草,和建房的移民一起住了下来。白天,他和移民选宅基地、运砖瓦水泥沙石。晚上,跳蚤横行,蚊子成群,他们就不停地和“要把人抬走的蚊子”抗争。一天,陈显安累倒了,赶去医院看病,就在输液的时候,传来十几个闹情绪移民跑到火车站,买了车票要回家的消息。
陈显安二话没说,拔掉输液的针头,心急火燎地赶到车站劝阻移民,这些移民因建房地点不满意,闹着要回家。他知道,移民如回到家,就不可能再外迁了。他拖着孱弱的身子向移民保证,建房地点可以调整,并一再请大家相信他一次。终于,移民们被陈显安的诚挚感动了,10多个移民又回到建房的工地。
万州区玉安居委会支部书记邓永清为移民早日富裕,用自家房产作抵押,贷款修通了玉安进城的公路,但日夜操劳的邓永清却积劳成疾,左眼永远失明了……
其实,移民干部对忙碌、劳累、奔波,什么都能忍受,不怕辛苦,就怕“心”苦;心里面的苦楚无法诉说,无处倾诉,所干的一切得不到理解,得不到认可,那么,所干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湖北省移民局局长汪元良是三峡的“土著人”。他出生在秭归,生长在秭归,工作在秭归;22岁当村支书,而后任区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2000年调省里当移民局长。
秭归全县移民补偿资金24.1亿元。汪元良提出:尽管是计划经济移民,但也得按市场规律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改革的办法搞好全县移民搬迁。为节省资金,他把县委、县府、人大、政协这“四大班子”集中在一起办公,把中医院、西医院、卫生、防疫等单位也集中在一块,同时决定“高中进城,初中进镇,村办完校”,再穷也不能穷了读书的孩子。
秭归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新县城搬迁之后,全城面貌一新。老县城从原来的0.7平方公里变成了4平方公里;原7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变成了140万平方米;原5000瓦的用电量变成了2万千瓦;原日用5000吨水变成了1.5万吨;原10个电视频道变成了20个;原主干道最宽9米变成了55米……
秭归成功的搬迁,被誉为“库区搬迁第一城”,但各种流言蜚语也在峡江弥漫起来。有人提出对秭归县城规划只有2.2平方公里,超了规模,要处分汪元良。可汪元良说:“超一点规模是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秭归县在移民搬迁中,共搬迁83座桥,修了很多房子、道路,这些年来移民工程没塌一道坎,没垮一幢房,没倒一个干部,凭什么处分我?”
有的移民干部在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各式各样的检举信、揭发信、控告信就会像雪片般飞向上级有关部门。用几毛钱的邮票去整治一个人,在恰当的时机,在要调动或重用你的时候,这些捕风捉影的信常常会起到奇妙无比的作用。等到“组织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后,提拔之事已是水过三秋、无可奈何花落去矣!
“语言大师”李善联也糊里糊涂“挨过一锅铲”,充当了其中的一例。当把他的事调查清楚之后,细心的甘宇平副市长在一次移民局长会上专门提起此事:“李善联同志是受委屈了。”这位脸上、额前布满沧桑的50多岁的汉子,听到副市长这么一说,禁不住泪水长流……
或许是他受过无端的委屈,受过莫名其妙的伤害,深知“莫须有”这三个字的诡谲;或许他是库区的“语言大师”,又对三峡移民业务特别熟悉,市里就把他提升到移民局信访处当了头儿。
诚然,我们应该看到,极个别的干部,在其位并不是真心实意谋其政,而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自己向上攀升的砝码,苦心孤诣地为自己营造向上攀升的小氛围、小气候;只唯上,不唯实,说假话,说空话;干工作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坚持原则,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二推三六九,脚底擦油——溜得比谁都快。叫这种人搞移民工作,由于擅长唯上,欺骗性大,隐蔽性强,当然只会留下一个后患无穷的烂摊子。
我们有的机关干部,到库区就指手画脚,从不深入民众中调查研究,给库区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这毕竟是少数人。
开县是一个移民大县,县城将全淹没,移民补偿资金达35亿元。
分管移民这一摊活儿的副县长在移民战线干了多年。不知咋的,一大堆信件飞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他利用手中权力为儿子谋私利:承包工程、贪污受贿、作风败坏,一肚子坏水。各式各样的闲言碎语、蜚短流长,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像幽灵一样地弥漫着、游荡着,足以淹没任何一个人的心志。
上级派李善联率队调查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揭发信上的事是捕风捉影。他在给市委、市政府的调查处理意见中,建议有关领导在适当的场合讲一下调查的结果,以利于这位副县长开展工作。
1999年元旦刚过,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库区的区县书记、区县长会议,传达朱镕基总理视察三峡库区的有关精神,心细如发的甘宇平副市长一句“你受委屈了”,使在座的这位副县长泪流如注。
这位副县长的儿子在调查组查清楚父子俩没问题之后,为避嫌和远离是非的漩涡,悲愤之中,一气之下辞去了公职。
移民干部也喜欢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理解啊,理解万岁。库区有一个全淹县的老移民局长,属兔,由于劳累过度,头发脱落得太多,前额过分宽阔。他32岁当区委书记,1990年5月调任县移民局长,一干就是10多个年头。多年来,他有个记笔记的好习惯,上午做啥,下午做啥,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说:“当移民局长比吃肥肉还腻,比吃醋还酸,比吃黄连还苦。这大半辈子,爹妈死后我掉过两次泪,可当移民局长却有三次伤心落泪的经历。”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曾多次向县长、书记赌咒发誓:谁要再当移民局长,就是你们的儿子、孙子!
咒也赌了,牙齿也痛了,可移民局长就像上了磨的骡子,只要枷在颈上,绳在磨上,就只能推着沉重的石磨原地兜圈子……
他曾向政协委员们汇报移民工作情况和移民局长的苦楚,谁知政协委员们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心”,还向政府建议说:我们希望他还当一届移民局长。
区、县移民局长这官儿,不大不小,老百姓都管得了,有点像“戴着镣铐跳舞”,想当的又轮不上,不想当的偏偏又卸不掉。这位局长说,我只有一个信念,相信共产党不会整共产党自己的好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处”。我在库区工作多年,和各地移民局的局长、副局长都很熟悉,还没有发现一个在工作中不掉泪的移民局正副局长。
一位移民干部对我发牢骚说:移民部门是啥?是各部、委、办、局中的一员,请注意,是一员;别他妈的想精想怪,想歪了理儿。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区、县、乡、镇长,才是大爷。人生一盘棋,世事如棋局,走棋的规则是:“车走直路炮打山,马走斜日相飞田,卒子过河横竖走,士相不离老帅边。”在这一盘棋中,省市区、县乡镇,就是车马炮,可以长驱直入,攻城拔寨;部委办局,就是士和相。士相只能呆在老帅指定的半径行事,其职责就是不得越雷池一步。卒子过河还可以横竖走哩,我们这些区、县移民局,有时连卒子都不如啊。用组织部门的话说,区县乡镇叫“主干线”,我们理所当然就是“支马路”了。车马炮是“官”,士相就是“僚”,官说的话,“僚”就得照办。当然,参谋参谋还是可以的,但是,库区移民搬迁如战场,参谋的话,最多只能说3遍,说多了就是不懂规矩。
在三峡移民区,移民局是矛盾中心的漩涡,如地方行政长官要把移民区的公路修宽一点,说这样更利于经济发展,不管有没有计划,就叫移民局拿钱,拿么,把钱用完了移民没移走怎么办?不拿么,闲言碎语满天飞,说这个移民局长眼光短浅,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眼睛里根本没有当地政府。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移民局长?移民局长解释说怕违规、违纪,有的官员就说,既不要违规,又不要违纪,反正你得给我拿出钱来。弄得移民局长啼笑皆非,苦不堪言。其实,许多地方超规模的建设,根本不是移民局长弄出来的事儿啊。
在移民局长这个岗位上“存活”下来的人,肯定是一个“不简单的家伙”,最少也是个“人中极品”。因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补偿资金的问题,说穿了就是一个“钱”字。钱多,事情就好办,钱少,事情就难办。
在库区,移民局长都掌管着几亿、几十亿移民资金,如果一个县城搬迁,县里的所有部门、企业、事业单位都得求他,虽说资金是淹没单位自个儿的,但依照投资流程,钱是先批、后批,还是多批、少批?权力就在局长手中。
比方说,移民是按四期水位来进行的,搬迁的资金也是按不同水位时期划拨。有的单位本是四期水位才给搬家资金,但企业在发展中找到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急需用钱先进行搬迁和技术改造。这就要移民局向上直至国务院三峡办求得支持,提前使用移民资金,这可不是小事,因为移民资金是全国人民一厘一厘积蓄起来的。因此,移民局长在管理、使用移民资金上花去了大量精力。
在三峡库区,移民局长这个官是十分敏感的,由于监管着大额的移民补偿金,担负着移民及时搬迁、库区社会重组和功能再造的重任,其作用、其影响力往往超过当地的财政局长。组织部门在考虑移民局长人选时常颇费踌躇。选得对,是地方的福音,选得不好,可能会给地方的政治、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们承认,移民干部中绝大多数是优秀的,也不乏为移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英人才。移民干部队伍中贪污、受贿、腐败分子毕竟是极少数和极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