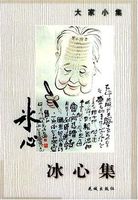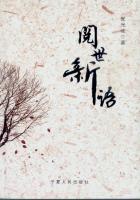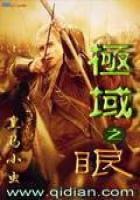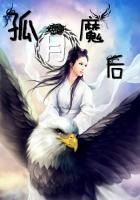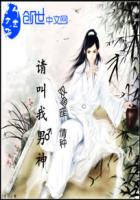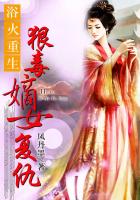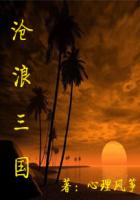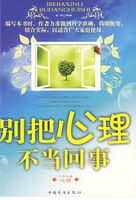“糖块”,是移民冯文化的一条棕黑色的小狗。
移民外迁不允许带“活物”同行。迁出当地,但不迁出重庆的部分移民,考虑到迁到新家路程并不远,就偷偷用编织袋、竹笼把猫、狗藏起来,放在搬运家具的货车中运到新家。
万州区长坪乡绿山村三组的移民冯文化,房屋处在175米水位淹没线下,大部分土地也要被淹掉,乡里就安排他一家四口人全部外迁,并定于2006年4月28日迁到璧山县正兴镇文家村三社安家。临走前的下午,由于很多东西无法搬走,冯文化就租了一辆车,准备把无法带走的东西搬到长坪乡樊家村6社的妹妹冯海燕家。正在收拾家具的时候,棕黑色小狗“糖块”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它一直围着家具转来转去地嗅,怎么也不停歇下来。
“糖块”怎么办?已读初二的大女儿冯雪琴眼睛有些湿润。
“嘘——”冯文化打一声呼哨,“糖块”像一道棕色的闪电一下就窜到他面前,不停地摇着尾巴撒欢。
吹口哨呼唤“糖块”,是冯文化呼唤小狗的一大嗜好。不管在屋前屋后,坡上坡下,赶场上街,他的口哨就是一种特殊的号令。锄地时累了,一声口哨,“糖块”会带给他欢乐;坐在田埂上歇息,一声口哨,“糖块”会为他消除疲劳。他耕田脚上糊了一腿稀泥,“糖块”会一口一口地舔舐,直到把他腿上的泥舔干净为止……
可是,这一次举家远迁,无论如何也无法带走可爱的“糖块”。冯文化和妻子蒲东芬商量了几个晚上,决定把“糖块”送给妹妹冯海燕喂养。他们担心全家迁走后,聪明的“糖块”循着山路找回来,房子在175米淹没线下,人一搬走就会立即拆除。所以,他们选择在晚上送走“糖块”,装进笼子之前,还特地蒙上它的眼睛,过了溪沟,转了几个圈子,还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它送到冯海燕家。
考虑到“糖块”到新家不习惯,冯文化就让读二年级的小女儿冯雪娇住在妹妹家两个月,把这一学期读完再到璧山的新家。
2006年4月28日,冯文化和妻子蒲东芬、大女儿冯雪琴挥泪告别即将淹没的房屋和土地,先是乘船到了万州,然后换乘大客车直奔新家。这一天,长坪乡有200位移民外迁。万州区移民局周一川科长、长坪乡乡长冯天荣等30名护送干部一路同行。400公里距离不算太远,从万州出发,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璧山县正兴镇各个移民安置点。
小“糖块”被蒙着眼睛,晕头晕脑地到了新主人的家。冯海燕怕它跑了,就用一根铁链子拴着,它不止一次想挣脱锁链,可使尽力气也是徒劳。应该说,以前冯海燕经常到哥哥家“走人户”,近几天她又到哥哥家帮忙拾掇家什,它对冯海燕也很熟悉。
第一天,“糖块”没见到主人,只是汪汪地叫着,呼唤着自己的主人。叫累了,它就伸长脖子、竖直耳朵,希望听到主人那熟悉的脚步,尤其希望听到主人一声尖厉的呼哨……
见不到主人,听不到口哨声,“糖块”开始“绝食”了。两天、三天……过去了,“糖块”仍不吃东西。它不明白,主人为何要把它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更不相信主人会弃它而去。
“哥,‘糖块’不行了,它几天都不吃……”冯海燕几乎是哭喊着给哥哥打电话。
“你给它弄点好吃的。”冯文化搬到新家就安了电话。听到妹妹说“糖块”不吃东西,泪水夺眶而出……
“那……你叫雪娇喂它试一试?”
“它也不吃,你以前喂它要吹口哨,我又不会吹……”
冯文化以前呼唤“糖块”吃饭,总是要吹几声口哨,搬到新家的头几天,他有时习惯性地打一声尖厉的呼哨,想起“糖块”已经留在了三峡老家,总是泪湿眼帘。
大女儿冯雪琴失去了“糖块”,整天就像丢了魂似的,想起“糖块”就泪如雨下,到附近镇上中学去上课,眼眶也都是红红的。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给了她无尽的关爱。可放学回到家,看不见还在老家读书的妹妹,看不见也是家中一员的“糖块”,便躲进自己的房间蒙着被子哭泣。她不明白,迁到新家为什么就不能带着小“糖块”呢?
冯文化从小喜欢养狗,在远近都出名。有一条狗他竟养了17年。妻子蒲东芬看到丈夫和女儿思念小狗,一连几天也都是以泪洗面。她对冯文化说:咱们去买一条狗吧,家里没有狗,一家人都不习惯。冯文化很快去买了一条棕色的小狼狗来喂养,颜色和“糖块”也差不多。家里有了这条小狼狗,他才有了些欢愉。一连哭了几天的大女儿雪琴才开始有了一点笑容。
“糖块”已经四天没进食,汪汪的叫声已经有些嘶哑,尤其是夜晚,它那拖着长音的声声哭号,如泣如诉,令冯海燕一家人心都碎了。渐渐地,它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知道自己将来会死去,而动物永远不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去。“糠块”再聪明,怎么也不相信主人会离它而去。
冯海燕没了办法,就强迫给它灌食,可“糖块”倔强地扭着头死活也不进食。第五天,7岁的小主人冯雪娇才强迫它进了点食,也许,小主人还在,主人还会回来,这成为“糖块”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糖块”虽然只是一条狗,但“饿死不食周粟”的感人故事在附近的村民中迅速传开了,长坪乡乡长冯天荣知道后陷入了沉思,一连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
安排迁往璧山县的200名移民,冯天荣对每一家都很熟悉,因为每一个移民安置点的住房都是经他一一选定的。他清楚记得,冯文化的住家原来在公路后面一点的地方,是他和璧山县正兴镇一起协商,才决定把住房建在公路边上。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糖块”送还给冯文化。之所以说这种做法“大胆”,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同。作为乡长,作为公务人员,他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移民外迁不准带“活物”同行,也不准带更多的杂件。这次迁到璧山县的移民,规定每一个人所带的东西不能超过2立方米,冯文化一家四口人,可以带8立方米的家用物品。
移民外迁搬家,如果不做出相关规定,移民会把撮箕、扫把和沉重的石磨都搬走,家破值万金,很多东西都是舍不得丢弃的。1999年外迁移民试点期间,就发生了一家移民外迁时就装了近30吨货物的“事件”。
长坪乡民风淳朴,移民们也按每一家的容积规定装运家什杂件。
几百人搬迁也十分顺利,这使乡长冯天荣十分感动。
被淹掉房子、土地的“双淹户”冯文化一家,搬家时泪别故园,无法能带走已与他相处三年的伙伴小“糖块”,就是自觉执行了不多装、不人畜混装的“有关规定”,表现了一个淳朴农村移民的理智和胸怀。
作为乡长,如果去为外迁移民冯文化送小狗,就是一种职务行为。但作为同乡,就是一种个人行为。正好,在重庆通讯学院读大学一年级的女儿冯洋打来电话,说是放暑假之前要搬一些东西回家。他决定休息日去一趟重庆,顺便把倔犟的小“糖块”也带上。从长坪乡到冯文化的新家,高速路只要四个多小时。
2006年6月30日是一个周末,下午,冯天荣搞完庆祝活动,就和要到重庆办事的乡干部李军一道,驱车前往璧山县正兴镇。
临行前,冯海燕把小“糖块”抱了过来,还特地在它的脖子上挂上一条彩带。冯文化读二年级的小女儿冯雪娇也随行,离开爸爸妈妈两个月了,这位小移民还从未见过自己的新家。临行前,冯乡长给雪娇买了饮料,又特地给小“糖块”买了几根火腿肠。
当天,我调查三期水位清库验收情况刚回重庆,听闻此事后,就立刻在高速路口“截住”冯乡长一同赶往璧山。上车一看,冯雪娇晕车,吐了一地,一条链子拴着的小“糖块”在一旁依偎着。冯乡长说,他还给移民汪琴带了一只搬迁时没有带走的猫儿。
冯乡长告诉我说,长坪乡是万州区最上游的一个移民乡,对面就是名满天下的石宝寨风景区。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全乡共有移民2714人,淹没土地2940亩,由于淹没的全是河滩上的良田熟地,先后有1447名移民迁到湖南、湖北和重庆市内的璧山县等地。冯文化就是乡里最后一批外迁的移民。
晚上7点多钟,当冯乡长带着猫、狗和小雪娇来到移民安置点时,冯文化早就守候在公路旁。
车一停下,冯文化把小“糖块”抱下车来,对着它打了一声响亮的呼哨,小“糖块”像是回应似的对着他汪汪地叫了几声。我看见,晶莹的泪水一下就贮满这位男人的眼眶。老家的乡长为他送来朝思暮想的“糖块”,他激动、哽咽,说话也语无伦次……
突然,小“糖块”摇晃着头,挣开冯文化的手,像发了疯似的拖着链子直奔新家而去。
“它要撒尿了。”冯文化眼睛红红地说。
果然,小“糖块”在它从未见过的新家门前的一堆碎石上撒了一泡尿。它用这种独特的、只有它自己才懂得的记忆方式,永远记住了主人的家,它不愿再离开主人了……
“啊,‘糖块’也真乖巧,在车上四五个小时都没有拉屎撒尿。不然,我要洗车了。在车上,‘糖块’只是闻了闻我给他买的火腿肠,还是绝食哩。”冯天荣感慨万分地说。
我走进冯文化的新家,听他讲着他与小“糖块”的许多难忘的往事,他的妻子在一旁站着,半个小时一直在陪着流泪。大女儿冯雪琴激动得抱着小“糖块”,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起来……
移民安置点沸腾起来了。“娘家的乡长来看望大家,给冯文化送来了女儿和狗儿,移民汪琴的猫儿也带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会儿工夫,冯文化门前就围了一大群移民和村民。
当冯天荣听他们说当地没有种柏树的习惯,而移民们在三峡每一年都要用柏树枝熏腊肉,冯天荣说:“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柏树苗来,就种在这门前做我们长坪乡的纪念树吧。”
从乡长冯天荣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光辉的闪烁,从这几件小事上,也看到了基层干部一颗挂记着移民乡亲的心。
告别冯文化等几家移民,我们驱车赶往重庆。冯文化一家四口激动得泪水涟涟的画面,却叠印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小“糖块”这只小狗拼死也要跟随自己的主人,以倔强的行为抗争,赢得了人类的尊敬,在冯天荣乡长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主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