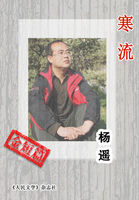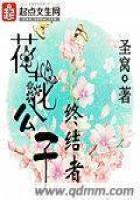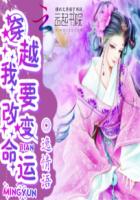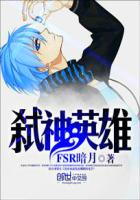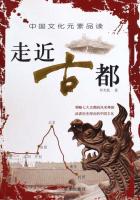门前是道街,小街,不算主干道,所以常有卖菜开店忝列其中,久而久之,成为街市。从西望去,路是直的,摆出的摊位却扭来扭去,蛇样的。有农妇卖菜的,蹲在地下,守着自己的那红的西红柿绿的青椒黄瓜清白的豆角一摊,眼睛瞅着熙来攘去的人流;有一家三口开了手扶拖拉机卖瓜果的,男的肃立不语,倚在盛满绿皮西瓜黄皮甜瓜的车旁只顾吸烟,车前的牌子写明了价钱,不过也是可以搞价的;也有江湖先儿吆喝的,是那些用了麦克挂在耳朵边上,手里挥舞了一物什招引看客,是削皮的小刀或者是磨刀的电火,和着满市的嚣声,添点生动。从东往西看,煎包铺烧饼铺粥铺胡辣汤铺豆腐汤铺米粉米线铺,呵呵,还有牛肉汤馆羊肉汤馆,大多利用了门前的空地,将矮桌低凳摆了人行道上,过往路人三教九流或许会在这铺位前留连,喝汤吃饼随你两便。卖卤肉卖豆浆是规规矩矩店内经营,顾客都是熟的了,不用吆喝就知道奔那儿去。
一街两巷,人们走来走去,主妇们也许是走了好几个来回,这个摊前看看,那个铺前问问,几多搞价,虽说不断地叹息“又涨价了”,手中方提溜满了惬意地回家转。现在有了超市,里面的东西丰富,价钱也许不贵,但是时鲜的东西还是到这街市买着方便,挑挑拣拣,尽拣那鲜货买。
我就在这市场的旁边生活工作,自然也对这几家铺子熟悉,甚至有的时候还称兄道弟的。再怎么热乎,该掏的块儿八角还是得掏,谁也不欠谁,也不落人情。其实这样最好。
买家的牛肉汤铺
买家,姓买,名字没问过,但是“买记”招牌高悬于门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买姓人家开的牛肉汤铺腾挪了好几个地方,犹如螺旋式地上升,门店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再怎么换地方,都不离这道街市。
当初刚进城的买姓人家当街支起了牛肉汤铺,也就是一个小铺面,十几平方,晚上两口子和两个杂作住在店里,白天哗啦啦地升起防盗的卷帘门,收起当庭的铺板铺盖,几张桌子长条凳布在店内,门口的一口三尺深锅冒着狼似的雾腾腾的蒸汽,熬了一夜的牛骨头汤泛着粘白的小浪花,小买——大家都是这样叫他——站在一方台阶上无论冬夏于热气腾腾的锅边上,执大勺子给人盛汤,旁边的大海碗里放好了薄如纸的牛肉片儿,碗底还铺满了碧绿的葱花儿,各类调料一一调进,仔细得如计算机设置好的程序,深勺在汤锅里一舀,徐徐倾入碗中,那牛肉片儿和葱花儿就翻滚着上下漂浮。夫妻二人各司其职。门外则搭了一顶遮阳棚,棚下也摆置了长条的矮桌矮凳,喝家也怪,还就喜欢坐在外面吃,甚至还有人端碗夹火烧蹲在外面呼呼噜噜就着街市的喧嚣把自己喝得满头冒水大汗淋漓。就这毛病。女人的桌子就在门外的遮阳棚下,收钱卖牌,还兼做切饼。杂作幸亏是小伙子,一个细气点的收碗洗碗抹桌子,细腿风似的跑的不亦说乎,一个粗壮些的烙饼切肉切葱,薄薄如纸的牛肉片在刀下翻飞,一会儿就码起了一堆。
买家的牛肉汤一个早上卖几百碗,甚至上千碗,动作程序就在这一起一落中,枯燥的过程枯燥的应对,细想想,这也需要本事啊。拾碗擦桌,择葱打煤,日子竟也这般过来了。现在杂作雇了四五个,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女人还是收钱卖牌,男人还是执勺盛汤。女人总是对熟客嫣然一笑,收钱找钱;男人在盛汤的起落间也总问:辣椒少点……还是不要葱?许多顾客认准了小买这一家,无论远近就好小买家的这一口,所以买家牛肉汤铺前的路边停满了摩托车、小轿车什么的。
说到收入,小买总是闪烁其词,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辛苦上。能有多少利,还不是点撅屁股哈腰的辛苦钱?你来卖50碗试试,光端那盛满汤的大海碗就够呛。不过,不说是不说,仝老板们也能算出来:一碗利润几何,十碗,一百碗……大致心里也有数了。就是不算,从开初略显憔悴土气的买家女人身上也能窥点端倪,如今的女人精神年轻了许多,偶尔还穿金戴银。大多是熟客,小买和小买的女人也和顾客扯点闲话。听说房子是刚性需求,调调涨涨,是吧?这是小买说的。股市那线这线的,看着头晕,不如咱卖汤踏实。这是小买女人柔柔的话了。想必那钱也去囤了房子或者投到股市上了。
小买也是场面上的人,也常被卖面条的仝老板或者张老兄等邀到烧烤摊甚至饭店喝点啤酒白酒的,有时也回请,回请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牛肉汤铺,切一疙瘩牛臀肉,拌个翠绿的黄瓜,或者几个松花蛋变鸡蛋。仝老板就开玩笑地对小买说,兄弟呀,啥时候到饭店里喝几口?小买的寸头下面就会浸出点汗珠子,偷觑一眼坐在门口的女人,说,内部消化内部消化。出了店铺的门,仝老板就对张老兄或者是李经理说,他小买的口袋里能掏出一张大票,我仝字把头割了。张老兄或者是李经理就嘻嘻笑着说,仝字没头就剩工了。
仝家的面条铺
这仝家面条铺的老板,自然是仝老板,富富态态,弥勒佛般,见人先笑后说话。人们叫他仝老板,是看他富态,衣服一穿挺胸凸肚的还真有点老板的派头。
十年前,仝老板的一家刚进城里这道街市的时候还比较寒酸,大大小小的五口人连同压面条机一起,住在一间倚楼栋一头搭建的约几平方米的临时建筑里。白天大人们忙乎着,十二岁的小姑娘就带着两个阶梯般的妹妹满街市地疯跑,仝老板夫妇把这街市当成了老家的村子,对这几个孩子不管不顾,吃饭的时候都一个个地回来了。饭是老三样,早上面叶,中午捞面条,晚上汤面条,一家几口端着碗顺次蹲在小屋的门前呼呼噜噜热火朝天地吃喝着,惹得买菜的大妈们路过这里直扭头看。亏得仝老板他们勤奋,每天经手的面袋子要一卡车。男人那个时候还不叫老板,大短裤一穿,精赤着上身,一会儿压面,一会儿“突突”着摩托车给其他面点上送面,反正染的就是一个白,白的眉毛白的面庞白的服裳……女人则亲自卖面,笑盈盈地对着每一位来买面的童叟,称完了面随手再抓几根放进去。
生活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进城几年后,仝老板还时常给别的面点送面,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是一小伙计来干了,仝老板时常骑着摩托车出去联系业务,寻求一些大的客户。那间当初栖身的临时建筑已经拆除,仝老板在别的地方觅得了压面车间和住室,但是这个菜市场上的面点却不舍得丢掉,老板娘和她的大女儿经营着。后来仝老板是开着桑塔纳四处联系业务的,还购买了商品房,下面两个超计划生育的女孩也在城里上了学。我还间或见到仝老板,仍然是那么富态,见了人还是喜欢先笑再说话,不同的是现在衣帽整齐干净了。
成为仝老板的仝老板还是有点郁闷和遗憾,膝下无男孩,比不得小买,喝酒的时候就哀叹一声,挣的钱够养老了。也就时常寻找一些偏方叫老婆给他熬着吃,什么绿豆熬山药,王八鳝鱼都吃过,还被一个算命的偏方给骗去了1000多元,终是无济于事。于是自嘲一声,命里该吃球,跑到天外头,拾块干蔓菁,一摸还是球。
我问仝老板,家里的地还种么?仝老板回答:那点地只能顾住吃。现在都住进了城里,就不考虑它了,租给了别人种。你们城里人会舍得干我这行么?只怕是丢不下那身份。细想想也就是,城里人能够舍下身份做这些的,恐怕是大智者哩。只可惜这样的大智者太少,宁可守着那三二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也不愿做这些“丢身份”的事,呵呵,都是些假斯文。农民进城,也算是把城里人看透了,就那点表面溜光水滑的本事。真地把钱揣兜里的,还是俺这些农民呵。嘿嘿!不给你说了,我还得进面去。“突突突”,拜拜了哈!
发达的二崔
要说发得大的,还得属当初买咸菜的二崔。也许有发得更大的,比如张老兄李经理们,人家可能是不露富,外人也就不知究竟了。
据说二崔从捣腾咸菜疙瘩起步,两千元钱还是借大舅子哥的,初始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也不为过。
二崔眼珠子见人忽悠悠地转,说话间不断笑着点头,不管顾客是褒是贬,好象满是赞同的意思。按老辈人的说法,眼珠子活的人,心眼儿比细筛子的眼儿还多。二崔本来个子就小,再一哈腰再一点头,就被埋在了咸菜缸子的后面。不知怎的,二崔知道了我也是夹河滩的人,就攀上了老乡。不仅是攀上了老乡,还知道我写写画画的,发表过点东西,就一定要看看我的剪贴本。几天看完,归还我的剪贴本的封面就多包了一层类似于学生包书皮的硬面纸,后面还写了“诗”,大约就是仰慕的意思了。这是街市上我见到的最有文化的一个摊贩。
有了这点文化,二崔终究是不愿意老蹲在这里卖咸菜疙瘩的。等我再去咸菜铺子,只见了二崔的女人守摊,二崔不见了,问女人,也只是笑笑说不出所以然。又过了些时日,连这个咸菜铺子也不见了,换成了卖卤肉的张经理。
再见到二崔,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这个时候的二崔走在街市上,不高的身材被西装裹了个严严实实,胳膊下面还加了一黑色的包包,逢谁跟谁打招呼。见到我,抓起腋下的黑包展开胳膊向我迎面扑来:老乡哥呀!你也不去看看兄弟!我被动地与他寒暄,不明就里地问:现在在哪儿高就?二崔忙不迭地从黑包里掏出了一个名片盒子,从里面祛出一张,我一看,龙门温泉洗浴中心总经理的头衔赫然在目。按说二崔的生意做大了,却没有忘记街市上的故友,挨着街发名片,有的还给一张黄澄澄的VIP贵宾卡,打八五折的。我和小买、仝老板也收到了一张这样黄澄澄的看着很尊贵的卡。临走,二崔给我们打着招呼:我请你们吃饭,一条龙的。
二崔不忽悠。又过了大概一个星期,二崔的电话给我们一个个通知了个遍,还说要来车接我。我一听,赶快谢绝。我和小买就坐仝老板的桑塔纳直奔龙门西山。
到了地方一看,才知道不是想象中的小洗澡堂子,还真的是一大片的有饭店有露天的温泉池子还有住宿的宾馆,这些都是配套的,还有就是主业的洗浴中心了。大门口有人专门候着等我们,一报上我的名字,门口一个婀娜艳丽的领班带我们到饭店的一个豪华包间。领班说,崔总有点事,马上过来,不过说了不要等他,我陪你们先吃着。老总们的“马上”是个什么时间概念?那就吃吧。虽是满桌子的佳肴,领班殷勤侍奉着,这饭却吃得有些沉闷,想必小买仝老板暗自对比了一番吧。马上了又马上,终于在走廊里听到了崔总打着电话的声音。进门,二崔电话没停,颐指气使,用滴溜溜转的眼睛向我们逐一示意了。屁股刚沾椅子,二崔就连连表示歉意,说刚才是一个副市长要来视察云云。
二崔端起酒杯略微表示了向我们的敬意,忆起街市的往日,随口引用了伟人的诗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作结。我适时把我新出版的书给二崔“雅正”,二崔接起书扑扑楞楞翻了一遍,仍是一脸谦恭地把书放到屁股底下,说,真了不起呀,大作家。回去一定秉灯夜读。接着又把伟人的“沁园春”从头到尾吟诵了一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句听得出是用了狠力的。
杯盏往来,都有些晕晕乎乎的,刚好适合去泡澡。这一切都由二崔手下的保安领我们去,二崔和领班还得忙乎着去陪领导,就此拜拜。一溜烟,二崔不见了。
柳柳
我们都叫她柳柳,或许是姓柳,或许是名中有个柳字,亦或是她与“柳”有着某种特殊的关联——反正,集市上街坊里的人们都叫她柳柳。
柳柳终日端坐在街市一隅,面前就是一米见方的摊位,那可是个黄金地带呢!摊位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针头线脑,利润以分厘计。柳柳的这个摊位,虽无正式的划分,却是她的“常所用”,市场上三教九流的人都知道,街道办事处的人也都知道,所以没有人来挤占她的位置,市场办的人反而还对她免费免税,若有初次来到街市的生面孔趁早占了这块地,左邻右舍做小本生意的人就会将其劝走。也有二蛋样的生瓜蛋子呈蛮不让的,柳柳来了,就把自己的纤维包往那儿一放,佝偻着身子与其对峙。是的,佝偻着身子!二蛋样的人就得居高临下俯着头看柳柳。柳柳虽然是个佝偻半残疾人,腰弯成射箭的弓,使身子不超过一米,但是头发梳得整齐,脸上也是干净的,眼神自然透着倔强透着澄澈,就是不与你吵不与你闹。与这样的人对峙,二蛋样的人也了无情趣,丝毫没有高大雄武的感觉,要么自己另寻了地方,要么就是街道办事处的人接到信儿了跑来劝你趁坷台下驴走人。总之,柳柳的摊位是铁打的营盘。
这块地方成为柳柳的“常所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源于何时何因,是柳柳的老公管了扒窃的闲事而血洒斯地还是大领导在这里视察与柳柳说了几句话?不得而知。许多知根知底的街坊邻居大多都调走了外出了搬家了,但是人们都隐隐约约知道有人给她供货,柳柳只管摆摊即可。街坊里的人们唏嘘柳柳坎坷,频频照顾柳柳的生意,柳柳也是感恩的,针头线脑的价钱也要打个折(或者抹了零头)。这一条柳柳永远都没能实行,老主顾们把该给的钱给了,什么打折不打折的,值不了一把青菜的钱,不值当。
反正,柳柳就是这样团着身子守着她的摊位,无论春夏秋冬。常到市场的人们都知道柳柳,缺个针头线脑硬扣软攀的,说声到柳柳摊儿上去了——就啥都有了。柳柳也怪,从来不吆喝的,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把佝偻的身子更是紧紧地团起来,脑袋支在抱紧的膝盖上头。这样子做生意,竟然还能挣得一个月的生活,并且把一个上高中的男孩子供得圆圆满满。日子久了,慢慢地人们从她的只言片语中也觅得了她的一点过往。据说柳柳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失去丈夫之前也是婷婷玉立如杨柳般,也许就是那血色中的一声哭泣,腰再也没能直立起来;据说现在的柳柳是坚决不吃低保的,把三番五次登门的街道社区干部给推了出去,嘶哑着嗓子说吃低保就能把老公吃回来么?柳柳的儿子倒是很少到柳柳的摊儿前帮忙摆摊收摊,柳柳说孩子的学习忙,不让他来的。
终于,柳柳的儿子到摊儿前来了。有人说那小伙子很挺拔很阳光,像他不在的父亲。柳柳的儿子来了是要说大事的。他考上了二本,南方的一所大学,学费拿不出。柳柳的儿子很焦急很无奈的样子,围着柳柳的摊儿磨圈打转。柳柳的头颈离开膝盖直起来,仰脸对着儿子小声而坚决地说,不能去找街道,咱们自己想办法。政府说不是可以贷款么?
这事儿不知怎的,传遍了整个街市,第二日就有三三两两沿街摆摊的小商贩们给柳柳捐款,票额红的绿的都有,还有许多叮叮当当的硬币。正在柳柳推辞不下的时候,那个二蛋样的男人也从街市的另一边来了,大大咧咧地把手中两张红票交到柳柳的手中,还是居高临下地俯望着柳柳粗着嗓门:还推辞啥?先叫孩子上学,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说完,转身就走。无奈,柳柳只好佝偻着身子,手偷偷抹去了眼中的湿润,把脸埋在膝盖之间,认真地把一笔笔大小款项零零碎碎地记在卷了毛边的小本子上。
某一天的清晨,柳柳的摊儿空着。柳柳领着她挺拔的儿子一个个地给街市上的人们鞠躬,晨光逆打在他们的身影,暖色调的镜像中一高一矮缓缓行走在街市上,儿子的背上背着蔚蓝色的旅行包时时地上下跳跃。而后,柳柳才回到家中,拉来纤维大包,继续团在自己的摊位前,不吆喝,面对着喧嚣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