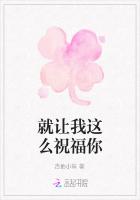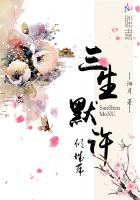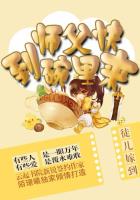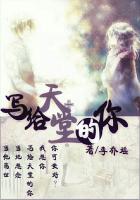作为韦克特妻子的吉拉受到的伤害更是触目惊心。她出场之时也是遍体鳞伤,衣衫不整。从尼古拉斯对韦克特讯问时的话语中得知,她受到了尼古拉斯手下人的轮奸。尼古拉斯一句“她没有看起来的好,她在流月经”暗示着轮奸给她的身体带来的巨大伤害。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被轮奸已是奇耻大辱,而尼古拉斯在审问她时还故意问她被轮奸了多少次,延长了她痛苦的过程,是对她身心的极端摧残。
韦克特的儿子尼奇还是个孩子,心中充满了对自由和未来的幻想,渴望像飞机一样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他在剧中的所有信息都是从尼古拉斯的口中透露出来的,他似乎没有受到拷打,然而他却最终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剧终之时,喝完了送行酒的韦克特不肯离开,口中喃喃地问起儿子的信息,尼古拉斯回答说:“别担心,他是一条小阴茎”。在这个句子中,他用上了过去时的“是”( was) ,暗示着尼奇已被杀害。
其实身体伤残的造就者尼古拉斯自身也受到了权力的伤害。在他身上,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情结、优越情结及虐待狂趋向。优越情结是指:“怀有优越感之人,其自己感觉的优越条件并不真实,只得以优越感来掩饰其自卑感的心理。”[88]尼古拉斯反复向韦克特一家展示自己是“国家、宗教的代表,跟国家首要人物关系密切”正是优越情结的表现,可见自卑根植于其内心。在他的行为上,体现了自卑———妒忌———疯狂的发展历程。他竭力表现自己是文明人,他处处展现自己的权力,然而从他的话语中可以解读出他内心的空虚自卑。他既然以文明人自居,却让人破坏作为文明代表的知识分子韦克特的书房,分明是对文明的诋毁,他的行为来源于妒忌心的驱动。从始至终,他都在炫耀自己的权力,其实除了权力,他一无所有,他大声呼喊:“我并不是单独的,我并不是单独的”,正是他内心残缺的表现。迫害韦克特三口之家,使之四分五裂也正是他的“破坏性的妒忌心”使然。自始至终,文中都没有提及到底韦克特犯了何种罪行,退一步说,如果是韦克特犯了罪,对他的拷打尚可理解,那这与他妻子、儿子又有何关系呢?尼古拉斯的行为还是一种虐待狂的表现。他对韦克特说:“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我喜欢他人的死亡!”表现了他歇斯底里的虐待狂热。他虽然没有亲身上阵参与对吉拉的凌辱,然而,他乐于窥探吉拉受轮奸的心理感受,表明了他的变态性心理。最后,在三口之家之中,尼古拉斯选择了对孩子的杀戮,完成了他对这个和谐之家的最大破坏。也许他正希望别人如他一样,孤单无依;希望通过斩断别人的亲情纽带以窥探别人家庭破裂、生不如死的心灵痛苦。精神分析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的人往往会寻求自我补偿,如果这种寻求过于偏执,就会形成过度补偿。[89]尼古拉斯选择了对权力的疯狂追逐,在权力上他成功了,然而他除开权力什么也没有。追根溯源,尼古拉斯对权力的过分膜拜,导致了他的人格分裂。一方面,他想做个文明人,拥有幸福的家园;另一方面,他过分追求权力,导致了人性的残缺,他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借国家的名义疯狂地摧残迫害文明及家庭。他对韦克特所说的“你认为我疯了吧?我母亲是这样认为的”正是他的心理状态恰如其分的写照。
然而,虽然尼古拉斯迫害一家三口有他个人的目的,但韦克特一家三口由于拥有与统治阶级不同的信仰而遭受身体的残害的事件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在对韦克特的审讯中,尼古拉斯指责韦克特是国家的叛徒,他说:“我们都是爱国人士,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拥有共同的信仰,除了你。”显然,尼古拉斯与韦克特之间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他们私人之间的问题,韦克特已被定位于国家之敌人,对他的伤害也许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但客观上发挥了规训人民的目的,他们一家三口的身体被当成了政治规训的工具。
在品特另一部戏剧《山地语言》中,品特同样展现了肢体伤残。该剧分为四幕,讲述的是青年妇女萨拉与几位妇女到监狱探望狱中的亲人的故事。在等候的过程中,有一位年长的妇女被监狱的狗咬伤了手,鲜血直流,萨拉勇敢斥责代表强权的狱警和军官。年长妇女和她儿子见面之时被禁止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山地语言进行交谈。轮到萨拉与丈夫见面了,她的丈夫被两个士兵架了出来,他显然也是刚刚受过刑讯,以至于不能行走,不能言语,因而萨拉和她丈夫什么也没说,在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是画外音。终于,狱警告诉年长的妇女,他们已被允许用山地语言进行交流,但她已不会说话。在这部剧作中,遭受肢体伤害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长的妇女,她不但手臂伤残,并且在恐吓之下,患上了失语症。另一个是年轻妇女萨拉的丈夫。
损伤性疾病有广义及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损伤性疾病是指由于机械、物理、化学或生物等因素造成的创伤;狭义上的损伤性疾病则是指机械致伤因子致伤于机体,所造成的组织结构完整性破坏或功能障碍。如锐器切割或穿刺、重力挤压、钝器打击、过度牵拉、子弹或弹片射击等,都是暴力作用破坏组织的连续性。[90]在品特这些戏剧之中,显然,他们患的都是“损伤性疾病”。然而,这些损伤不是某种事故造成的,而是以国家的名义形成的。在《送行酒》中,韦克特一家的信仰与代表国家信仰不同,他不屈服的后果就是妻子的被轮奸及儿子的死亡,以及自己的遍体鳞伤。妻子身体所遭受的伤害及儿子的死亡又成为胁迫他屈服的工具。而在《山地语言》中老妇因为使用山地语言———一种被国家禁止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遭受了肉体损伤及心理胁迫失语。
损伤性疾病的特点在于其鲜血淋漓的直观性,随之而来的是其巨大的心理威慑效果。统治阶级正是看中了这一威慑效果,因而往往使某些敌对力量身体遭受此类的惩罚以警示他人。虽然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微观权力的时代,品特戏剧中触目惊心的肢体伤残却意在提醒世人,中世纪时通过砍头、五马分尸的手段来实现暴力统治的方式并未消失。品特戏剧中的损伤性疾病给读者带来惊悚的效果,引起民众的深思,表明了作家痛恨国家权力滥用的政治立场。
在品特的另一部戏剧《归于尘土》中,疾病则以隐晦的方式展现了国家权力对人们的伤害,该剧讲述的是精神病人丽贝卡在心理治疗师德夫林的催眠引导下回忆起她此前的生活经历。丽贝卡的情人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常常用双手一前一后扼住丽贝卡的脖子对她施虐。在丽贝卡与她的情人生活的经历中,她目睹了一些恐怖的经历:成排成排的囚犯被驱赶到海中淹死。而在一个工厂中,所有的人都要向她的情人脱帽致敬。她的情人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火车站台将妇女们的孩子从她们手中抢走。而在丽贝卡的生活当中,搜捕犯人的汽车警报声总是不绝于耳,在一个天上布满星星的夜晚,在死寂的街道上,一个老人与一个小孩拖着行李前行,其后跟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其实这个妇女就是丽贝卡,她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在月台,妇女们怀中的孩子被士兵们从手中抢走,丽贝卡的孩子虽然经过了伪装,却因为在紧要关头哭出声来,也被劈手夺去。也许这正是她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沿袭了品特一贯的不确定性风格,《归于尘土》的许多情节也是令人迷惑不解,剧情缺乏必要的理解背景,人物关系模糊不清,身份来历不明,丽贝卡的回忆与现实相互交织,让读者如坠雾里,不知所云,难以理清头绪。被剧中的男女所迷惑,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该剧讲述的是一个情爱故事,德夫林和丽贝卡分别就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91]
然而,大多数学者还是一眼就认定了其中的大屠杀主题。学者格莱姆认为:“《归于尘土》是品特的唯一历史剧,源于品特对于大屠杀的终生思索及自从1980年以来的品特政治剧和主题剧写作方向。这是一部深入接触品特的犹太人属性的戏剧,虽然品特在剧中对纳粹或种族灭绝并未直接提及,然而这就是一部涉及大屠杀的戏剧。”[92]路易斯·高登也指出:“《归于尘土》是由一个简单的人物讲述的20 世纪大迫害的集体记忆。”[93]
的确,品特对于丽贝卡的致病原因并未明言,在剧作中对于纳粹也是只字未提,这可能就是造成人们对于剧中内容难以确定的原因。表面上看,心理病人丽贝卡是暴力的唯一受害者,然而,通过对她的病因的探寻,却发现后面隐藏着更多的暴力。在催眠师的刨根问底下,通过丽贝卡的叙述,就像电影的回放,往事一幕一幕呈现,在她的言语中首先呈现的是一群人在向导的指引下默默走向大海,不久,海上能看到的便只是随海浪上下漂浮着的各种行李;丽贝卡认为他的情人是一个导游,然而她又看见他站在一个工厂中,戴着软帽的人们站成两列,全体脱帽向他敬礼;后来,丽贝卡又看到了一个女人站在高楼的房间,俯视着星空下老人小孩拖着行李在冰冷的街上行走,后面跟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突然,妇女手中的孩子被士兵劈手夺走。
在催眠师的引导下,女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抱小孩的女人正是准备逃离的自己,也正是这个情人夺走了她最宝贵的、她怀中的孩子。荒诞派擅长的直喻手法发生了作用,显然,品特提供的场景会让读者毫不犹豫地将思维联接至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她的情人可能是个纳粹军官,他在工厂中的行为正是纳粹施展淫威的方式,他也不是什么导游,而是干着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进地狱的活儿,成群死亡的人群正是得于他的“引导”。而在丽贝卡的回忆中,她还无时不刻地听到警报声。“警报声没有一刻不在响着,不是在这个街角就是在那个街角,他们坐在警车中,鸣着警笛”,[94]警笛声已经成为了丽贝卡生活中的一部分,极其荒诞的是以至于她认为自己已经离不开它了:“我讨厌它的声音消失,我讨厌它离开我,我憎恨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拥有了它。我需要它,时时刻刻,这是一种美妙的声音,不是吗?”[95]不过,也许丽贝卡这么说却又是那么正常,因为警笛还响在周围,别的地方的人就还没有遭殃。时时刻刻生活在这样的恐怖环境中,丽贝卡患上精神疾病是再正常不过了,她正是在国家暴力的胁迫下致病。而通过丽贝卡的疾病,又联系上了无数的犹太人的伤残与死亡,这是一个民族通过国家力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的暴行。
品特在1996年巴塞罗那品特戏剧节前夕接受记者的采访中的陈述印证了人们的猜测,《归于尘土》的剧情有所明朗。在品特看来,这部戏首先表达了对纳粹作为国家暴力的对人们的伤害:
《归于尘土》是关于两个人物的一部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德夫林和丽贝卡。在我看来,这个女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野蛮暴行的环境中,从而一生为这些回忆饱受折磨。……很多年来,我自己也深受类似痛苦回忆的折磨,我相信肯定不只我一个人有此感受。我成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结束时我十五岁。年少时的恐怖的景象和人类之间的残暴深深印刻在我记忆中,伴随了我的一生。你无法逃避,因为这些回忆时刻都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这就是《归于尘土》所要表达的,也是丽贝卡终生不能摆脱的。[96]
然而,品特并不认为纳粹暴力就是这部戏剧的唯一主题。他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
记者:那么,这部戏是关于纳粹主义的吗?
品特:不,完全不是。这部戏是有纳粹德国的影子,我认为没人能彻底忘掉这一点……丹尼尔·戈德哈根在新近出版的《希特勒的忠心刽子手》里说到,当时大部分德国人清楚地知道所发生的暴行。这的确是真的,比如说,早先纳粹分子把犹太人赶到充满毒气的卡车里屠杀,工程师们必须确保这一过程可行有效。开始的时候,效果并不好,因为卡车质量不均衡,于是当毒气开始注入时,人们便涌向车尾导致卡车翻倒,所以工程师们不得不重新调整卡车结构,这样,杀人的目的达到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比方说当时生产毒气的人,他们可不是为了杀鸡而生产毒气的。[97]
在这里,通过工程师改进杀人卡车和生产毒气的故事,品特表达了对于普通公民对人权的漠视的痛心疾首,很多时候他们不但不反抗,任由人权遭受践踏,甚至成为国家暴力的帮凶,资助国家暴力践踏人权。接下来,品特继续表达了他对国家权力的谴责:
我在《归于尘土》里所反映的不仅是纳粹分子,因为在我看来,如果简单地集中在纳粹分子,那这部戏就不值一看了……我认为这么多年来,不单单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也包括许多宣扬所谓民主的国家也默认一系列镇压式的、冷漠无情的谋杀行径……在《归于尘土》里,我不单谈到纳粹,我还谈到我们自己,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反思,以及历史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影响。[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