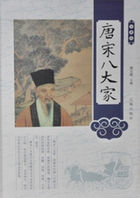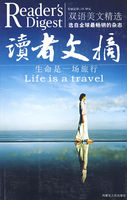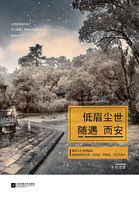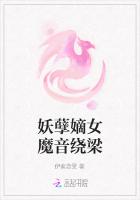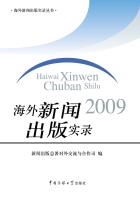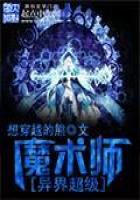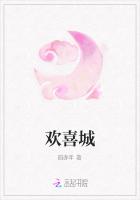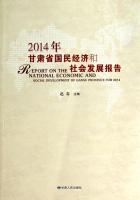阿斯顿的这个故事中断了原来故事的直线叙述线条,具有了米勒所说的“巴尔扎克之蛇”的弯曲回环叙述线条之妙。[103]它拓展了戏剧的时空,在时间上将剧情引入了阿斯顿过去的生活,从现在回溯到了过去,而在空间上,则从阿斯顿与弟弟米克的房间内移换至了精神病院及其阿斯顿过去生活的环境,扩大了戏剧的深度和广度。从阿斯顿的角度而言,他是一个受迫害的对象,是一个“被精神病患者”,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话多了些,是由于某种谎言的不断扩散导致了自己的“被精神病”命运。阿斯顿在精神病院中被盘问、被隔离、被强行电疗,他反应迟钝、话语结巴的行为似乎有了某种合理的解释。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词,别忘了阿斯顿刚从精神病院中出来不久,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他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他的精神分裂幻觉呢?因为照他自己所言,自己过去也常常会产生幻觉。然而,阿斯顿虽然话语结巴,但好像思路却又是十分清晰。或者,他说这些只是为了拉拢外来力量戴维斯,搏取他的同情,让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一边,以共同对付弟弟米克。由于阿斯顿的过去的病人的身份和他具有拉拢戴维斯的动机,他的叙述是不可靠的,观众对于阿斯顿这一节外生枝的疾病难下定论,而阿斯顿这一故事的效果怎么样呢?能否会引起戴维斯的同情?戴维斯还会按照原来的思想行动,即要跟米克站在一边以巩固看管人的位置吗?对于阿斯顿的行为,米克又会采取什么反击措施?由于这一疾病叙述给戏剧情节带来不确定性,情节的向前稳定发展受到破坏,剧情有了多种诠释的可能,引起了观众更多的悬念,从而推动着剧情向前发展。
品特戏剧中的疾病还常常出现在戏剧的结局部分,成为戏剧发展的高潮。所谓的“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指“本身自然地承继它者,但不再接受承继的部分,它的承继或是因为出于必须,或是因为符合多数的情况。”[104]亚里士多德的结尾论意味着“尾”是一个解结过程,至此所有的事件谜底已然解开,情节不再发展。然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尾”却是一个打结的过程,是前面部分所有线索的收拢。例如特罗洛普在他的《养老院院长》中这么说道:“故事到此为止,剩下的只是把这个故事分散的线条收拢,打成一个适当的结。”[105]然而,无论是打结或是解结,都不能准确概括品特戏剧的“尾”,品特戏剧的“尾”通常既没有完全解开“结”,也没有打上“结”,是戛然而止的“尾”,开放式的“尾”。以《房间》为例,在结局部分,目睹赖利被伯特击杀在地,罗斯双眼致盲了。根据艾斯林,品特戏剧所呈现的只是一个意象,而不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完整情节。那么,赖利的死亡、罗斯的致盲正是全剧的核心,而之前各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为这一意象作铺垫,所有的线索最终都将聚集于这一时刻,疾病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而在《生日晚会》中,在最后一刻,斯坦利神情呆滞,失去了眼镜的他双目空洞,口不能言,被麦肯恩和戈德伯格用轮椅送上了的黑色的轿车。然而即使如此,这种结局也是没有结果的结局,疾病在情节推动上还要再送观众一程。罗斯致盲了,但她与伯特的关系会怎么样呢?等待她的又会是怎么样的命运?同样,被送上了黑色的轿车的斯坦利将会被送到什么地方?他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呢?虽然,评论家们给出了种种臆测,但是,这些也只能是臆测,一千个观众就可能有一千种解读,连品特本人也不知道接下来情节会怎么样发展。观众的印象还停留在疾病那里,并将为人物的命运作出不同的预测。正如品特在诺贝尔奖授奖演说中说过的那样:“我的创作往往由一行话、一个词或一个意象引起……正如我们的人生,开始的时候,我们永远不知道结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艺术的语言是高度暧昧、模棱两可的事:是流沙、是蹦床、是冰封的水池。”[106]正是品特的这种创作观,使他的戏剧的情节获得无限的推进。
其实,如从修辞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品特戏剧的这种结尾却是再正常不过。修辞叙事学将读者看作叙事交流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将“疾病”放置于故事的结尾,构建开放性的结局,是作者实现通过文本,与读者交流的目的,而不同维度的读者能从故事中读出各种意蕴,使作品具有多种阐释,则正体现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二、疾病推动主题意义的彰显
首先,疾病叙述视角(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Illness)促进了主题意义的彰显。疾病叙述视角是指以疾病作为叙述焦点切入主题。艾斯林认为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等其他文学流派的区别之一在于用“非理性的形式表现非理性的现实”。在品特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作为荒诞派剧作家的他以“病”表“病”是理所当然的。因而病态这一主题深入了他的剧作的肌理,形成了各种文本的向心力,构建了叙述框架,成为他的戏剧着力反映的内容。疾病形成极强的形式动力,参与构筑着他的戏剧的整体的叙述方式、形态、风格。其实,以“病”表“病”的表达方式在品特的第一首小诗《英国中部的新年》中便已呈现了。在诗中,品特先是描绘了一个妇女:
她一面唱着“天国之歌”,
一边摆动着她的假肢,
就像洪水中漂浮的丁字尺。
(英国中部的新年,第3~5行)
诗中的人物在继续前行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个男人:
黄色的酒吧就像狭窄街道边的垃圾箱,
我们到达那里,
发现一个瘦骨嶙峋的奇怪老人,
苍白、绝望的眼神、还穿着雨衣,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107]
(第9~13行)
在诗中,残疾的妇女与病弱的老人被品特选作了表意形象,戴着假肢的妇女就像水中的木头随波逐流,而瘦骨嶙峋、苍白绝望的老人在风雨中怀念过去,他们病态的外形象征着他们孤独绝望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是孤寂的、落漠的,本来应是吉祥喜庆、充满希望的新年却毫无生机,品特用寥寥数语勾勒出来的病态人物便映射出一个凋敝的荒原英国:人们精神空虚、渺无希望,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耗费时光,人生毫无意义,直至死亡,疾病视角的选取成功的展现了主题意义。
赫伯特·马尔库赛( Herbert Marcuse)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108]病态的社会由病态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构成,而病态的社会环境形成了病态的人际关系。为了书写这种病态,在品特的戏剧中,描述了大量的这种病态社会环境。例如反映在政治上的官僚主义、政治迫害、战争杀戮、种族歧视;反映在经济上的恶劣的居所、拮据的生活;反映在精神状态上的信仰缺失、伦理丧失、道德沦丧;反映在人际关系上的互相欺骗、互相陷害、利益争夺。正是基于展现病态社会主题的需要,引发了这些叙述,成为了品特戏剧中常见的意象。例如在《温室》一剧中,官僚主义是明显的主题,为了突显这一主题,品特展现了以治疗病人为职责的疗养院,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疗养院并非人们心目中的医疗机构,里面却像一个小型衙门,官僚习气严重、等级森严却又管理混乱。即使只要随便改动就有利于病人的措施,领导阶层却不愿施行。例如,有职员提出该疗养院以监狱的方式,以号码代替病人的名字不妥,因为这些人是病人而不是囚犯,最高行政长官———院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他却以这是前任院长颁布的条例为由拒绝改动。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所里,管理混乱,理应照顾与救治病人的职员们却从不履行医生的职责,他们所做的只是将病人区与职员区隔离,将病人区的大门紧紧锁住。而在疗养院里,一个病人6457与职员有染,生下了一小孩,而另一病人6459 在院中死亡,职员却使用欺骗的手段,敷衍病人家属,隐瞒病人死亡的信息,并责怪家属探视不足,将家属哄离了疗养院。院长知道了这些事情后,采取的措施就是极力封锁消息。更严重的是,疗养院里的职员们为了权力和利益,互相陷害。最后诚实的员工兰姆被电击至精神病,口不能言,被陷害为渎职的职员,成为了牺牲品。而院长本人也与情人在床上这一微秒时刻被杀死,职员升任院长。在这里,品特展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病态世界,他所选取的地域是疗养院这样一个疾病医疗场所,主要是以行政管理高层与职员之间的病态关系、职员与病人之间的病态关系、职员与职员之间的病态关系作为叙述视角。这些疾病叙述视角的选取,有力地实现了展示病态世界主题的目的。
其次,疾病叙述声音( Narrative Voice of Illness )推动主题意义的彰显。费伦认为在代理作者与文本现象处于一定张力之处,可以聆听到“隐含作者”的声音。[109]“隐含作者”既然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那么他代表的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意义。费伦所指的声音并非日常所说的物体震动所发出的响声,他说:“声音是叙事的一个独特因素,与人物行动等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对叙事行为所提供的交流却有自己的贡献。”在费伦看来,声音具有四个特点:1.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体现象。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声音。2.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3.叙述者的声音可以包含在作者的声音之内,从而创造了“双声话语”。4.声音存在于文体和人物之间的空间中。当把社会价值和个性赋予声音时,我们是在把声音从文体的领域移向了人物的领域。[110]费伦认为一方面,真实作者的意图隐藏在文本的建构当中,以隐含作者的声音出现,而文本的发展方向却与隐含作者的声音相背离,形成了某种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形成之处,可以聆听隐含作者的声音,也就是真实作者的意图。聆听隐含作者的声音也就是相信一种“作者式阅读”:读者与作者共同认为叙事作品存在的目的就是以某种方式打动读者,于是读者接受作者的邀请,按照特定的社会规约来“默契”作者的意图、“还原”文本声音调配者,也即是隐含作者全部的意识形态。
上文所提及的《月光》中,虽然安迪与贝尔的声音不会完全等同于品特的声音,但在如何对待重病的亲人这一认识上,他们的声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真实作者品特的声音隐藏在叙述者安迪与贝尔的声音之后。在安迪与贝尔看来,跟重病在床、即将死亡的亲人见上一面,是人伦常理,代表某种约定速成的社会规约,他们的行动代表着文字的发展方向,因而安迪与贝尔在此方面的行动就是隐含作者的声音。为此,安迪迟迟不肯咽气,一次又一次询问妻子联系的结果,而他的妻子一遍又一遍地给儿子打电话。然而,他们的两个儿子的行动却令人难以置信。
(电话铃响了,杰克拿起电话。)
杰克:这里是中国洗衣店。
沉默
贝尔:你爸爸病得很重。
杰克:这里是中国洗衣店。
贝尔:你爸爸病得很重。
杰克:我能让我的同事来接你的电话吗?
弗雷德:这里是中国洗衣店。
停顿[111]
为了拒绝跟父亲见面,安迪的两个儿子干脆采取了假装陌生人的手段,阻断了与母亲的正常交流的渠道,让母亲的正常诉求失去附着对象,而在家中,他们的父亲却正在苦苦等候:
安迪:他们在哪儿?我的儿子们呢?宝宝们呢?我的女儿呢?
停顿
他们在外面等着吗?你为什么让他们在外面等着?他们为什么不进来?他们在等什么?
停顿
发生什么事了?
停顿
发生什么事了?[112]
与安迪的苦苦等候相一致,贝尔在安迪的再三追问下也不忍心说出儿子没有回来的事实,他与安迪在如何对待患病亲人方面有着相似的伦理认同,他们的声音包含在真实作者品特的声音中,同时又属于作为文本发展方向的隐含作者的声音,是双声话语。杰克与弗雷德拒绝探视身患重病的亲人的行为代表着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与文本发展方向———隐含作者的声音发生了冲突,代表着另一种伦理认识,从两种声音所形成的张力中,读者可以轻易从中读出真实作者的意图:对于社会中亲情伦理丧失的谴责。品特巧妙地利用疾病叙述声音,彰显了戏剧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