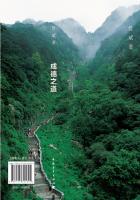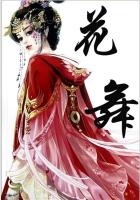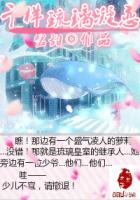在1916—1917 年冬天,首先在欧洲,接着在全世界曾经蔓延过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疾病表现出诸多的形式:精神错乱、狂躁、恍惚、昏迷、睡眠不醒、失眠、焦躁、帕金森症状。最终这种病被伟大的医生伊卡诺玛( Constantin Von Economo)识别并命名为脑炎,或者睡眠症。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大约500万人成为该种疾病的牺牲品,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虽然部分幸存者毫发无损,但大多数却陷入了睡眠的状态。最严重的那些病人长期进入了单一的睡眠状态,他们一动不动,不言不语,对周围环境毫无知觉,被安置在收容所或其他医疗机构中。
50年后,随着一种非凡的、叫做L-DOP A的药物的发明,他们得以康复。[45]
乍一看来,品特的这一段说明几乎就可以证明他进行疾病创作的原因———作家目睹疾病。然而,仔细探察却发现了其中的不可能,1916 至1917年,品特还没有出生呢,他是不可能目睹这样的疾病的,显然,他的这段说明只是让读者或观众进入戏剧情境的导引而已,并不代表着品特经历了世界的重大疫情。因而,品特由于目睹疾病从而进行疾病创作也是缺乏充分的证据的。那么,品特是否是病人呢?从其生平介绍资料中也几乎难以寻觅他身患重病的记录,虽然,最终品特不幸死于癌症,但那时他的创作时期已经结束,癌症几乎与他的创作没有关联。那么,是什么驱使他以疾病作为文学构件呢?仔细搜寻品特的人生历程,发现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个病人,只不过,他患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理疾病,而是病在“心”里的创伤性疾病。
1967年,品特在接受《纽约客》( The New Yorker)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起他的童年生活环境:
我住在西斯尔韦特( Thistlewaite )路的一间砖房中,那儿离克拉普敦池塘不远,河上面经常有许多鸭子,这里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地,到处是破败倒塌的维多利亚式房子,附近的一间肥皂厂发出难闻的臭味,这儿还有铁路车场,有商店,但是沿着路向前走不远就是黎河,它是泰晤士河的支流,如果你沿着黎河走两里路,你就会走进一片沼泽,那里有一条肮脏的运河。那里也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工厂,巨大的脏兮兮的烟囱,废水全排到了运河里面……我母亲是总是在家做饭,我父亲工作非常卖力,他每天工作12小时,在店里做衣服,但他终于还是失败了,不得不替别人做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个守夜人。[46]
破败杂乱的房屋、令人讨厌的肮脏的工厂、臭气熏天的运河、艰辛度日的父母,品特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了无生气、阴暗色调的画卷,这就是品特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环境的印象。这种环境是典型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从品特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厌恶与抵触的情感,看得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环境的极端不满。然而在品特看来,他的童年仍然是快乐的。一方面,这是由于父亲的努力工作,家庭生活条件相比之下尚可,品特的母亲没有外出工作,专门在家照顾品特一家,作为独子的品特倍受父母的疼爱。品特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他的叔伯阿姨们经常在一起聚会,让品特时常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另一方面,品特的家中有一个后花园,品特将它当成了个人的领地,在其中度过了快乐时光。对此,他说道:“我不知道,如果我有兄弟姐妹的话我的生活会怎么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在我的后花园里常常与一些自己创造出来的、想象中的朋友相会。园里有一株丁香树和一个拱门,穿过拱门就是未经打理的花园。我把那当成了自己的乐土,在那里与那些看不见的朋友相会,他们当然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但肯定都是男孩子。我的心中充满了奇思异想,在丁香树下大声与他们交谈。在花园的后边,也有一个洗衣间,我常常随着洗衣间的声音展开我的想象。”[47]这里,是品特的私人伊甸园,“代表了品特情爱、温暖和安全的天堂”。[48]然而,这种快乐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品特的伊甸园成了失乐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品特所在的哈克尼区属于疏散地区之一,九岁的品特被送到了伦敦郊外大约400公里的一处乡村躲藏,远离父母的孤寂生活对于本来尚沉浸于父母之爱的儿童来说,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于某些孩子来说,远离了安全家园及母爱,是一个创伤及痛苦的经历,当然对于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来说,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农村生活的机会,品特是二者兼而有之。”[49]成年后的品特回忆起在伦敦郊区的这段经历时,唯一的印象就是“孤单、迷惑、隔离及失落”,[50]这种痛苦不时被伦敦传来的噩耗加剧,品特的一个好友的父母就是在伦敦的大轰炸中丧生。根据品特所言,品特当时的感觉是离开了父母与死亡意味没有什么分别。即使偶尔的团聚又会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分离。轰炸也造成了品特一家生活的困难,品特父母甚至难以支付乘火车的费用来看望品特,因而少有的见面弥足珍贵。品特记得有一次,当父母看望完他在公共汽车站台等车时,自己忍不住又回过来,父母也向他跑去,一家人沉浸在分离的痛苦中。多年以后,当品特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安东尼亚·弗莱泽( Antonia Fraser)故地重游时,他对这段经历如此描述:
我对童年的印象是黛绿色、瓶绿色、黑色的树干,巨大的花丛,沿着公路,一大圈的绿色,突然,天空被拉上了帘子,远远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好大一块窗帘,接着又是黑色和绿色的石头再次遮住了视线,被关闭在城堡里,被关闭在城堡里了,长长黑夜,飞溅的浪花,痛苦、陌生、隔离……[51]
“黛绿色、瓶绿色、黑色”,品特印象中的童年是一幅暗色调的图画,缺乏轻快明亮的色彩,显然,“痛苦、陌生、隔离”代表了品特对童年的印象。
不久后,品特从乡下回到了伦敦,他经历了大部分的伦敦大轰炸时期。“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袭来,警报声不绝于耳,一种极其危险的生活,随着敌机的来临,伦敦实行灯火管制,冬天的伦敦,5点已是一片漆黑,只是不时看到炸弹爆炸的闪光及发出的沉闷声音”。[52]更令品特终生难忘怀的是,1944年的一天,14岁的品特回到伦敦,在大街上第一次目睹了炸弹呼啸而过,有一次,他打开家里的后门,看到家里的后花园燃烧成一片火海,品特的伊甸园彻底被破坏了。品特认为,这一段经历使他一下子成长起来,多年后,他写道:“我不再是一个孩子,我开始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53]比灵顿认为,伦敦大轰炸这段时间留给品特的是“生与死的强烈体验,害怕和恐惧是他当时的主要记忆,也是品特最初对于这个世界的印象”。[54]战争造就了品特童年的创伤。
品特的另一创伤来自于他的犹太人身份。品特是犹太人后裔,一种说法是他的祖父们来自于葡萄牙或是西班牙,他的姓“Pinter”最初便源自葡萄牙的犹太人姓氏“P into”,但根据品特的父母回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波兰的德系犹太人。然而,无论哪一种来源,都印证了品特的犹太人后裔的身份。对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一次,在回答评论家米莱亚·阿拉盖( Mireia Aragay)的采访时,品特予以了确认:“我不是严格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记得上一次交宗教会费,是在我十三岁参加成人礼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除了参加一两场婚礼和葬礼,我再没参加过犹太人的集会,可我仍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作为犹太人这能说明什么,也没人知道,我只知道,作为犹太人,这不说明我赞同在以色列发生的一切,反而是我对所发生的深感悲痛。”[55]
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苦难史,一世纪时期,罗马人攻入耶路撒冷,犹太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国家,居民四散奔逃,从那时起直到1948 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一千多年来,犹太人历尽艰辛,他们犹如无根的浮萍,在世界各地四处漂泊,四处遭受排挤打击和驱逐杀戮。作为犹太人的子孙,品特不但对祖先的苦难历史难以忘怀,对其中的滋味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品特居住的伦敦东区是一个外来人员的聚居地,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从20世纪初便来到了这里,一战后尤其是二战后,更多的外来移民聚居于此。伦敦东区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犹太人、中国人、爱尔兰人、非洲黑人等的多民族混居区。外来移民饱受当地人的歧视,在当地的一些小区,常常挂有“外来移民禁止入内”的牌子。由于当地人员成分复杂,这里充斥着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多年以后,当品特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他说:
每个人在那儿都会遇到暴力。二战后,我在伦敦东区就确实碰到过一次。当时,法西斯在英国正处于猖獗时期,我也有好几次卷入了斗殴之中。当时,只要你看起来稍稍有点儿像是犹太人,你可能就会有麻烦。有一次,在我去犹太人俱乐部的路上,在一处铁路拱桥边,有一些人手里拿着弄破了的牛奶瓶,等在那儿,摆脱困境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用身体跟他们拼杀,但我们是没有办法对付他们的,他们有牛奶瓶子,我们却没有。另一种办法是走过去对他们说些什么。你知道,就是“你好吗?”“是啊,我很好。”“喔,这样啊,那很好啊,是吗?”这些,说着说着就朝着有灯光的大路上拼命地走着。……在那时,暴力事件实在太多了。”[56]
可以看出,在作为犹太人的品特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不公平的、充满敌意的世界。品特就像一只惊弓之鸟,在高空惴惴不安地、孤独地飞翔,充满了生存的焦虑。品特觉得这个世界对犹太人极其不公正,他多次表达了对德国纳粹的谴责和对以色列的同情。根据品特的第二任妻子安东尼亚·弗莱泽的回忆,有一次她与品特一同受邀参加晚宴,她当时与品特分开就座,突然她发现品特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开始,弗莱泽还以为是有人提到了萨尔瓦多。后来才知道,是一个酒醉的老人发表了一大通的关于纳粹主义的谈话,然而他言内之意并非对纳粹进行谴责,而是指责犹太人引起了战争。品特非常生气,与这位老人争论起来,宴会气氛搞得十分难堪。当然,受到众人指责的是那位酒醉的老人。弗莱泽后来回忆道:“品特告诉我,最难过的时刻是听到某些人谈论起纳粹,他哈罗德·品特,是犹太人,这是关键之处。”[57]在作为犹太人后裔的品特看来,这个世界对于犹太人是不公正的,而作为犹太人,命运是苦难的。犹太人的身份也是造成品特创伤的一个原因。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如果人们经受了诸如战争和重大事故之后,如果不能应付强烈的情绪体验,便会形成‘创伤性神经病( Trauma Neurotic) ’ ,这种病症主要表现为对创伤当时情境的执着,病人无法从中解脱。”[58]品特屡屡不忘童年战争记忆,一提到犹太人的遭遇时便情绪激动,表现出对事件的缠绕执着,症状完全符合弗洛伊德所谓的“创伤性神经病”,可见,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一个创伤性神经病人。对此,学者蒂盖尔特尼等人也持有类似看法。[59]“疾病是一种早期的老龄,它教给我们现世状态中的脆弱,同时启发我们思考未来,可以说胜过一千卷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述”,[60]品特所经历的创伤是他人生的强烈体验,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思维空间。弗洛伊德后来在提到潜意识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时再次指出:“人们童年经受的强烈刺激如遭压抑,就会隐藏于他的潜意识,在他长大成人后,如遇合适的刺激,这种压抑就会释放出来。对于普通人,他们可能通过言语叙述或是某种行为进行释放,对于作家而言,这种压抑的释放则往往会通过创作进行。”[61]依据弗洛伊德,那么可见,正是品特早年所遭受的创伤痛苦体验成为驱动他进行疾病书写的内驱动力。
二、和平斗士品特
1988年,品特对记者高索说:“我知道你喜欢叫我剧作家,但是我对自己是公民这一点更感兴趣。我一直在说,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中,但是我们都期望能够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准确地说出我们心中所思考的是我们的责任。”[62]品特所说的“公民”是有历史内涵的,其最初来源于古代雅典共和国,当时,雅典共和国的“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均由其产生,公民在雅典共和国拥有很高的地位,20 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可以在大会上自由发言和展开激烈的辩论,据有广泛的参政议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