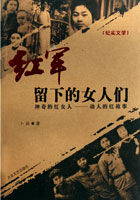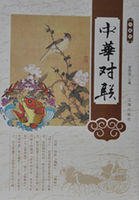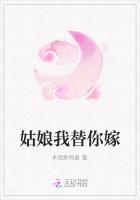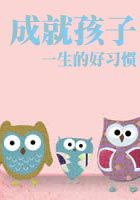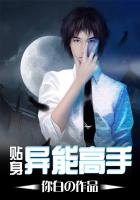品特戏剧中出现的第二大类疾病是精神疾病,这些疾病主要有:
焦虑症。焦虑症是品特戏剧中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意象。一种表现为喋喋不休、不能安静的场面。例如《房间》中的老妇罗斯,《生日晚会》中的梅格等。另一种表现为各种心理暗示,由于受到外界莫名的威胁,人物往往会采取各种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是给别人造成伤害,或是使自己致病。例如由于对外界威胁的焦虑,《微痛》中的爱德华最终伤害了自己,双眼致盲。又如《送菜升降机》中的杀手高斯和本,由于对于生存的焦虑,互相欺骗。品特戏剧中还存在着俄狄浦斯式的焦虑,人物因为对于母亲的争夺而发生冲突,例如《归家》中的父子们因为露丝而互相冲突。
分裂症。分裂症是精神病症的极端形式,往往表现为人物精神崩溃,失去理智。例如《生日晚会》中的斯坦利在两个跟踪者的盘问之下,语无伦次,精神错乱,意识处于分裂状态。
强迫症。强迫障碍简称“强迫症”,是以反复出现强迫观念为基本特征的“类神经症性障碍”。[30]强迫行为是指反复出现的、呆板的仪式动作,患者明知不合理,但又不得不做。往往是作为减轻强迫观念引起的焦虑不安而采取的顺应行为,以强迫检查和强迫清洗最常见,常继发于强迫怀疑。[31]《房间》中的罗斯由于担心安全,老是怀疑门外有人,于是反反复复地到门边去查看,表现出一种强迫状态。
偏执狂。偏执狂热是指“偏执狂”又名“妄想狂”。本病特点为“逐渐发展的一种来自内部原因的持久而不可动摇的系统妄想,其思维过程清晰有条理、意志活动保持良好”,患者的妄想有一定的现实性,易被人当成真的是这样。开始常以被害妄恕为主,以后可逐渐出现夸大妄想和嫉妒妄想,以男性多见。[32]例如《房间》中的伯特一见到黑人赖利就将之杀死,表现出一种对黑人认知的偏执。
创伤后应急障碍,是个体对异乎寻常的威胁性、灾难性事件的延迟和持久的心里反应。异乎寻常的创伤性事件(如自然灾害、战争、严重事故、目睹他人惨死、身受酷刑等)是发生本病的自接原因。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但有部分人最终成为创伤后应急障碍的患者。[33]患者以各种形式更新体验创伤性事件,有驱之不去的闯入性回忆,频频出现的痛苦梦境。有时可见患者处于意识分离状态,持续时间可从数秒钟到几天不等、称为“闪回”。此时患者仿佛又完全身临创伤性事件发生时的情境,重新表现出事件发生时所引发的各种情感,患者面临、接触与创伤性事件相关联或类似的事件、情景或其他线索时,通常出现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生理反应。[34]《看管人》中的阿斯顿,由于此前在精神病院受到过电击,于是只要一见到电击用的钳子,便会全身发抖,极度害怕,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创伤后遗症。
虐待变态。虐待变态分为施虐狂和受虐狂。施虐狂喜欢以虐待别人为乐,虐待方式可能是精神上的,也可能是肉体上的,目的都在于使对方遭到痛苦和羞辱,从而从中获得心理满足,究其原因,可能是患者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从而希望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虐待的行为主要产生于自卑心理。《送行酒》中的尼古拉斯老是在韦克特面前挥舞着皮鞋、拳头,让别人轮奸他的妻子,杀死他的儿子,表现出的就是这种虐待狂热。虐待变态往往还与性相关,尼古拉斯让别人轮奸韦克特的妻子显然就是性虐待变态。虐待变态的另一种病症是受虐狂,这类患者通过忍耐肉体或精神的痛苦,从而获得快乐。弗洛伊德认为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是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自己好过一些。《归家》中的露丝,以能同时为丈夫一家男人、甚至还为外人提供性服务为乐,《归于尘土》中的丽贝卡喜欢情人用手扼住脖子产生的快感,这些均是受虐狂的表现。
品特戏剧中出现的第三大类疾病是损伤性疾病,品特戏剧中的损伤性疾病根据损伤的部位及后果可分为:
四肢伤残。病人受到外界力量伤害,肢体受伤。例如《山地语言》中的老妇,由于受到了监狱豢养的狼狗的撕咬,手臂鲜血直流。
全身损伤。病人全身均受到了外界力量的伤害,伤痕累累。例如《山地语言》中的萨拉的丈夫,受到了刑讯,浑身上下青紫。《送行酒》中的韦克特也是如此,同样的还有《新世界秩序》中的犯人,被折磨得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损伤致死。品特戏剧中的一些人在外力的重创之下,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生命丧失。例如《归家》中的赖利,在遭到伯特先用椅子敲击,后又将头踢向煤炉的残忍对待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已经死亡了。
品特戏剧中的病人多种多样,疾病种类纷繁复杂,让人仿佛置身于大型综合性医院。这里的某个病人身上可能只有一种疾病的症状,有些病人身上却可能是多种疾病症状的叠加,让人眼花缭乱。大致说来,疾病在品特戏剧中出现的情况如表1-1。
表1-1 品特戏剧中的疾病一览表(此表为论文作者自制)
剧 目 病 症
《房间》 失明症、损伤致死、焦虑症、失聪症、偏执狂、强迫症
《生日晚会》 失明症、失语症、焦虑症、分裂症
《微痛》 失明症、焦虑症
《温室》 分裂症、偏执狂
《看管人》 分裂症、强迫症、创伤后遗症
《送行酒》 全身损伤、死亡、虐待变态
《山地语言》 失语症、肢体伤残、虐待变态
《一种阿拉斯加》 睡眠症、失忆症
《新世界秩序》 全身损伤
《茶会》 失明症、分裂症
《月光》 未命名的疾病
《归于尘土》 分裂症、虐待变态
《侏儒》 肢体伤残
《归家》 休克症、瘫痪症、虐待变态
《情人》 性变态
《背叛》 性变态
《一夜外出》 焦虑症
第二节 品特的疾病叙述动力
所谓叙述动力( narrative drive) ,是指叙述的发动和推动之力。由于品特的人生创伤及生活体验所形成的苦难意识,在他的戏剧中,疾病被选择成为了语言的构件。
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热议的话题。传统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通常持作者决定论。例如贺拉斯认为,要想写出好诗,诗人就要修身养性,保持良好的品格。[35]郎吉努斯则指出“崇高是伟大灵魂的反映”,[36]文学作品要想实现崇高,首先作家要具备崇高的心灵。哥德则说得更是明白:“作家的风格应该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一个人要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若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种“文如其人”的人格影响风格论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坛占有广大的市场。直到20世纪上半叶,新批评学派才对作者决定论提出了质疑。被视为新批评思想先驱的艾略特在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了“非个性化论”,他强调:“艺术情感是非个人的……艺术的过程就是自我牺牲的过程,是隔绝个性的过程。”[37]换言之即作品只是客观的象征物,与作家无关,诗人的感情要想进入作品,必须转化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感,诗人要想诗歌创作成功,首先就要放弃自己。新批评学派所持的理论称为文学本体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活动的本原。文学研究要以作品为本体,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研究文学的特征。1961 年,经典叙事学家布思出版了《小说修辞学》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区分,认为小说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隐含读者”而非“真实作者”,“隐含作者”是指“以特定方式写作的人”,是“以特定面貌写作的作者本人”是现实作者的“第二自我”,以文本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意图。[38]依据布思这一说法,真实读者似乎就是多余的,因为从文本中的隐含作者那里,真实作者的意图已经得到体现。借用另一位修辞叙事学家查特曼的叙事交流图(见图1-1) ,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 ……真实读者[39]
图1-1 查特曼叙事交流图(Chatman,1978:151)
在这个叙事交流图中,真实作者被排除在方框之外,并且与方框和虚线相连,表明了二者之间不存在实质的直接关系,作为创作者的真实作者与文本无关。1968年,罗兰·巴特甚至发表了《作者已死》一文,将作品决定论推向了极端。他认为作品在完成之际,作者就已经死亡,剩下的文本解读工作,就是读者的权利了:“唯有作者死亡,读者才能诞生,所有阅读活动,都是读者心灵与一个写定的‘文本’的对话,价值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40]作品中心论将文学批评从作家核心引导至作品核心,从关注作品的外部形式转变至关注作品的内部形式,强化了对语言的关注,这对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文学本体论完全切断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现实生活乃至作者、读者及其审美心理的一切联系,将文本作为一个完全封闭的本体来研究是从一个极端转至另一个极端,不免过于绝对。在关注作品本身的同时,作家的重要性也不能忽略。这种声音在文学批评界从未完全消失。随经典叙事学之后发展起来的后经典叙事学就重新认定了作者的作用,认为作者的社会历史语境会对作者的创作产生影响,作者、文本、读者共同构成了叙事交流。新历史主义的崛起更是对文学本体论的一种反拨。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作为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叠的历史过程,文学作为诸多因素诸多环节的多向运作,文学与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双向交互作用和永无穷尽的多样性阐释的效应史等,决定了文学不可能局囿于本文的封闭体系之内。”[41]虽然,新历史主义并非意味着作者中心论的原样回归,但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作者的作用。例如米歇尔·福柯在他的《作者是什么?》一文中,在认定文本本身具有建构性的同时,认为文本作为一种知识,是社会上各种力互相作用的结果,作者在文本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作者的名字不只是一种词类成分(如一个主语,一个补语,或一个可以用名词或其他词类代替的成分)。它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因为它用作一种分类的方式。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一个名字还在文本中间确立不同形式的关系。”[42]福柯的意思是作者并非消失不见了,而是已分散在各个文本载体之中继续发挥着功能,文本的选择构建仍然离不开作者。传统的作者决定论过份高估作家作用,与形式主义将作品与作家完全割裂都过于极端了。文本在脱离作家后会重构意义不可否认,作家的作用也不可以完全否认,作品终究是作家创作的,某种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作家的人生经历总会在作品中留下痕迹。处于后现代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品特向来反对文本诠释,在诺奖获奖演说中,对于作家与作品,他说了这样一些话:“作家的处境是非常奇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受人物欢迎,他们也不容易相处,他们也不大可能界定,你当然也不大可能向他们发号施令。”[43]品特的意思是文本中的人物一旦创造成型,就具有了生命,会自己呼吸,作者就是多余的了。在此之余,品特还极力否认自己的戏剧创作有政治、宗教背景,认为自己的创作只是由一刹那间的灵感所触发。然而,还是有那么一两次,他承认了现实生活对他创作的影响。有一次,当记者问起品特写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时,品特这样说:“每个作家都大致这样做,要不然我们写什么?我们所写的东西往往与自己相关,或是与自己观察的现实相关。”[44]又有一次,品特说道:“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放弃对于我创造的人物的责任,相反,我为他们负责并对他们负责。戏剧自我发展,但是坦白地说,它们是我写的,有目的的、充满敌意的、针对性很强的,我掌控着它们的发展。这是否跟我以前所说的自相矛盾呢?好极了! 这种掌控其实是不够严格的,也不够明白的,但是谁说的我一定要为明白而努力?”1对此,比灵顿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说品特的戏剧都是自传性质的,但是它们毫无疑问与品特曾经观察到的景象及其人生经历相关。”2显然,创作过程中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不容回避的,出自于作家之手的作品不可能是天外来物,作家意图至少在作品选材、文本选取及作品结构构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剧作家品特的人生经历当然对他的戏剧创作也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情感力量驱使他以疾病作为介质,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人生观念、创作思维等。
一、品特的“心”病
亨利·西格里斯特在探讨疾病与文学的关系中总结了疾病写作的三种原因:作家目睹疾病内心产生强烈的震动写作疾病;作家患病进行身体写作;医生作家记录病人状况或是医生具有创作爱好。3显然,品特并非医生,创作之前也不曾有过行医的经历,他不可能是弗洛伊德之类的医生作家。1982年,在戏剧《一种阿拉斯加》的戏剧说明中,品特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