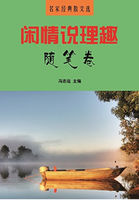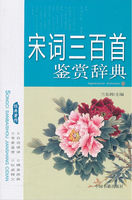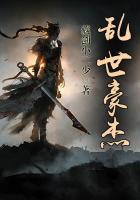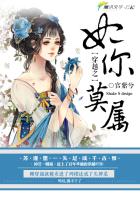抗战年间,丰子恺居住在重庆沙坪坝,先到国立艺专执教,后因人事纠葛辞职,以卖画为生,兼写散文。
早在“五四”时期,丰子恺就以文名和画名并重于文化界,被誉为一代新文人。他的散文清新隽永,自成一体,看似平淡却耐人寻味,所著《缘缘堂随笔》曾多次再版。同时,他对漫画艺术的造诣颇高,自20年代起就为上海多家杂志提供封面及插图,画面生动简约,尤以描绘儿童形象见长,深得读者喜爱。
迁到沙坪坝后,丰子恺自费建起平房数间,取名“沙坪小屋”,其所作画幅皆署名“缘缘堂”,待价而沽。有达官贵人上门求购,则索以高价;有文化界朋友慕名求画,则只取工本费,或有干脆无偿赠予。至于他珍藏的抗战前的沪版《子恺画集》、《子恺漫画》、《护生画集》、《漫画阿Q正传》等则秘不示人,只对极少数知音展示,看过便要仔细收藏起来的。
为了体现自己的风格,他亲给版式,设计出“缘缘堂”画笺,交给一位擅长细活的木工刻版,以便翻印。殊不知木工一见画笺的四条边线弯弯曲曲,竟用木尺校平,自以为办了件好事。
丰子恺收到版模就说:“这不是我设计的版式,我不要了,请你另刻个模子,我加倍付钱。”
木工大惑不解,急忙分辩说:“我见丰先生的样稿边线不直,这才用角尺重新画过,本是一片好心呀。”
丰子恺笑着说:“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不过你不该改动图样。你做木工靠直线卖钱,我却要靠这几笔弯线卖钱,改动后我的画就卖不掉了。”
木工恍然大悟,回去另刻了木模送来。
抗战方殷,物力很难。一日三餐,油盐酱醋,旷日持久,虽无壮烈可言,却也难尽个中滋味。丰子恺笔下的弯曲,实在也有避祸的思想。
某日有两位新贵来访,口中对丰子恺表示非常的仰慕,频频称赞他的画寓意深刻。当翻看到《夕阳无限好》时,那人突发奇想,说这幅画是暗喻国民政府的日子不长了。
丰子恺听了啼笑皆非,并深感不安,这种牵强的附会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玩笑,此人显然居心叵测。他乃正色答道:“先生过奖,我画的是风景,题词借用的也只是一句古诗,并没有什么刻意的影射。”
俟客人走后,他立即将这幅画束之高阁,以免惹事生非。他遵从“贫贱不能移”的古训,自有一身傲骨,本不是怯懦之人。但他知道除了维护“尊严”外还有一件事情,叫做“使命”,所以不愿戴这种高帽子,卷入不必要的风波。
丰子恺白天作画,写文章,晚上喜欢独酌几杯,聊以解乏。他是江浙人,不爱喝高度数的白酒、曲酒,惟嗜绍兴的黄酒如命。惜华东已失陷,黄酒不可得,弄得他度日如年,喉急时只能以五加皮酒充数。
有一天他上街闲逛,无意中见到一种“渝酒”出售,标明是低度数的仿绍兴黄酒。他似信非信,掏钱买下一瓶,当场品尝,觉得口感与绍兴所产相去不远,欣喜若狂。从此,他成了“渝酒”的老买主,每天晚上至少喝八两,盛夏挥汗如雨也从不间断,以全酒德。
岁月悠悠,有的同龄人被生活的利斧砍得斑斑驳驳,满脸皱纹,丰子恺却笑口常开,一杯在手,自得其乐。他的视野开阔,不囿于方寸的得失,生活的压力便无形减轻了许多。
手捧一杯“渝酒”,他眼见五个小儿女渐渐成长,升学毕业,任职攒钱,深感欣慰。手捧一杯“渝酒”,他耳闻德国投降、独夫自杀、轰炸东京、波茨坦宣言发出,坚信抗战必胜,返乡有望。他的酒量越来越大,从八两增至一斤,越喝越香。
他是个生性淡泊的人,不善交际,仅与开明书店关系密切,因该书店办有《开明少年》杂志,每期都要采用他的画稿。书店来的是叶圣陶,还有夏宗禹等人,都是文化界同仁,惺惺惜惺惺。但凡老友来,他必出“渝酒”待客,赞不绝口。
叶圣陶等人均辞以不善饮,丰子恺亦不以为意,自捧大杯向客,谈笑自若。客人下次复来,他又忘了人家不喝酒,照样又夸赞“渝酒”一番,总想劝客人多少喝一点。
抗战胜利之日,丰子恺激动万分,连日伏案创作,绘出了多幅传世之作。《八月十五日夜》,反映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陪都万人空巷,齐上大街游行狂欢的场景。《炮弹作花瓶,永世乐太平》,表达了久经战乱的中国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之情。
丰子恺在重庆的生活颇为清苦,蜀道也不平坦,但他安然处之,苦撑到1946年初才离开沙坪坝回华东。不久内战又起,民不聊生。于是,他在一篇散文中感叹道:“沙坪小屋中晚酌的那种兴味,现在是不可得了。唉!我很想回重庆去,再到沙坪小屋里去吃那种美酒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