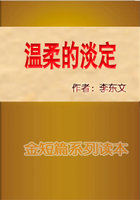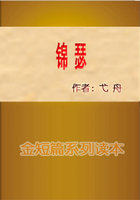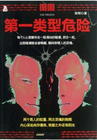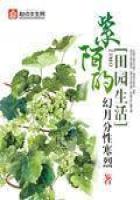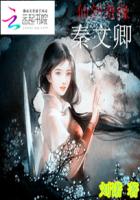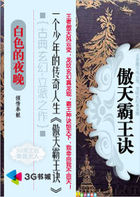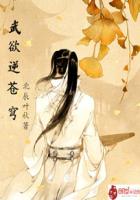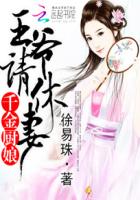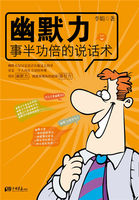小酒馆的意象让我回到风雨飘摇的1989年,那一年我正经历着生命中一段灰暗而苦闷的日子。
春天的时候我与一位满族姑娘奇迹般地恋爱。我们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邂逅的。通过交谈,我知道她从南方一所大学到山东实习,相识的第二天我们就改到床上聊天了。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在此后的许多个春天的夜晚,我们俩除了彼此相拥着聊天外基本没有其它内容,尽管男女之事当时我们都已懂得,但莫名的恐惧和对于生理常识的严重贫乏还是占了上风,它最终阻止了我们跃跃欲试的越轨行动。
聊到天快亮的时候她睡着了,那是第一个晚上。院子里到处弥漫着花香和树木散发的清新,风把世界吹得幽深而安静;透过窗外投射而来的月光,我看到她的嘴角流着一弯涎水,我低下头嗅着她的有点枯涩的头发,心里有一种甜蜜的忧伤。如今回忆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她都是个美人。但她的皮肤比较黝黑,尽管乳房不大但绝对结实饱满,腰肢光洁而柔软就像一根绳子,里面没有一点骨头的内容。她洁净的口腔始终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野薄荷的气味,每当我与她接吻时这气味顿时变成了一剂毒药,令我全身陷入半麻醉状态。这个巫气缠身的女孩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奇怪的是她的眼皮是多层次的,双了一层又一层。她特意给我表演过一次:她闭上眼睛,眼皮落下一层;眼珠在里面一转动,又落下一层。逗得我哈哈大笑。
多年过去,此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有谁长着她那样的眼皮。总之,她是个多么奇特的女孩。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她身上没有一丝虚荣心,我当时挣的钱很少,她从不介意我的贫穷,甚至从不关心我的收入。只要一下班,我们立即进入世俗之外的颠狂,到麦田里或者到野外的荒草丛中幽会,弄得全身都是尘土和草籽。当我们在每一次长吻过后,她的眼睛都涌满了泪水。我至今也没弄明白那泪水意味着什么,是痛苦还是甜蜜。有一次我们相拥着倒在野外的一个玉米垛上睡着了,结果被一阵狗腥味给弄醒了,那狗的主人正在日光下锄地,他呆呆地朝我们凝望,全然丢失了工作效率。我们只好笑一笑,不好意思地离开,站起来互相拍拍身上的风尘。她的头发上全是碎草屑,但她是多么美丽呵,那脱俗的一瞬已在我记忆中永存!还有一次,我独自倚着一棵树翻看一本书,她到灌木深处采撷喇叭花,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野猫的住所。她惊喜地跳过来,什么也不说,拉起我的手朝深草里走,我看到三只可爱的小动物,皮毛全是黑颜色。一只肥大的野猫紧紧守护着两只幼仔,母猫的眼睛里充满了警惕的光芒。
我们已经谈到婚嫁问题,按理说剩下的一切应该顺理成章。但上帝偏偏另有一番安排,——仅仅因为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事,让我目睹到一个女孩如此可怕的乖张与不通,那是人性的另一个侧面。它如果爆发的时间再晚一些,会怎么样呢?哦,我真不敢预测沉重的命运,因为命运的变数无法捕捉。这件事让我们对双方的感觉都产生了难以粘合的裂纹,分手已经不可避免。
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律师,那个小伙子我曾见过一面,是她特意领来让我“看看”的: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头发蓬乱,面部白皙而精瘦,给人一种大男孩的感觉。我记得自己当时很虚伪的朝她笑笑,说挺好,结婚时通知我一声。她答应着,但事实是并没有兑现,此后她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她与丈夫一道,到了另一个海滨城市。
几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她说:“喂,是我啊!我在你的办公楼下,有时间吗?”声音温婉中透着平静,即便她不报上姓名,我也仍能辨认出来,那一口南方味道的普通话,那洒在野地里的咯咯笑声。急忙下楼,见她身着长裙,卓尔不群地立在风中,周围散发着一种冷美。中午,我请她吃饭,在一家店面不大的海鲜馆。其间,她向我打听我妻子,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很小的照片,是在一次办理什么证件时顺手夹在钱包里的。她仔细地看了又看,笑了起来,说:“呵呵不错,我喜欢她这样子的。你真有福气。”我的脸有点发烧,急于避开这个话题:“说说你吧,日子过得还顺心吧。”
她轻叹一声:“唉,还可以……一般般吧。我去年离婚了,你没听说么?”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的消息其实很闭塞,从不打听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事情。
“哈……”她笑了,“那你靠什么写作呢?”
“靠想象,瞎编的。”我说,心想我没有说假话。“来,往事休提。干一杯。”
在酒杯相碰的刹那,我的灵魂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能清晰地听到一声脆响,心有些乱。我的脑海里顿时升起三盏昏黄的小灯,我偷偷苦笑起来了,眼里有了热辣辣的东西:哈,小酒馆!金岭镇!你还在吗?
时光的胶片在快速倒转,眼前渐渐变得一片模糊。
分手的季节正值冬天,从相识到分手,我们的爱情经历了沧桑的四季。摊牌后的那个黄昏,天空正在无端地落雪,看不清道路和行人,我跳上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大巴车,木然地坐下,把眼睛闭上,依然驱不走的是她的影子和声音,我吃惊地发现,相处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都兀自浮出水面,真实可触。相处时的每一个设计此刻都变成了谎言,让我痛感人性的多变。我很痛苦,愚蠢可笑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狗日的,值吗?你真没出息!我这样骂着自己,一边安慰着自己,急于找个方式尽快把内心的委屈释放出来。找身边的人倾诉一番显然不符合我的性格,况且我当时对“人”这一概念正心生厌恶,觉得倾诉的结果只能让别人暗自发笑罢了,而博来的同情是廉价而有失尊严。我们周围的文化环境里没有教堂,没有上帝,内心的挣扎与搏斗已经习惯了憋在肚子里自生自灭。
这时,大巴车呜呜地开动了,在苍茫的冬季黄昏,迎着一场斜飞的暴风雪缓缓滚动,好像因了一个人的愁苦而格外滞重,轮胎频频打滑。车里有很少的几位乘客,大概是上夜班的工人。人们跺着脚,口里丝丝呵呵地喷着白气,抖落身上的积雪。天太冷了,我能感受到他们上车时夹带而入的一股寒气,我的膝关节已经被冻得麻木不堪。不一会儿,售票员开始工作,在我面前停住:
“有月票吗?去哪?”
我敏感地闻到她衣服上散发出一股死耗子味,禁不住捂了捂鼻子。
我不知道大巴车开往何方,途经哪些小站。在它剧烈的颠簸中,我感到自己是个被世界遗弃的穷孩子,踏上了一艘狭窄的驳船,我把命运交给它了,我甚至隐隐地盼望着这辆车在路上出点事儿,一头栽到沟里。哈,那样就彻底解脱了。我沙哑着嗓子向售票员打听车的终点站,心想我就到终点站下车吧。终点站是一个工业区,我有点失望。但我还是掏钱买了票,至此才知道车是朝西行驶,其间要经过一个名叫金岭的小镇。我马上想好了,就到金岭下车吧。那个小镇的居民有一多半是回民,我早就听说过,只是我从未曾到过那里。但生活的一次偶然变故让我与这个永远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镇发生了神秘的联系。
我下车时天色已经黑暗了,我缓步行走,观察着周围陌生的景物:错落的房屋被雪光映照,冷冽的气息,斑驳的树影,此起彼伏的狗吠,以及屠宰的血腥味一同涌入。但似乎正赶上停电,家家户户的窗口上一律烛光幽幽,在落雪中给人一种大静与安详之美。
一切都像预想中的那样,我找到一家小酒馆坐了下来。那个我始终叫不出名字的小酒馆是个二层砖楼,外观是白灰粉过的墙壁,门两侧是两个一米多高的木格窗户,木门上垂挂着一块棕色皮革门帘。我掀开门帘后眼镜片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雾气,我把眼镜摘下来,朝衣服上胡乱擦了两下。
老板娘是个模样富态的女人,年约三十七八,她热情地把我引到一个坐位,又朝楼上喊侍女下来多点几支蜡烛。不一会儿,屋内亮了许多。屋子中央燃着一盆木炭火,木桌的摆放错落有致,桌上是一些碗碟、卫生筷子、胡椒粉、味精、醋壶、辣椒油、餐巾纸等等。我点了一个羊肉汤,一盆牛骨头,又要了一瓶当地产的低度白酒“蒲公2号”——我平时从不自己喝酒,但现在只求一醉方休。开始时是慢慢地吃喝,后来就风卷残云了。饕餮吧,妈的,人生苦短,不能委屈了自己呀。渐渐地,酒精在我体内发生作用,但意识模糊中仍然算是清醒。我看看酒瓶,已经下去了一大半,这已经达到了我酒量的极限。突然,屋子里爆出一段京剧唱腔,整个房子在颤抖: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我唬了一跳,急忙顺着声音望去,见是紧靠巴台的桌上一个约摸四十的男人眼珠正瞪得像车灯,大概醉得差不多了,他站起身来,一只脚踩着凳子,手里还拿着一根大大的牛骨头挥舞了两下。凭心而论,他的唱腔不错,嗓门洪亮悠远,与革命样板戏中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相差无几,甚至连长相也颇有几分相似。我不禁咧嘴想乐,刚才的一阵尿憋感也没有了。唱声停顿,老板娘调笑道:“大兄弟,你又喝高了?哈哈哈!继续唱,唱得不孬。”
那人却显得不好意思了,摆摆手,面带羞涩地坐下了,嘴里呼呼地往外吐了两口气。
我借着酒力,朝他举杯:“干!”
他急忙倒满杯,朝我道:“兄弟!干了!哈哈真痛快!”
事情的变化极富戏剧性,三干两干,他就招呼我凑到了他桌子上去,并且不顾我的阻拦,他又要了两个菜,一盘羊杂碎,一盘油炸花生米,我们不顾一切地喝了下去。谈的什么话题我已记不清了,大概是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全是祝福之类的胡言乱语,双方的舌头都打了卷儿。后来,我看到他双臂抱紧了头,埋到了裤裆里,我说老哥,你不行了吧?他举出一只右手摆了摆,头仍然是没有抬起来,我听到他在咯咯地笑,笑得像小女孩被人咯吱了似的:“哎呀——嗬嗬嗬嗬嗬!”
我也想笑,但笑不出。然后他抬起了头,我才吃惊地发现他满脸都是泪水。
我说:“老哥,你笑得好特别呀!”
接着我们就拥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放声大哭。哭过之后,我觉得心底的伤痛奇怪的被清除了,变得一片光明。然后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镇子,有两次摔倒在雪里。已是半夜时分,雪停了,到处是耀眼的白光。我说老哥,先送你吧,他用手指了一个方向,口吃得厉害:“我,我家就在……阿就附近。先、先送你。嗯嗯。”
于是我们约好下周再到小酒馆来,不见不散。我清楚地记得,在公路上等车的时候,他很关切地把头上的皮帽子摘下来让我戴了一会儿,我几次试图摘下,都被他用手死死摁住,他的力气可真大!后来,终于来了一辆出租,我把帽子还给他与他告别,那帽子里油腻的汗味跟随了我好多天也不肯走。
可惜,我第二天就因公出差到大连了,一去就是半个多月。此后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小酒馆,但我一直很怀念它。
(原载《当代小说》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