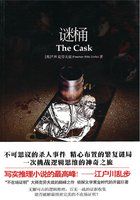一
这个小村,从来就没有这么喧嚣过。
如果不是二婶家闺女麦花回来,依旧是世外桃源般的寂静,没有风掀起什么波澜,倒是有布谷鸟围着这个小村的上空叫春,偶尔还有几声狗吠填充着这个默默的小村子。
自从有才嫁到二婶家成了二婶的合法夫妻和麦花的后爹,并充当了一阵子餐桌上的下酒菜后,街头巷尾就再也没有多大嚼头,用有才的话说都他娘的喝着小酒过着舒坦日子。
二婶闺女麦花自跟村里狗蛋偷着在草垛里睡觉后,就被二婶赶到砖窑厂干活去了,一月也不回家一次。二婶每天打发着丈夫有才到坡里放羊,有才就每天清早赶着羊群逛荡在小河岸边的草地上,不时的“狗日的操他娘的”骂那些自己亲自从母羊腚里接生的羊羔,那些羊羔吃高兴了就爬到同伴的胯上,有才看不顺眼,就甩着鞭子“狗日的操他娘的”抽这些不知羞耻的畜生,“狗娘养的,看我不把你们这些骚畜生剁巴剁巴煮了下酒”。看羊羔不再越轨,乖顺地吃草后,从裤腰里摸出烧酒喝一口,这个小日子过得舒坦极了。
有才原来是个画画的,在县里文化馆工作,听说还在县里得过大奖。后来跟一个女人睡觉,被女人的丈夫逮个正着,所有画画的家当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砸碎了,还被单位开回了家,回到生他养他的小村当农民。本来艺术家气质的有才想娶个志同道合的女孩当老婆,可在家不会种地,家里穷,正儿八经的大闺女看不上他,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子。后来经媒婆牵线,才嫁到了带着个孩子的二婶家。
之前,二婶的丈夫在石矿干活,那一年春暖花开时节,还没好好欣赏满园的春色,下井干活时石矿塌方被压在井下,连个尸体也没找着,倒是二婶接着石矿上赔偿的一千块钱,活得比原来还滋润。
闺女麦花那时还小,就苦了年轻风韵的二婶,丰满的身子像熟透了的面瓜似的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满村都弥漫着暧昧的气息,村里的光棍经不住二婶的青春荡漾,都想耕种这块免费的肥沃黑土地,深更半夜地敲二婶家的窗户,有的还在二婶家的土院墙外发着猫叫狗叫什么的暗号,魅力无限的二婶,按捺不住内心的骚动,诱惑了不少男人的身体。
后来二婶想,这样排遣寂寞也不是个办法,得想法子招进个专用的,就央求媒婆把邻村有才嫁过来,比起村里野蛮的像小壮牛似的光棍汉来,有才那东西蔫巴多了,办那事不淡不咸地,但总算有个专用的了。
有才嫁过来,起初手还痒痒,忘不了画画的好时光,有时候还背着画夹站在河边瞎涂抹,把他瞎划拉的画经常夹在院子的晾衣绳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自已的王国开画展。跟晒尿布片似的。
然而,威猛的胖二婶一边嘴里娘的狗吊样的画画能当饭吃,一边干净利落地把那些画一把捋下来填了锅灶底,尿布似的画片一溜烟爬了烟筒。有才刚要发火,张开的嘴巴就被二婶的那双肥白的奶子堵住了,干瘪的有才趴在二婶的身上云雨一翻,心底萌芽的艺术细胞渐渐熄灭了,带着一肚子满足赶着羊群跟二婶好好过日子。
这一晃十年过去了,麦花都十七岁了。
这天本来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街头一堆人甩着扑克,唱着小曲,下着象棋,生活得有滋有味,一片太平盛世。谁知,村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二婶的闺女麦花上吊了……
二
当人们在街头棋盘上杀得天昏地暗,突然传来鬼哭狼嚎的哭声,是从二婶家传来的,人们丢下棋子一窝蜂聚到二婶家院里,二婶正抱着不省人事的麦花干嚎。
门框上空吊着一根绳子。
“天杀的,俺那可怜的黄花闺女啊……”
有才在麦花嘴上鼻子上乱掐着,竟然把死了一样的麦花掐过来。
二婶见麦花醒过来,放下麦花“忽地”站起来,嚎叫着往墙上撞,寻死寻活地,有才丢下麦花又去拉二婶,一霎间全乱了套了。
有才和继女麦花睡觉被二婶捉奸了……
这事还得回到一周前,这个破败的小村突然闯进一辆轿车,轿车里下来一个人到了有才家里,和有才谈妥了一桩买卖。
从轿车下来的这个人是有才原单位的同事,因要到北京开画展,没有画出一幅像样的裸体画,就暗自求有才代画一幅,价格二千。
有才多年没画了,画画的爱好都转移到二婶膘肥体壮的身子上去了,现在手拙的五个指头不分丫,白天跟羊群练习嘴功夫,晚上真枪实弹地在二婶身上练,画画的手艺荒废了,已经好多年没拿画笔了,哪里还敢接这个活,不说二千,就是二万也不敢接。
二婶心动,放一年羊也赚不了二千,多画几幅就成了万元户了不是?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发了大财,就这么一夜间脱贫了,比那麦花他爹死去时人家赔偿的钱还多,哪里能轻易放弃。二婶好说歹说劝有才接下了这笔买卖。
她说她这几天替他放羊,他尽管呆在家里画。
一周交画。
有才又重新握住画笔,却怎么也找不回以前的感觉,几天都没有画出一幅画。
眼看一周就要过去。
二婶万分着急,从坡里采回一束狗尾巴花插在屋里,让屋里增添一些艺术气息,可是有才就像一块死木头疙瘩不开窍,画出的裸体画死气沉沉地没有生机,木乃伊一般。
狗日他娘的,女人的身子就这么难画。本来有才画画时下决心不骂人,保持一个艺术家的风度。
眼前要是有个模特就好了,有才心想。心里不免想起以前在文化馆工作的日子,想起那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画女人,和那个模特女人睡觉时被她丈夫看见,丢了工作,丢了前途。为艺术献身嘛,有才愤愤不平。
狗日的女人,有才在心里恨恨地骂。
二婶放一天羊回家,看有才没有画好画,也不说娘的狗吊样的画画能当饭吃的话了,积极地脱掉衣服给有才当模特。二婶肥胖的身体像下了十窝猪仔的老母猪,奶子耷拉在肚子上,浑身肌肉一颤一颤的。
每当有才见了女人就欲火中烧,就来了灵感,而此时看见这个老母猪样的女人,竟感到恶心。
奇怪,往日怎么不厌恶呢,有才苦思冥想,现在拿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看女人,审美观大大不同了。
“奶奶的。”有才在心里骂了一句,抓起地上的衣服扔在二婶的身上。
说来也巧,在砖窑厂干活的麦花突然回了家,二婶高兴地裂开嘴,赶紧下厨做菜。
“有了。”二婶想,拉着风箱的声音格外脆生。
二婶特意启开一瓶家里来客时才喝的当地产的茅台“商羊神”,破例也给女儿麦花倒上一杯。女儿在外地闯荡世界多少也能喝点,就没推让。
二婶端起酒杯,说麦花你爹接了一幅画能挣二千,这不趁你麦花来家庆贺一番,高兴高兴。
有才说这不还没画嘛,钱不是还没到手嘛,就不喝,二婶不依,逼着有才端起酒杯。
一瓶酒都进了有才和麦花嘴里,两人都晕乎了,小脸都像下蛋的老母鸡似的红晕,说话舌头也不会打弯了。
二婶这时看火候已到,说出一个大胆的设想。
“我说,有才,我也是麦花一进门才突发的一个念头,人家画家开画展还有个设计,我今天就好好给你设计设计。”
有才有点喝高,已经坐不住了,歪斜在炕头被子上,也没心听老婆的设计。
“我说,是吧,麦花,你爹接了一个活,是画一幅画,你爹说没有模特就画不成,为了你爹的画,为了你爹的艺术,你今天就给你爹当模具,不,当模特。”
有才最后一句听得仔细,“忽”地从炕上蹦起来。“你这娘们儿开什么玩笑!”
麦花狠狠地瞅了娘一眼站起来就走。被二婶一把拉住。
“你今天不当也得当,你给我坐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二千啊麦花……”
有才和麦花被二婶煽动地心动,就决定今晚合作一把。为艺术献身。
二婶抿着胜利的笑容。在金钱眼里,一切都是王八蛋。
三
二婶特意烧热一锅水让麦花洗澡。
有才换上二十年前在文化馆工作时穿过的白衬衣,胡须飘然,炕头一站,俨然一个艺术家模样。
二婶从南墙根拔了一把艾蒿,顺手捡起一个空酒瓶插在里面,放在麦花屋里,还特地准备一盆碳火,深春不必火盆的,怕麦花光着身子时间久了冻着,地上铺上一块羊皮,麦花赤脚站在地上不受凉,把罩子灯拨得亮一些。
二婶心里想,如果得到这笔巨款,就安装上县城散热器厂的暖气片,也过上冬暖夏凉的小日子。
一切布置完毕,二婶就把两人拉扯到麦花屋里,就回屋躺下了。放了一天羊太疲惫,不一会儿就打起呼噜。
一家人共同的心愿,期待今晚完成一个伟大的创举。
这边有才和麦花一开始还扭捏。
麦花想想是为了艺术,脱一下又有何妨。
不一会儿各自进入神圣的工作状态。
有才又拾起二十年前的画家感觉,女人身上沟沟坎坎的部位都生动地出现在画面上,不觉心里也闪现出一丝欲念,想扑上去用下边挺起的家伙在麦花身上描一笔,但还是努力克制这种邪念……
终于在醉生梦死的梦境里画完最后一笔,有才就倒在炕上睡着了……
麦花披了件睡衣,见爹有才斜躺在自己炕上,从单薄的裤子里面突出的那根东西像高山一样戳在眼前。麦花被挑逗出了骚动欲望,浑身上下被汹涌的波涛冲垮一般,瘫软地倒在有才身上。她颤栗的双手握住那个东西,觉得这个硬邦邦热乎乎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多次梦中的欢乐淫念,会带来跟村里狗蛋第一次在麦秸草垛里偷吃禁果时的心跳。她轻轻地抚摸着,完全沉浸在一种妙不可言的快感里。
有才正在梦境里,想念那初恋情人叶子,叶子正向他款款走来,还是那么柔情,娇小的身材轻柔的附在他身上,失去多年的爱情又像春天的河面一样复苏,又达到沉寂多年的爱情欲望,下部那根像火腿肠放在火上烧烤一样膨胀,就要爆裂。想自己这些年放羊也老了,身子像秋后农家院墙的吊瓜,蔓藤已经枯死在清冷的墙头上,蔓藤上的瓜还是那么脆生的挂在半死不活的蔓藤上生辉。在叶子渴望的呻吟里,又撩拨起原始的冲动,不觉搂住叶子压在身子底下。
半醉的麦花终于又尝到巴望已久的男女之情,一阵微微胀疼过后感觉到的是那么美妙的韵味,忍不住像她娘一样放浪地哼唧起来……
二婶醒来天已大亮,身边不见有才,穿衣去了闺女麦花屋,看见两个人正赤条的交织在一起酣睡,也不打上个被单遮盖一下。
二婶气炸了,“娘啊,天杀的啊……”就拉着长腔哭号起来。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撕天裂地的嚎哭,惊醒了睡在炕上的有才和麦花,有才发现自己赤条条地躺在麦花炕上,不觉蒙了。
麦花酒也惊醒了,想想自己和后爹上了床,羞愤地跳下炕。趁爹娘争吵之际,摸起一根绳子就上了吊。
四
看热闹的人群退去,有才颓废地蹲在院里,麦花躺在炕上哭泣。
二婶平静过后,心想,也不是馍馍吃了就没有了,吃一回也就罢了,随他们去吧,就想起正事,看麦花屋里的画已经画好,二千啊,马上就到手了,脸上不觉露出灿烂的光芒。
还挺标致,这个骚娘们儿。二婶望着这幅画心里有点吃醋。
“该死的,到村里小卖部给人家打电话来拿画。”
有才抱着头不动,“还拿什么画,全村人都知道了,都丢尽人了,你嚎叫什么!”
“你跟麦花上了床俺还不敢吱声啊,这么大的事你能捂住!巴掌大的村,放个屁全村都臭。”
没出息的东西。二婶自己捋了一把头发就出了门。
二婶在村里人的目礼下风风火火地去了小卖部。
“我说画家同志啊,有才把画画好了,来拿吧。”
听见话筒里传出那边的声音。“不是昨天就到期了吗?怎么才说,我们已经进京了,不用了。”
二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飞天》2010年12月 。又录入《小小说创作启蒙》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