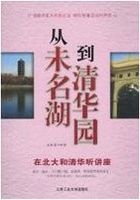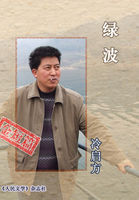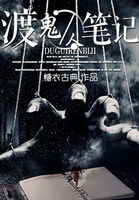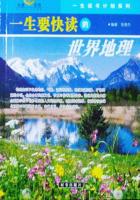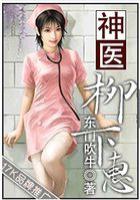天也不知什么时候黑下来的,江对面凤凰山只余影影绰绰的一个轮廓,黑的,天幕则是浅黑色,然而山影与天幕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似乎很快就可以融在一起。
暗黑的一大块里忽然嵌入了一闪一闪的亮,大概是夜行的小车在上山,不多久忽然一切都归于黑暗,让人疑心是不是有那么一闪闪的光存在过,看一会儿别处,几乎忘了有亮光那回事,偶然再扫一眼时,那暗黑与浅黑的轮廓相交处忽然就有一星微弱的光——不知是山行停下的小车重又启动,抑或只是天边的一粒星子。
我所在的地方是沅陵沅江大桥北岸的轮船码头边,水中泊着几艘极大的趸船,一艘大概是客轮码头的,白日里看得见上行下行的水路标志,另两艘趸船上有木楼,船头有锅灶与小小桌子,上面挂有“吃饭住宿”的招牌,自己原想住在趸船旅馆里(这样的体验从来没有过),谁知客人早已满了,船老板推荐自己住岸边的吊脚楼。码头附近只一家吊脚楼,一半在岸上,一半临水,全是木结构,在这新式县城的一角,居然有这样一个古旧的吊脚楼,对我这个向往湘西的异乡人来说,或许多少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吊脚楼一楼住着主人,堂屋一张牌桌前镶了不少人在看牌,老老少少的很是热闹,二楼一排房间供旅客居住,风景不坏,推门即是沅江,房间均以木板相隔,极简陋,七八个平方,只一床一桌,被角有些黑——一个大男人出门在外,这些倒是无可无不可的,然而那好心的老汉送热水壶来时的一句耳语却让自己有些意外,并决定重新选择住宿之处——“伙家,这里三教九流的多,如果有钱的话随身带,不要放在房间里。”孤身一人的自己随身是带了一些现金的,若出个什么意外,不仅不妙,整个旅行也会成为问题,遂又到江边不远处一家宾馆重新登记——那里是安全之所,对于不能在沅江边的吊脚楼过上一夜,自己是有些遗憾的,在宾馆里放下行李,洗漱过,看看已近黄昏,便重又坐在吊脚楼边的这码头上。
天黑得并不透。
趸船船头正对码头,起初有炒菜落锅的声音,哧哧拉拉地响,一个妇人脸被红彤彤的火光映着,正快速翻动手中的铲子,大概在炒腊肉,一阵独特的香味儿,菜炒好后,端进去了,一切便安静下来。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捧着一碗面条,不得安神一般,一会儿跳到码头上,一会儿又跳到船上——什么地方摇来了两只小犬,男孩便蹲在那里耐心地用筷子搛起一根面条,极有兴味地逗弄小犬。
透过舱门,可以看到中舱的一个大房间里,一只晕白的日光灯下,一大堆人簇在一处观看电视,而全然不在乎屋内的闷热。
似乎只有倚在临水舱门的瘦高个子有些不定神,他一会儿看看水,一会儿看看电视,神情间有些落寞。
河堤草丛间有草虫在合奏,乍听整整齐齐的,一片清音,然而听的时间长了,细碎中其实自有分别,看天上,满天的星子,明天应当是个好天吧。
对河趸船上渔庄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暗淡下去了,几乎只余一线光亮,缩着要消失一般,沅江大桥的光也却极亮,投映在森森的水面,一块一块拼成红红黄黄的长长缎子,弯弯曲曲地飘摇着。
忽然就听到身后什么地方很响地传来“咩——咩——”的声音,哀伤而固执的调子,让人心里一惊,再听时,那声音又似乎不见了,觉得一定是自己看久了水边夜景,又对《湘行散记》中那“为了过年而死去的小畜生”印象太深而出现的幻觉——一直难忘那在鸭窠围水边固执而又柔和的羊叫声,然而再细细听去时,竟又是清晰的“咩——咩——”的声音,或者竟似“妈——妈——”的声音,有些奇怪,这个县城的码头边照理是不会有人养些小羊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过一会儿,那声音终于换成“啊——啊——”的哭声——直到这时,自己才断定是个婴孩在啼哭,从声音所来的方向细细分辨,是在河边吊脚楼上,或许来自我所订房间的隔壁。还是在白天订房间时,听房东老汉说隔壁是一对夫妻从乡下到沅陵给孩子看病的,自己经过那房间门时,还曾看到一个头发打结的女人歪在门前凳上看水,她的目光空洞而无神,一种对生活的无奈与无着看着有些揪心。
哭声是那女人的孩子吗?这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因病难受而哭,还是睡醒了哭闹呢?想起母亲说起的儿时的自己,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大或者周岁左右,寒冷的冬夜,也曾被母亲抱在怀中坐船去找医生,那时自己的哭声也应是这样的,那哭声曾经杂糅着橹声、水波声与岸边草丛里的虫吟声……那些声音,现在又去了哪里呢?那时的小人,和那时他的父母,现在还在家乡那处水边吗?
没有谁会回答这些问题,水中趸船上的小犬忽然对着暗夜吠起来,与吊脚楼上的婴儿哭声相应着,一瞬间几乎让人起人生悲凉的情绪……天空的星子很远,然而细看时又似乎很近,这一远一近中间有着一个无限的空隙——越定神看去,那空隙愈发扩大……扩大至最后,竟将这沅水边的哭声、吠声、虫声,以及一切声光电色全部收缩进去一般?
那些属于儿时自己的哭声与笑声,是不是也被收缩进什么空隙里了呢?
……
自己到这处湘西水边到底要寻找什么呢?似乎什么也没找到,然而又似乎找到了某种东西,只是无法诉诸语言——但无论如何,这处水边如小羊般“咩咩”的小儿夜啼会在自己记忆中永存的。
不知什么时候又到了吊脚楼上,二楼临水房间安安静静的,再没有婴儿的哭泣——想象中,或者那孩子并不在这吊脚楼上,或者哭累了,哭着哭着便昏昏沉沉睡去了,被孩子折腾很久的大人因此也躺下和衣睡去了,走过时那房间黑黑的,无一丝光亮。
终于悄悄锁门离开吊脚楼,漫无目的地走向另一条热闹的小街,这小小河街一溜不少生意红火的烧烤小吃店,中间夹有生意清淡的百货店、修车铺、理发店,更多的却是灯光暧昧的发廊按摩店,门虚掩着,里面可见三五或浓妆或清丽的女孩子,或随手嗑吃瓜子,目光有意无意间搜索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或聚在一处百无聊赖地玩牌作乐,时不时瞟一下门外……一个缩在门边沙发上黑俏瘦小的女孩子让自己印象尤深,这女孩不过十七八岁,似乎全身都无力极了,路人走过时,她只是懒懒抬头报以冷漠的一瞥——我几乎难以想象这女孩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然而对照现实却又无法不这样想去。
沅陵一带水电站的建设,使得沅水不再是多激流、险滩的航道,也使得沈从文笔下“柏子”、“牛保”那样的多情水手近于消逝,我不知道这些女子还会不会如沈从文所见的那样,与水手之间作家常而多情的对话。
吃完晚饭再经过那家发廊时,缩在门边沙发上黑俏的身影已不见了,我不知道她是出去了,还是陪着客人到了里面的隐蔽房间?没来由的,我想了解一些关于她的生活与命运,然而却又害怕想象下去……她的明天在哪里呢?回到乡间开一家小店,或者,累积更多的钱,开一家发廊,开一家饭店,继续周旋于丑陋之间,或者,寻找一位无能或有能的男子,试着改变自己的命运,运气好,成家生子,运气不好,就一直流荡下去——我忽然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感慨者的可耻,别一些人实在是不配对她们感慨些什么的,她们的无奈与坚强,她们的柔软与温情,只与她们自己有关,别一些人,无论感慨是真诚或虚伪,都与她们无关。
到江边码头边让风吹了一些,终于感觉到些许凉意,趸船上的电视不知什么时候已关掉了,人已散了,但仍听得到人的低语声,一个瘦瘦的老人拿了撒网却走出来,在码头边找个地方抛下去,一团银白的光,一阵水响。
夜已深了,吊脚楼最后一缕灯光已经熄了,远近几只小舟也没了灯光,只有沅江大桥映下来大块昏黄的灯光,原先是长条的,此时全然扭曲交错在一起,近岸处,一艘铁驳船的船尾有一方暗淡的光闷在水面。
没有再到那家吊脚楼,回到宾馆时,大堂看门的妇人已歪在木沙发上昏然睡去了,面前的电视屏幕却仍在播放着一部国外的电影,一对男女的对话声在黑夜里听来让人却更加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