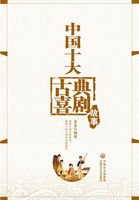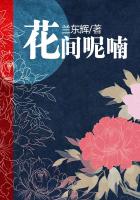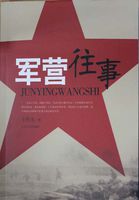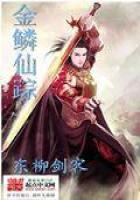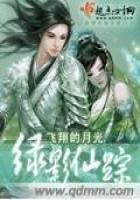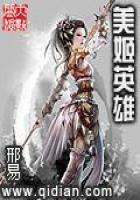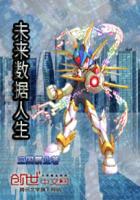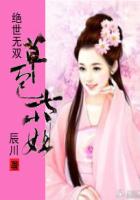他家只有两间屋子,门前拴一条大黑狗,见我和它的主人一起过来,一声也不吱,只安静地看我们;两间屋子一间吃饭用,一间卧室,只有一张床,屋顶可见天空的光线,问他这屋漏不漏雨,小杨说不漏的“别看有一些天光,但瓦的接头很好的,一点也不漏。”又拿出自家的凉薯来,请我吃,撕吃了一个,满口甜脆。
边吃边聊,先是比较起江苏与湘西的地形特点,又说起茶峒的苗人,小杨说镇上苗人很少的,他们大多住在深山里,他说他自己是土家族的“土家族现在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服装——什么都失传了。”
我问他怎么看,他憨厚地说了两个字——“随便”:“我们这里的土家族很多的,我觉得与汉族没什么区别,我在无锡打工,别人看电视看到介绍土家族的服装风俗,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就回答说现在不是,那是电视上的土家族,现在的土家族都和我差不多,我还叫他看看我,看看与汉人有什么区别——当然没有区别。”他最后的结论是土家族与苗族是不同的,苗人通过服装语言是可以辨别的,但土家族却不行。
说起当地人的“边边场”(赶集)——这才知道原来今天正是逢场的日子,茶峒地方逢农历的“五”与“十”赶场,在周边影响最大,对岸的重庆洪安则逢“六”与“一”赶场,附近三省(市)村寨的乡亲背了背篓到茶峒办货掉货的极多,他和他母亲吃完饭(茶峒人只吃两顿)本来也是约好一起去茶峒赶场的,谁知意外来了自己“反正没什么事,闲着也是闲着的,我去那里就是甩着手到处看看玩玩。”有些庆幸到茶峒来竟如此之巧,聊了一会儿,因为怕错过了茶峒边集赶场的热闹,便打消了在这边再看看的念头,和小杨一起过渡,翻过小山山且向茶峒方向去了。
经过原先泊着的那渡船时,小杨指着那船说:“这人才真是快活。”
我说:“怎么的?”“也不知又跑到哪里玩去了,他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原来溪边这摆渡的水手是条老光棍汉子。
(四)赶场
赶场的人真多。
茶峒老街行着、蹲着、站着、看着、谈着的,到处是从附近村寨赶来的背竹篓乡亲。
街边店铺门前是大把大把的粉条,大缸大缸的青盐与白糖,小堆小堆黄灿灿的烟丝,一箩一箩红彤彤的长辣椒……街边巷子里,剃头师傅只在青砖墙上搭一木板,放些剃头用的推子、剪刀,旁边挂一廉价粉红塑料镜,很快便有乡亲张一张,随后便放下背篓,安然坐在那里,听任他把那个瘦黑的脑袋刮刮剃剃。
老街通向河边码头的十字路口从早开始便一直烧着几口大锅,一直未看清煮的什么,再回茶峒看时,锅里沸腾着的原来是麻辣猪肚片,煎得黄中发黑的鲤鱼层层摞在锅边篓子里(应当是先煎鱼再下猪肚片的);河边方向,沿墙排着两溜方桌,一直排到码头台阶上,约十四五桌之多,桌上一片残羹,然而每张桌上都有人在吃饭,狗在人腿桌腿间钻进钻出,意味盎然,看看地上散落着炸碎的鞭炮屑就知道——这应是附近人家在办什么庆贺的酒席,本地人一天只吃两顿饭,这顿饭自然算是早饭了。
也有人捧碗站着,边搛菜边和另一个人说些什么;一个头发梳得滑滑滴滴、穿对襟衣服的七八十岁老太太,脸色清净净的,正和一个壮汉同时将饭勺在大盆中盛饭,老太太的嘴瘪瘪的,但她盛的白米饭可不少,她的胃口一定好极了。
——所有人的胃口感觉都似乎好极了。
三四个老人蹲在一处草烟摊前,一扎一扎地挑拣,其中一个戴蓝帽(帽后露出一块薄薄的帽衬)、穿一身蓝中山装的短须老人尤其沉迷,他腮边青筋突着,将一支金黄软和的烟叶捻一些到随身带着的铜烟管里,点燃了,便将烟嘴放在口中,安静从容地吸起来,他那态度真当得起一个“品”字,身边围着的几个老人很快也被几缕白烟包裹着,老人那种满心的沉醉与热爱,让我忽然也有了来一口的冲动,想起《边城》里的老船户几十年前在茶峒街上买烟,不知是不是这样的神气?印象里的老船户会到茶峒去买本地出产的上等草烟,挂在自己腰边,看到过渡人过分注意那烟叶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式!’”
那句话真是有味极了——那些来自善良人性深处的鲜活语言,应当是永恒的,我觉得这些老人或许也会说出。
沿街靠墙一面排下去全是各种摊位,卖草鞋的、箍桶的、卖麻绳的,算命打卦的、玩蛇的,都各有其形式,各有其主顾。
忽然有对歌的声音传来,走近前去,原来是一家店铺正用电视放着当地民歌,门前围满了带竹笠、背竹篓的蓝衣黑衣乡亲,几乎清一色都是中老年人,妇人尤多,他们寂无声息地面对着电视里对唱情歌的一男一女:茶妹是桂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木叶吹得响穿山,穿过妹妹心中间。
晓得是郎来会见,三脚两步就上山。
……奴妹下河洗围腰,十个指头水上飘。哪个喝了围腰水,不害相思也害痨。
……远望姣妹身穿蓝,好比红花酒一坛。哪时吃得红花酒,死在黄泉心也甘。
……东边落雨西边晴,斑鸠爱住苦竹林。鱼爱深塘虎爱山,奴妹只爱吃苦人。
……
歌词朴素而直白,比喻极其巧妙,声音或高亢,或悠远,末一声少了凤凰苗女对歌里的“呦喂”,总有些拉长的调子,在老街上飘来荡去。我在那里呆了有十多分钟,没一个人挪步,不断有老人挤进这个队伍,他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几个老太太全无表情,如雕塑一般,只有几个中年妇人歪头听着渐渐微笑起来,无论是沉默或是微笑,这些远去的歌谣应当曾经让他们的灵魂飘浮起来的吧,他们生命里的哀乐,他们的青春,在这些歌谣里应当好好地保留了不少成分。
我走开时,听歌的人群中依然未能看到一个当地年轻人,一如那位土家水手所说,茶峒的年轻人,离这些边城民歌已经越来越远了。
回程时路过一家绿豆粉摊前,不少人围着在吃,一个背负细篾竹篓的小女孩托碗蹲在地上吃得极香,竹篓有些倾斜,只看得见一块编织布,也不知下面覆着什么。狗在她脚边钻来钻去,她年纪不过十岁左右,没任何同伴,神情自然清灵,细看时又有些许似有若无的忧郁,脚上穿一双红雨靴——早起的露水大,她应当走过不少山路才到茶峒的。我把手中相机对准她时,她似乎注意到了,抿嘴抬头看我一眼,隐隐地有些好奇,但分明又没有任何表情,便依然埋头吃碗里的绿豆粉了。
转过一条街,回头再来时,这女孩就再也没见。
(五)黄昏
茶峒的黄昏,极静而美。一个人坐在宾馆窗前注视连绵起伏的远山与后面激射的点点金光,想着还是该融入这方黄昏时的山水才好。
经过楼下老街时,两边的摊点只剩下零零落落的了,一个胖胖的男子将百货杂物收拾进小箱子里,开始拆那把竖着的大伞,准备回家;河边码头上,原先泊着的几条从上游下来装载赶场乡亲的篷船也不知什么时候移开的,秋水黄昏中,那些完成交易的乡亲说笑着或者已该到家了,我甚至能想象得出他们说笑些什么。
其实自己是想挤在这些乡亲中间坐船回到一个村寨的,村寨里我仿佛有个很久以前认识的熟人或者亲戚,我觉得自己应当要和他或她说上很多的话,然而自己也搞不清怎么就没赶上他们的船,以至于孤孤单单地在这河街上闲逛——一个人在这样黄昏时想起那些平凡生活的乡亲,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自己抓住了,然而事实上又无法抓住。
已经到翠翠岛水坝后面了,这里正当两条溪水的交汇处,近溪岸边,一处残破的房舍遗址,只有两块突起的残垣,旁边立着一座青砖黑瓦的小屋,就在这破墙根边,却舒展着两株姿态极其优美的树,黑黑的老梅一般虬曲茶的干,斜斜地伸向溪水,有些像故乡的楝树,绿茸茸的细叶尤其像,但细看时却没有楝树果,小时一直喜欢开出满树紫花披短柔毛的楝树,还有楝树果儿——那时候总喜欢拣拾这圆溜溜的果子玩儿,未熟时青青的,成熟后黄黄的,甚至恼恨这玩意儿这样好看却不能吃上一口。
正对自己的是翠翠岛后面那处黑石的溪水,从远处到跟前成一个转折,中间是尖尖的滩头,水两边还是黑的,然而中间却给铺上一层淡淡的褐黄,柔和和地亮着——那该是山头返照的余晖,水过了那滩头,抵达缘山边的溪中,越过水中一堆白色、茶色的石子,便奔向不远处的水坝而去。
什么地方的雀子突然急促地叫了几声,另一处立即便有雀儿啾啾地回应起来。
树丛里隐隐有人声,循声看去,才知道靠水坝方向溪边树丛下两个中年男子正在溪边擦洗身子,他们脱得光光的,全无顾忌,生活态度的天然处不得不让人羡慕。
缘山路再往前去,到了自己所认为的“碧溪山且”溪边泊渡船处,船已停到溪对面去了,船上依然无人。
坐在溪边一块大黑石上,身边招摇三五枝黄蕊淡紫花瓣的野菊花,远山与对岸倒映水中作深黑色,黄昏时的天空在山上张得很开,披散开无数浅桃色的薄云,使得天空似乎仍在极力扩大,映在豆青色的水中,却又被消解了,揉碎了,满溪散落着桃花一般。
比之水坝处,此处各类鸟雀的声音极其繁密,正如沈从文所说,每个时段的鸟鸣都是各不相同的,我想细细分辨一下是不是有黄昏静极情况下发出“舟勾格达”叫声的杜鹃,然而听了一会儿,才知道是徒劳,鸟声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它似乎轻抚每一根神经,让人整个的心灵为之放松,尤其是在茶峒这处黄昏的溪边。
西天的云影不断地变幻、游移,溪水中的桃花渐渐变淡、消逝,终而转为深青色,对面隐隐有些人声,远山、竹篁、棚屋映在水中的颜色也由深紫转成深黛。
溪尽头起伏的远山背景此时却成为巨大的浅白,天空清清朗朗的,提醒人这原是一个秋季。
不知什么时候更远一些的溪边岩间忽然燃起野烧,大概是什么人堆起枯叶树枝在烧,一小点红火,袅起一缕白烟,渐渐散淡开去,正如沈从文所说:“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
有一瞬间,坐在那里的我似乎不见了——我在这个梦中无数次来到的地方不见了自己,眼前的风景亦复不存,只有一个巨大虚空,那虚空不断地扩大、旋绕,所有的一切都被包容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是瞬间即逝的,然而所有的一切却又是永恒的……一切光景与感受形诸文字,才知道语言的贫乏。我所写的,能依稀捕捉得那里所体会的万分之一就很可欣喜了。
暮色不知不觉间就笼住了一切。
对溪有依稀的人声,看去时,浅淡颜色中一个男孩跟在一个妇人身后沿溪水走着——忽然想到自己该回去了,看看身边的一切,忽然想起溪边守着果园的小杨,那个悠闲自在的光棍水手,此刻,又在哪里呢?
这些奇怪的问题当然没有结果,回宾馆收拾了行囊,十分钟后,自己已挤在一辆小面包车上由茶峒向花垣方向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