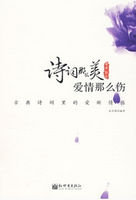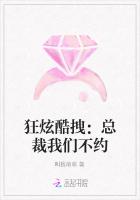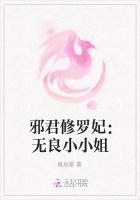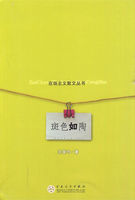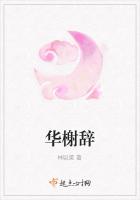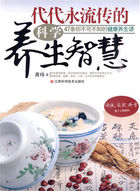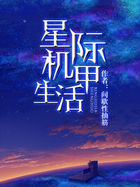手上的材料写得分明:黄蒙拉,1980年出生。在第49届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上,一举囊括金奖、最佳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纪念马里奥罗明内里奖三项大奖,成为继吕思清、黄滨之后中国第三个帕格尼尼金奖得主。目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研究生二年级。
迎面他就先抛来两个问题:“你喜欢音乐吗?古典还是流行?”还来不及回答,第三个问题又抛过来:“你喜欢物理吗?最近我正在看物理方面的书——《寻找薛定谔的猫》。”
说小提琴手喜欢文学,我相信;关心物理的小提琴手……稀罕。后来,我逐渐知道,黄蒙拉不仅仅是个优秀的小提琴手——
他还热爱物理、网球、电脑游戏;
他从不掩饰自己;
他是被破格录取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的;
他做的论文令老师头疼,却的确是合格的论文……
以及最重要的,他身上最明晰、最有“锋芒”的特点,就是80年代的那种“张扬”。
1.他爱校敬师,不过,对于自己的论文,却有着非
同一般的坚持与自信黄蒙拉是温文尔雅的青年,得出这个印象,并不源于他态度傲慢、眼高于顶之类,而是来自与他的交谈——
李纯:“喜欢物理的小提琴家恐怕不多,我倒是知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业余嗜好是拉小提琴。”
黄蒙拉淡淡地笑:“没人知道我的物理学,或者他的小提琴程度究竟有多少。”
李纯:“那么多人苦练小提琴,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为什么偏偏是你,拿到了帕格尼尼金奖?”
黄蒙拉沉吟片刻:“也许是因为我的演奏更接近于时代精神。”
李纯:“什么是时代精神?”
黄蒙拉:“就像巴洛克体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一样,从建筑、绘画到音乐,我想,我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频频拿自己与大师比肩。采访过中年人,他们多半会成熟内敛地答:“大师超凡脱俗,我怎么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青年人黄蒙拉看着我,说:“是的,我相信,我相信的,就可以说。”目光真诚,不容置疑。
还有别的可以为证。在上海音乐学院,黄蒙拉有一句口头禅:“说我什么都可以,但说我两点我不答应,说我论文写得不好,我不答应;说我‘星际’(男孩子中人气很旺的游戏)打得不好,我不答应。”
黄蒙拉的论文屡屡令老师头疼,学院派恪守的准则——措辞严谨、字斟句酌、起承转合,黄蒙拉全不肯遵守。名门大派总要求弟子们招招式式不出差错,但黄蒙拉却钟爱以无招胜有招的“小李飞刀”,钟爱以生动的词汇、“不守规范”的形式(譬如聊天记录),直抒一个青年音乐人的胸臆。为了这风格,好几次被老师叫去,苦口婆心,黄蒙拉发丝飞扬,站在那里淡定地笑,下次写论文,却依然不改本色。
这个南方男孩性子恬淡,即使被人批评看家本领小提琴,至多付诸一笑。从骨子里,他深爱上海音乐学院,敬爱师长,不过,对于自己的论文,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自信和坚持。上海音乐学院治学严谨,但也不反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此,黄蒙拉的论文得以过关。
2002年7月,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获得本科文凭。专业分数高高在上的他,因为公共课成绩差那么几分,未能被保送研究生。回首四年,蒙拉觉得自己把一部分时间献给了音乐,另外一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星际”和谈恋爱,并不怎么特别懊恼。
此前,黄蒙拉已在一些国际比赛上获得过奖项,但在人才辈出的音乐界,这些成绩不算突出。
当他于当年9月获得帕格尼尼金奖时,不少音乐界人士欣喜之余,也有意外——
为什么是黄蒙拉?
2.黄蒙拉的少年记事簿
追根溯源,黄蒙拉走上小提琴之路,并不因为是神童出世,也不起源于“兴趣”。练琴竟然是为了——户口。父母都是下乡知青,回城之后母亲的户口落在郊县。“学点本事,好把户口调回上海市区。”
于是,4岁的黄蒙拉从“弹棉花”起步,在铮铮之声中顽强地成长。
“不觉得弹琴枯燥,让你失去很多快乐?”
枯燥,当然枯燥,很长时间处于混混沌沌里,因为被长辈要求这样做,不得不努力,即使痛恨小提琴也不敢声张。也从不曾被老师们视为天才,幼年黄蒙拉对节奏反应灵敏,手指灵活,但与普天下有灵性的琴童相比,他只能算作庞大分母上一个不起眼的分子而已。有时候小蒙拉会疲乏得哭起来,问老师张欣:“为什么要拉琴?”老师笑道:“谁叫你名字叫‘梦拉’,做梦都要拉,你现在不刻苦拉琴怎么行?”又问老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能出去玩,我不可以?”老师答:“因为拉琴的英文名就是play the violin 啊,play ,不就是玩耍的意思吗?”
于是,小蒙拉背着不怎么喜欢的小提琴,一次次奔波于家与学校(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之间,“长大后做天文学家”的梦想逐渐变得影影绰绰,若有若无。
混混沌沌很多年,直到18岁——黄蒙拉反复跟我们强调的18岁——青春与小提琴,终于碰撞出强大的化学反应。
这一年,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他随团去法国演出,巴黎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无意中,黄蒙拉仰头看向天际,观察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云层重重叠叠,排列出多棱的形状,天空在阳光的折射下犹如一块幻彩水晶。
黄蒙拉在刹那间顿悟:原来自己以前一直是一张白纸,一潭死水,一个劲儿地练技巧,把指法练得纯熟,传递出的旋律却始终缺乏动人心魄的力量,不能带给人无限的喜悦和感动,其中的缘故,就是因为自己只在乎其“技”,只在乎其“器”,而忽略了其内在的“精神”。今后必须在演奏时融入更多的元素。
另一件事,与父亲有关。黄父是外科医生,家境殷实。但培养一个小提琴家,真的像培养一个“贵族”。一天,父子俩去俞丽拿老师家玩,无意中看到一把小提琴。回去的路上,黄蒙拉沉醉于方才试拉小提琴的感觉,说不出的契合,真想立刻拥有它,可是价钱……9000多美金,相当于八九万人民币,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开口的数字,特别是向自己的父亲,18岁的男子汉黄蒙拉默默地想,曾经拿着钢尺督促他学琴的父亲,曾经把他关在大门外惩罚他的调皮行径的父亲,同时也是奔波操劳、呵护自己衣食无忧的父亲。
是父亲打破了缄默:“你确实喜欢这把琴吗?喜欢,我们就买下来,但你以后要好好地拉。”
当父亲将这把小提琴交到他手里时,黄蒙拉也把一种信念放在了心里,那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对音乐的热爱,不掺杂质、不带委屈的爱。(2004年春天,黄蒙拉告诉记者:“那笔钱我已经还给父亲了。”说完,脸上浮现出一个浅浅的得意笑容。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儿子欠父亲的债向来是模糊不清的,能做到“还了”,“还得起”,对24岁的蒙拉来说,多么值得骄傲。)
18岁那年,还值得一记的,就是黄蒙拉开始收到“圣地雅听”的邀请在那里演出,“圣地雅听”位于上海静安宾馆底楼,是音乐爱好者聆听新人演奏的地方。在那里,黄蒙拉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公开演出。
3.参加帕格尼尼比赛,某个意义上,是百无聊赖状态
下的一种尝试参加帕格尼尼比赛,完全是一种尝试,确切地说,是在百无聊赖状态下的一种尝试。拿到毕业证离开“上音”的那天,失落感正式降临:从附小到大学,14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在“学校—家—淮海路”方圆3公里之内的路途中晃荡。接下来干吗?做职业琴手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眼下……得找点儿有趣的事做做。
于是,报名参加帕格尼尼大赛。对年轻人而言,帕格尼尼金奖好似一枚至尊魔戒,诱惑力十足,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小提琴家,都曾通过这项比赛奠定自己的“江湖地位”。
并不是因为对大奖顶礼膜拜才去参赛,只因为年轻的时候总想经历一些事情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使失败也无所谓;恬淡、自在,是蒙拉的生活态度。记得2001年去波兰参加利宾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好强的韩国选手哭了,为未能摘取桂冠;蒙拉只取得第二名,照样兴致盎然,他对随团老师说:“我听过第三名的演奏,拉得真棒!”
真的,外界授予的名次,只能填补一时的“饥饿感”,心室空间终归有限,不可以被功名填满,宁可淡漠一些,留白天地宽。
最喜欢的大师是美国小提琴演奏家海菲兹,完美的海菲兹,深邃的海菲兹,对煊赫功名漠然处之,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成为百年难遇的小提琴奇才。
老师俞丽拿和父母都大力支持。黄蒙拉孤身上路,带上那把价值9000美元的心爱的小提琴,带上头一年从日本仙台第一届国际音乐比赛上挣来的奖金(此次比赛他获得金奖,也是头一次在国际大赛上获得金奖,收获无穷信心),自费去了意大利热那亚。
比赛的前奏曲并不那么赏心悦目,住的是青年旅馆,八个床位分成上下铺,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无处可放,黄蒙拉只能把它随手往桌上一搁,一夜酣睡到天明;上午9点以后,旅馆不许逗留,黄蒙拉只能出去练琴;连练琴的房间都限量供应,黄蒙拉只能一次又一次去争取去讨要。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波折产生在第二轮比赛,黄蒙拉忽然发现,苦练了很久的曲目——小提琴钢琴协奏曲《苗岭早晨》完全作废,规则里写得明白,参赛作品必须是无伴奏现代舞曲。
那边,黄蒙拉在异国他乡遭遇难题,这边,黄父在思南路的小洋楼中等待儿子的消息,无论成败。父亲一直以儿子为骄傲,哪怕儿子始终平凡。对音乐对人生,蒙拉有自己的解读方式,尽管生活圈子异常单纯,较少介入纷繁芜杂的人事纠葛,也较少贴近大众,但蒙拉通过广泛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文学、哲学、历史、物理……
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小提琴演奏家,丰沛的情愫非常重要,科学的严谨的思维也不可或缺,黄蒙拉认为,音乐越“理性”越“高贵”。
有时,这个出生于80年代的孩子也让父亲费解,譬如蒙拉读完《约翰·克里斯朵夫》,会问“英雄主义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一定要做英雄”。新新人类已经不满足于激情澎湃的豪言壮语,他们相信,做什么都不如做自己重要,“我就是我,晶晶亮。”
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也在等待蒙拉的消息。“最幸运的就是遇上俞老师”,俞老师的音乐造诣与她的包容之心,她为弟子付出的种种心血,早已被蒙拉深铭于心。
蒙拉是个调皮的徒弟,如果想逃课,就能找出五花八门的理由;也是个有韧性的徒弟,为了练好一个音符能再熬上六个小时。在蒙拉满不在乎的外表下,有一颗“认真”的心,认真思索,认真“求变”。
别看蒙拉和他的80年代的同龄人一样,吃着洋快餐看着好莱坞电影度过童年、少年,现在他已经有意识地让“心中的音乐”和浮华尘世保持“疏离”,他“心中的音乐”,是不容亵渎的,是从“生活的艺术”中酿出的香,是生活的思想的骨骼,是在X光下隐去毛发皮肤经脉血液脂肪肌肉后的新鲜骨架,是潜藏在最深处的东西。
让我们再回到意大利帕格尼尼比赛,中国选手黄蒙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灵机一动,冲其他选手说:“把你的练习曲谱借我看一眼好吗?只看一眼。”他的英文口语很流利,尽管笔试分数总是很难看。
对方疑惑地递过来。
黄蒙拉的确只看了一眼,但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符合比赛规则的曲谱。
离比赛时间只有三天,三天要练习一个全新的曲目。其他选手为了一个曲目可能厉兵秣马了好几个月,但中国选手黄蒙拉只有三天。
弓弦舒展,心情更舒展,没什么好紧张的,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当你把外在的那些“泡沫”都撇去,剩下唯一要做的,就是和自己的肢体、自己的神经、自己的心灵对话。
第二轮比赛,黄蒙拉顺利通过。
决赛,第二次出场演奏完帕格尼尼协奏曲后,欢腾声像黑夜里的火焰,从极小的一簇开始燃烧,接着遍布全场,经久不息。
在帕格尼尼金奖获得者名录上,中国人的名字已经消失了八年(上次获奖,是1994年,旅美小提琴家黄斌获得金奖),片刻之后,由上海音乐学院本土制造的黄蒙拉,将打破这段沉寂。
黄蒙拉垂下小提琴,向宏大的音乐厅鞠躬,就像无数次在上海的“圣地雅听”,向爱乐者鞠躬一样,音乐要演奏给所有贴近你的心灵。
4.我喜欢法拉利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的末尾,绝顶高手第三次来华山论剑,新一代的高手杨过刚刚崛起。大家商量着要给杨过一个名号,叫他继承“西毒”显然不妥,“侠”啊“邪”啊也不合适。商议良久,杨过得了一个全新的名号,“西狂”。
与黄蒙拉的近距离接触,他身上鲜明的80年代人的特征,使我想选择一个“狂”来凸显他,“狂”,是内敛之后的“张扬”,“狂”,因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使他们有足够的天地和自信去实现“野心”。
不过,别忘了,坚持与洒脱、清高与随和、简单与深刻,全是黄蒙拉多棱性格的某个层面,是他取得今天这个成绩的根本。
得奖之后,黄蒙拉被学校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演出邀约不断,有时为了钱而演奏,有时为了“任务”而演奏,有时,为了“梦想”本身而演奏。父亲的困惑又来了,眼下黄蒙拉已经走上一条非常平坦的大道,但偏爱念叨,“我想去做生意,我现在对赚钱很感兴趣。”呵,是这个年龄的写照,惊鸿一瞥、想法飘忽,有未来,就没有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