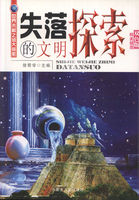阳光很好。难得的冬日里的小阳春。小区里新近飞过来一种鸟儿,黑羽毛,头顶上和翅膀上各有一个白花斑,低空盘旋时,翅膀上的花斑像两个飞转的小火轮,很漂亮。它们在光秃秃的梧桐枝上跳来跳去。梧桐树远看似乎有一点绿,若有若无的绿。其实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季节才到了“小寒”,数九天气才开了一个头。从梧桐树枝上感觉出来的绿,是蓝天红日把树木衬托得有生气了。
卫东平站在眼镜店门口,对走过巷子的舒一眉说:“今年的蓝天好像比往年多,空气污染的情况不那么严重了。”
他忽然看到舒一眉手里拎着的一盒蛋糕,马上明白了什么:“是弟弟过生日吧?”
舒一眉不愿意太张扬,笑了笑:“十一岁,小生日。”
卫东平说:“你等等啊。”
他返身进屋,片刻之后拿出一个做工精致的小木盒。他打开盒盖给舒一眉看:“《三国演义》的烟标,张飞的一张。弟弟已经有了东吴、周瑜、关羽、赤壁、华容道、长坂坡、诸葛亮,加上这一张张飞,就集齐八张一套了。”
舒一眉轻轻地“啊”了一声,说:“难为你帮他费心。”
卫东平把盒子递到舒一眉手上:“算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可你千万别说是我送的。”
舒一眉挑一挑眉毛:“为什么?”
卫东平说:“我已经帮他收过几张了,如果最后一张还是我收的,他会觉得这一套烟标得来太容易,跟他自己没有多少关系,心里不爽。”
舒一眉看了他一眼:“卫师傅,你真是个心细的人。”
卫东平嘿嘿地笑着,搓了搓手:“小孩子啊,难得让他们高兴。”
弟弟生日的前三天,远在老家的姑妈就给他打了电话。姑妈在电话里问弟弟:“你妈会记得你的生日吗?她会不会给你买个蛋糕啊?要是不记得,你提醒她,别客气。”
弟弟赶快说:“不,妈妈记得,她都已经说过这事了。”
“说过了吗?”姑妈像是有点不相信似的。
姑妈一再叮嘱他:“你想要什么东西,就跟她提!她是你妈,该做的。”
弟弟回答:“知道了。”
其实舒一眉从来没说过关于生日的事,弟弟不知道她记得还是不记得这个日子。弟弟心里是这样替舒一眉解释的:他在这个家里还是第一次过生日,如果妈妈不记得,这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弟弟不愿意主动提这事,也不希望别人(比如姑妈)为他提。提醒妈妈为自己过生日,总是一件别扭的事。
这一天弟弟收到了张小晨的礼物。不过张小晨不是为弟弟的生日而送的,他一点儿不知道这是个歪打正着的事。
张小晨的妈妈新近养了一只猫,很漂亮的准波斯猫,跟真正波斯猫的区别就是两只眼睛一模一样绿。这样一来,家里的小鸟儿呆不住了。张小晨说,那猫的鼻子贼灵,老是嗅来嗅去,爬高爬低,还会用爪子开门开橱柜,他把鸟儿藏到任何地方,危险都是存在的。张小晨说,他可不愿意看到家里鸟尸横陈的惨状。况且猫是他妈妈养的,他要是偷偷打了猫,猫懂得向他妈告状,那家伙整个一个马屁精,奸细小人。
张小晨把鸟儿带到学校,藏在门卫老徐师傅的屋子里,放学的时候郑重其事交接给了弟弟。事先他还在“耐克”鞋盒上系了一条粉红的塑料丝带,加上一朵同样的颜色的花(都是花店门口垃圾桶里的剩余物资)。这样一系,小鸟儿就真的成了礼品,比较正式。同时奉送的还有一瓶米黄色肉虫。满满一瓶,他特意坐车去夫子庙买的。这瓶肉虫的细节,比起送一只小鸟儿,更让弟弟感动。
张小晨托起鞋盒说:“兄弟,我这就把它交给你了!你不能冷落它,不能欺负它,更不能抛弃它。它饿的时候你要及时喂它,它生病了你要带它去看兽医,它死了――”
这时候张小晨做了一个大大的停顿。弟弟惊讶地看见,泪水已经极难得地在这个顽皮孩子的眼眶里打转。
“它死了――”张小晨有点哽咽地说:“你要好好地埋葬它。千万不要让野猫偷吃了它的尸体。”
弟弟用双手接过了鞋盒。盒子里的小鸟儿在动,悉悉索索的,盒子就跟着动,也像是有了生命,活了起来。
弟弟觉得,张小晨说的这番话,有点像电影里面外国人结婚时,神父对新娘或者新郎说的话。以一种极其庄严的方式,把一个人的手,交到了另一个人的手里。
张小晨交出小鸟儿之后,很快就忘了他的难受,开始眉飞色舞谈起新的打算:他要寻找一只蓝色眼睛的公猫,来跟他们家里绿色眼睛的母猫配种,期望生下来一只真正的波斯猫,一只眼睛蓝色,一只眼睛绿色。
他说,如果猫的试验能够成功,长大之后他就学生物,然后把蓝眼睛人种的基因注射到黑眼睛人种的体内,生出一种奇妙的“波斯人”:一只眼睛蓝,一只眼睛黑。从左边看过去是白种人,从右边看过去是黄种人。这样的人做间谍最合适,根本不需要易容术。
弟弟捧着鞋盒,抿嘴笑着,听张小晨的胡言乱语。他脑子里想像着一个长了不同眼睛的人,感觉如果这个人真的出现在面前,肯定非常恐怖。
弟弟又想起来,张小晨以前还说过让邻居家的斑点狗跟一只猫杂交的话,现在不提了,可见没有希望了。肯定是斑点狗不同意。或者狗同意了,猫又不同意。总之,做这样的事情不容易,张小晨要实现他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六点半钟,弟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着张小晨的样子,拿镊子夹肉虫喂进小鸟儿嘴巴时,舒一眉敲响了他的房门。
舒一眉声音轻快地喊:“弟弟!弟弟!”
弟弟跳起来,一步窜上前,打开房门。
在房门洞开的一瞬间里,弟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惊讶地发现屋子里变了样:所有的顶灯壁灯台灯都熄灭了,桌上一只奶油蛋糕上插着点燃的小蜡烛,火苗儿快乐地跳着舞,就像幼儿园的小孩子排着队伍拍手欢迎客人来临一样。在房间的上空,从西向东,横贯着系了一条很长的彩带,带子上挂了满满一串汽球,红绿黄紫,热闹非凡。空调机正对着汽球呼呼地吹,那些轻盈的小东西们随风飘荡着,美女荡秋千一样好看。
舒一眉拉着弟弟的手,把他带到桌边,像天底下最温柔最爱孩子的母亲那样,说了一句话:“儿子,祝你生日快乐。”
弟弟呆愣了片刻,只有片刻,一分钟的时间吧,然后他张开嘴,眼睛眯成了月芽儿一样,无声地笑起来。他笑着笑着,眼睛里忽然有了眼泪,不好意思让舒一眉看见,装作弯腰去辨认用奶油写在蛋糕上的字,胳膊顺便从脸上扫过去,带掉了眼角溢出来的小水珠。
舒一眉双手扶住弟弟的肩,把他的身体轻轻扳过来,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赵安迪,”她说,“安宝儿,弟弟,我的宝贝儿!我生下你的时候,给你取了这个名字。可我还从来没有给你过一个生日。我不是一个好妈妈。你能够原谅我吗?”
弟弟拼命地点头:“妈妈,等我长大后,我会每年给你过生日的。”
舒一眉一下子就哭了。她又哭又笑,眼泪哗哗地流,把弟弟的脑袋抱起来,勾着头去亲他。她亲他的额头,亲他的鼻子,亲他的脸颊和耳朵。她把湿滤滤的泪水糊得弟弟满脸都是,让弟弟难为情得要命。
舒一眉从来都没有这样,让自己的感情恣意泛滥。这个隐忍的、压抑的、忧郁和高傲的人,她在这个晚上尽情地释放了自己,同时也是解救了自己。
舒一眉声音哽咽地说:“弟弟,安宝儿,你要是喜欢妈妈,你也亲我一次。”
说完这句话,舒一眉一下子直起了腰。她的脸上忽然有了一种紧张。紧张和害怕,和期盼。她在紧张期盼着弟弟的反应。
弟弟抬起头,微微地皱着眉,表情显得庄重和严肃,琢磨舒一眉的脸。他在想,在他的婴儿时代,他还没有学会认识人的时候,这张脸是什么样子?也像现在一样美丽和年轻吗?她第一次解开衣襟给他喂奶的时候,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脸上有喜悦和羞涩吗?
弟弟于是踮起了脚,如同舒一眉抱住他的脑袋一样,抱住他的妈妈,轻轻勾下她的头,嘴唇贴上她的脸颊,很久都没有离开。
他闻到了她脸上润肤霜的淡淡香气,衣领上橙花的清幽,和皮肤中散发出来的温暖的呼吸。这是舒一眉的气味。妈妈的气味。
他用劲地将嘴唇贴紧她的脸,并且希望永远这样:抱住她,亲吻她。
可儿的妈妈舒宁静,突然有一天成了一家超大规模茶社的餐食领班。
事情是这样开头的:有一次舒宁静和她的几个好姐妹去茶社打麻将,中午不回家,叫了茶社里的简餐吃。舒宁静叫的是一份豉汗排骨饭。她一吃就吃出来不对,豉汁熬得不对,排骨煎得也不对。舒宁静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对食物烹制的不尊重,她马上起身去找经理,态度很严肃,讲道理,摆事实,说明茶社里的简餐应该怎样做,顺便又拿起一份菜单,指出还可以加添哪些哪些品种在单子上。
舒宁静这段时间只为可儿做饭。可儿在意身材,不肯多吃,舒宁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家里憋得发慌。她逮住了这个教导茶社经理的机会,情不自禁地有了超常发挥,把她几年中在家里研读和操作美食的经验谈得头头是道。那个经理就像是中了魔法一样地坐着听她谈,听得一惊一乍,眼珠子瞪成了牛铃铛。
经理在舒宁静告辞的时候,非但免了她那一桌人茶水和简餐的单,还不无谦恭地表示,改日要专门到府上拜访。
舒宁静以为人家不过是客气,这么一说罢了。谁料想过两天经理真的找她去了,还随身带着一份用工合同,聘请舒宁静当这家茶社的全职餐食领班。舒宁静打电话告诉舒一眉说,她当时死活都不敢相信,以为那个经理疯了,又怀疑人家是不是迷恋上她了,因为舒宁静怎么说也是一个余韵犹存的美妇人。
舒宁静考虑了三天,结果是欣然应聘。她说,不是她缺钱用,是她要让宝林看看,他一直视为家中旧花瓶的这个前妻,其实擦一擦可以成为拍卖会上的宝物。
放寒假期间,外婆特意带了弟弟去那个茶社喝茶吃简餐,想亲眼见识一下舒宁静当领班之后的风采。
那天舒宁静穿着一套藏青收腰小西服,胸前别了一枚亮闪闪的“领班”胸牌,头发盘起来别在脑后,脸上化着淡妆,看上去比五星级大酒店的领班还要神气。舒宁静得意地告诉外婆说,她才来了一个月,茶社的经理已经给她加过一次薪了,那人现在变着法儿地巴结她,就怕她有一天会被五星级大酒店挖过去。
舒宁静安排外婆和弟弟坐在里面最暖和的位置上,做主给他们要了两份饭:外婆是一份海鲜煲仔饭,原材料很普通,但是加了一种很特殊的带辣味的汁。舒宁静说,这是她从一本意大利菜谱上学到的,用在煲仔饭里,中西风味结合。给弟弟的一份,有一串用竹签穿起来的彩色的球,白色和绿色,一半对一半,互不掺合。舒宁静解释道,白色的是土豆泥,绿色的是蚕豆泥。白色那一边是咸的,绿色这一边是甜的。她说,跟父母来茶馆的小孩子们都喜欢吃。
外婆尝了一个弟弟盘子里的球。她啧了一声说:就这个东西啊!小孩子会喜欢这个?根本就是玩花样经哦!她一点儿不能理解,现在的消费文化是“眼球文化”,谁能够创新谁才能立足。
在这一点上,舒宁静正好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和乐趣,所以她的前途还很大。
有一个星期天,弟弟的“前姨夫”宝林把舒一眉约出去,非常正式地问了她一件事:那个教初中英语的老师,老是在她家里出出进进的,叫李轻松的大个儿,他有没有可能成为弟弟的继父?
舒一眉马上有了警惕,问宝林说这话什么意思?
宝林说,就是想问问,核实一下,如果有可能,他就决定成全李轻松,帮一帮这个人。毕竟曾经是亲戚,舒一眉是可儿的姨妈,亲戚不帮亲戚,留着这个名份有什么用?
舒一眉急了,催宝林赶快说,到底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