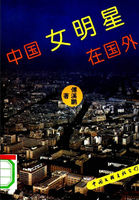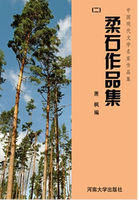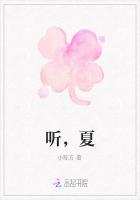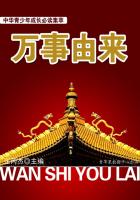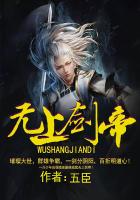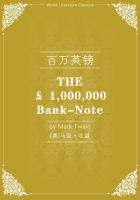蓝天深处飘泊着苍老的白云,已近中午的春天阳光饴糖般绵软腥红,缓缓注入水中,鹅蛋形的湖面在阳光的融和下亮得像一面新磨出的镜子。有风掠过,镜面光点闪烁,白茫茫一片五色金属的颤音在风中交织,宛如一幅会唱歌的画。
我看着眼前黄泗浦河水,思绪却想着远方——长江。长江水,奔腾不息,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它都无所畏惧,不知疲倦的向前……
长江源头的那一滴滴水是千年冰川的融化,长江的水融会了千年冰川的精华;长江水“无所畏惧,不知疲倦”地向前,深蕴着开拓进取、勇于牺牲的精神。“你从雪山走来,你向东海奔去”,正如《长江之歌》中唱的那样,从青藏高原各拉丹冬雪山到入海口,行走6380公里的长江横贯中国,每时每刻都奔腾向前激荡着流向大海,实现与世界的交融。长江的水哺育了她的儿女,她的勇往直前精神也为儿女们所继承。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她的儿女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鉴真,像一炷香,把自己点燃。一个固执的盲者,他将光明付与海浪,付与舟楫,付与飓风,付与誓言。
鉴真及其弟子六次东渡的曲折坎坷,向后人昭示了一个道理:只有像长江水那样,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才有可能攻坚克难,铸造成功。
如果说黑暗在鉴真心中是另一种光明的话,那么困难,对于张家港人来说,则成为了另一种希望;张家港速度就是张家港人从鉴真东渡的历史故事中,悟出鉴真最为可贵的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并付之于实践搏得的。
张家港速度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举世震惊的“中国奇迹”,就像传说中的阿拉丁神灯那么神奇,说给我一座城市吧,荒草萋萋、人烟寂寥的海滩、渔村就建成了一座城市;说建造一座大坝吧,世界水利史上就增添了新的名词———葛州坝、三峡大坝……
张家港让一座城市有沧海桑田的诗意是来自于精神,长江两岸乃至整个中国龙的巨变也是来自于精神。
东渡苑之神奥在于让人从鉴真精神中看到了长江精神,看到了张家港精神与之一脉相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不过,我今天听这曲,却是另一种感慨。东渡苑深蕴着一部历史,一部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历史。因为这里既是我们祖先一千多年前曾恩泽过那个岛国民族的最好见证,也是上世纪30年代遭受这个岛国铁蹄践踏蹂躏而靠“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长江精神、敢于涉险永不言败的鉴真东渡精神,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崛起的见证。
浪可淘英雄,却无法淘去英雄之精神——长江精神、鉴真精神,还有与之一脉相承的张家港精神,这些精神将会像长江水一样,向前,向前!流淌亿万年。
走进清晏园
四月的清晨,清晏园清风习习、翠鸟啼鸣。
走进清晏园,就走进三百多年前河督府那深沉的宁静和庄重。
在未来之前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特性,使水一般以流域或河系为单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治理、开发互相影响,甚至一河发洪水也可能影响到相邻的河流。水的这一自然特征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权威性的中枢机构统筹管理水务活动。
康熙十五年,黄河冲决王营,高家堰决口达34处,治理一年多无显效,朝廷决定临阵易帅。康熙从众多人选中调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派他治河。河道总督衙门是驻京外的国家部级单位,河道总督直接受皇帝领导。新任河道总督靳辅感到责任重大,为靠前指挥治水,来到淮安清江浦,以明户部分司公署旧址“凿池种树,以为行馆”,清晏园由此诞生。此后各任河督或南河总督皆驻节于此。康熙四次,乾隆六次亲临这里视河道,查巡漕运。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河督麟庆对清晏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改造。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裁撤河督,以漕运总管河务,漕督迁驻于此。
有人说,是大运河的漕运、盐运推动了淮安的繁荣。我想,这话虽对,但不完全,还要加上治水。
“淮”字的组成是“氵”旁加一“隹”字,淮意吉,但离不开“水”。文明从水开始。水是文明的摇篮,是以农业为本的民族的命脉。从青莲岗遗物可见,大约距今7000年—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栽种水稻。相传大禹曾至境内治水,“使淮水永安”。正像那悠悠的淮水,淮安的历史源远流长。淮安人对淮河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早在远古时期,淮河就在这里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然而,同样是这条河,1194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一部分河水经封丘、长垣、定陶向东南流,通过泗水入淮。从此,淮河遭到了厄运,变成了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一直到20世纪中叶,平均每年一次的水灾使这块土地与淮河结下了千年的恩怨。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东方社会是治水社会,一切围绕着治水进行。东方文明是治水的产物。他还第一次提出了“水利文明”的概念,指出“凡是依靠政府管理的大规模水利设施——无论是生产性的(为了灌溉),还是保护性的(为了防洪)——而推行其农业制度的文明时期,即水利文明。”
“江淮熟,天下足”,描写的就是当年淮安府为中心的这一产粮腹地。如果说,在黄河夺淮以前,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一个五谷丰登的富地,那么黄河夺淮入海以后给淮河流域特别是淮安带来的灾难就特别深重。明代的高家堰应该是治水史上最著名的壮举。但这个高家堰建成以后,虽然暂时可以保证漕运,但洪泽湖的水位抬高,却形成了一个人工的悬湖。这一悬湖就像一盆水顶在一个人的头上,那盆沿很不牢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闹出些事来。因此,盆下的人,甚至包括旁观者心里都会不安。
京杭大运河是支撑着中国经济命脉的一条航道,而淮安是沟通南北的水运码头。因此,千百年来,淮安就一直是在因水带来的祸与福中生存和发展的。始建于北宋的一座酒楼,后来取名镇淮楼,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包括朝廷对治水的重视,还可以看出对治水的一种无奈。河下镇运河河堤上的一块石碑,更可以看出朝廷的心思——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从这儿上岸,看了后就在这儿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把土堤改建成石堤。
环境的挑战产生文明。67公里长的洪泽湖大堤,早先为土坝,后全改筑石坝,从明朝万历皇帝到清乾隆皇帝,修了171年,共选用了6万多块千斤以上条形巨石。如果用单块条石头尾相接,那么可以从淮安一直铺到北京。工程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治水与文明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与洪涝、干旱作斗争而不断进步的历史。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历史进程中,水利文明自始至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治水活动不仅参与了中华物质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精神文明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蕴含着治水的成果。
事实上,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都是处在大江大河流域,其四大源流是指尼罗河文明(古埃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又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巴比伦)、印度河文明(古印度)、黄河文明(古中国),顾名思义,它们都是江河孕育的人类古文明。国家民族如此,地方亦如此。而无论是四大文明古国,还是文明淮安,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了治水的能力或者说制河权。所谓制河权,一是指控制河流、治理河流的能力;二是指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否则,虽有河流,也不可能产生文明。
有人说,通过了解废墟,我们进入历史深处。清晏园虽不是废墟,但它是从废墟中获得新生的。捻军攻下清江浦,火焚清晏园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漕运总督吴棠于原址复建时,将七倒八歪的古御碑一律树立于荷芳书院东西两侧及北侧的碑亭和碑廊内,有计划排列。清晏园内计有康熙帝御碑一块,乾隆帝御碑13块,道光帝御碑一块。受御赐者均为河道总督,计有高斌、高晋、张鹏翮、白钟山、李奉翰、黎世序等六人。
读史令人清醒。康熙帝第四次南巡留给河督张鹏翮的题辞。张鹏翮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清官,治河也有功,他指挥数十万民工治河,历时8年,黄淮大治,漕运通达,所以康熙皇帝专程来他处视察慰问以示褒奖。皇帝来了,总要将衙门整治一番才好,于是张河督就将“淮园”修葺一新。但一向讲究节俭的康熙帝倒不乐意了,特御制了《河工箴》:“自古水患,惟河为大。治之有方,民乃无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赖。降及汉唐,决复未艾。渐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议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既弭其患,复资其力。矧此一方,耕凿失职。泽国波臣,恫鳏已极。肩兹巨任,曷容怠佚。毋俾金堤溃于蚁穴,毋使田庐沦为蛟窟。毋徒糜国帑而势难终日。毋虚动畚筑而功鲜核实。务图先事尽利导策,莫悔后时饬补苴术。勿即私而背公,勿辞劳而就逸。惟洁清而自持,兼集思而广益。则患无不除,绩可光册。示我河臣,敬哉以勖。”同时赐“澹泊宁静”四字。康熙帝的题字,矗立在前,高大醒目,引人沉思。
而荷芳书院,则是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河督高斌为迎接女婿乾隆皇帝所建。这年乾隆效法他爷爷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高斌的女儿高佳氏是乾隆的孝贤皇贵妃,所以高斌特破费建了一座不俗的书院接驾。乾隆见后对其大加赏识,喜滋滋的勒碑记事。
然而,高斌虽四任总河,前后达38年之久,又是乾隆的老丈人,照理这个后台硬上了天。但即使如此,只要河务上出了问题,也是毫不留情的。
史海遨游中,你无时无刻不在被先人奋力进取的精神所感奋着。
高耸在人们头上的“悬湖”终于在公元1825年又一次水漫决堤。当时因母亲去世在家守丧的林则徐被急招到淮安堵水,他率领人们在决口的大堤后面修筑了另一道石堤,成功地堵住了洪水……
读史也使人震惊。
从乾隆三十年,直至裁撤的一百年间,南河总督署每年从国库里领取600万到1000万两不等的白银。而这些银两用于治理河道、贪污行贿,还有吃喝招待,约各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从乾隆中期一直到道光末年,一百年中就挪占了治河的专项经费3亿两银子用于大吃大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可据说在清晏园内的理河厅就曾经上演过从辰时到夜半没有终止的宴席,最长宴席延续几天几夜。清康熙年间的《淮安府志》中记载:“涉江以北,宴会珍错之盛,淮安为最。民间或延贵客,陈设方丈,伎乐杂陈,珍氏百味,一筵费数金。”乾隆、嘉庆年间,有关淮扬宴席的记载更多。如,他们的“舆台厮养皆食厌珍错”。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连他们家里的轿夫和仆人都吃腻了山珍海味。
《清稗类钞·饮食类》记载,说天下五大名筵,淮安独居其二。一为全鳝席,以鳝为主,配以“牛羊豸鸡鸭”,“号称一百单八品”;一为全羊席,“多至七八十品”;其实应该独居其三。对满汉全席,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在《古今食事》的“河工与盐商”一章中,以大量的史料说明它源自淮安。他说,河道总督长期住在淮安。淮扬菜的形成与豪奢饮宴有密切关系。而搞水利的官员既有钱吃又有时间研究吃,因为忙“河工”一年仅三两个月,余下的时间都用在吃上,自然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了。
因漕运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可以说淮安也就成了一个烹饪技艺最大的一个实验场。这种机遇是很难得的。因为它集南北的美食之长和烹饪技术之长,是相融相长的一个过程。正是这空前绝后的盛宴,吃灭了腐败的清政府,但也吃出了极具风味的美食。
清晏园子的名字,也是在不断地改变。河道总督靳辅驻节后,将西园改为淮园。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当时河道总督吴璥,徘徊在一块块皇帝的题辞碑前,看着“绩奏安澜”等褒奖的笔墨倒没有感悟,但看到康熙帝的“澹泊宁静”却心有所动。他将园子改名为澹园。八年后,他再以尚书任上来当河督,因治河失误,革去二品顶带,留任效力。后他再度成功,官复原职。这时,他将园子改名为清晏园,取河清海晏之意。光绪年间,有河督要去任时,又改为留园,“用以留示后之览者”之意。1928年曾更名城南公园,1946年为纪念叶挺将军,又更名为叶挺公园,1948年复名城南公园。1983年,市政府对园林进行增修,形成现在规模。1989年园子重新修整,又改回清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