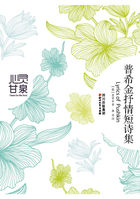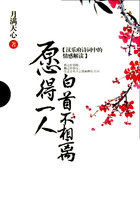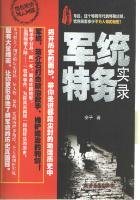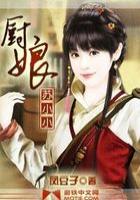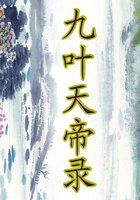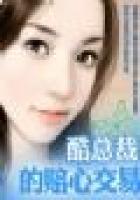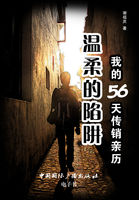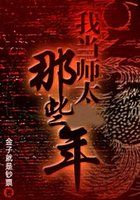淘气的小皇帝胡适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宫中逢二休息)去看他。”胡适在日记里说得轻描淡写,没把宣统帝看得多大多粗,你约我去喝茶聊天不要紧,但也得看看我有没有时间。在宣统帝溥仪看来,约胡适也没什么正经事,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他只是听家教老师老是说某某好生了得,国中有如此高人,朕当然要见见,就多少有点淘气地给胡适打了这个电话,甚至还带点恶作剧心理——那年他才17岁,正是爱调皮捣蛋的年纪。
那个时候电话刚传入中国不久,却没人给溥仪装电话。他这个皇上虽然是傀儡,可是傀儡也总是皇上啊,堂堂皇室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像什么话?溥仪吵死吵活,结果给装了一部。才装电话的人总是好奇,一连好几天电话一声不响,淘气的小皇帝坐不住了,他拿起电话到处乱打,先是给京剧名角段小楼家打电话,开口一声“我是宣统”,把段小楼吓得一哆嗦。小皇上在电话这头听到咚的一声,也不知道那头是电话掉地上还是段小楼跪在地上磕头,开心得哈哈大笑。他又给一个叫狗子的杂技小丑打电话。这个狗子跟溥仪关系不错,他一来,小皇帝就关上祈年殿大门,两个伙伴玩疯了。后来小皇帝想吃烤鸭,就给东兴楼饭馆打电话,让他们送一只烤鸭来。大厨不知道这皇上的真假,吓得屁也不敢放一个。小皇帝笑痛了肚子,拿着话筒不肯放下,可是接下来给谁打呢?想来想去忽然眼前一亮:对,打给胡大博士。
胡适那天正好在家,本来家里电话统统由秘书接,巧的是那天秘书外出,正好是胡适本人接到电话。对方在电话中阴阳怪气地说:“你可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猜我是谁?”胡适一愣,说:“您是谁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对方忽然笑起来:“哈哈哈,甭猜啦,我说了吧,我是宣统呵!”胡适大吃一惊:“啊,宣统?……皇上?”对方说:“猜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朕瞅瞅吧。”
胡适放下电话,一时像做梦一样,又有点不太相信,别是哪个家伙搞恶作剧,然后等着看胡适的笑话吧?胡适想了半天,就给溥仪的洋家教庄士敦打了个电话。庄士敦告诉他,打电话的正是宣统皇上。胡适没有进过宫,连忙向庄士敦打听进宫的规矩。庄士敦说:“他请你来的,你是新派人士,不必太拘礼,磕头就免了。这小皇上脾气还好,没事的,你来吧。”
那天胡适进宫费了一些周折,太监忘了关照守门的护兵,胡适一个人走到神武门,那些把门的兵丁死活不让他进去,怎么说也不行,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后来护兵见胡适不走,半信半疑到奏事处询问,才发现真有这么回事,就放了他进来。胡适在养心殿见着了皇上。溥仪的样子很清秀,有点瘦弱,眼睛是高度近视,比胡适还厉害,穿着一件蓝袍子和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的地方放着许多书,炕上有当天的报纸十几种,比如《晨报》、《英文快报》等。胡适开口叫他“皇上”,溥仪则称胡适为“先生”。
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记载道:“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问了他白话文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等等。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书,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在背地里吵闹起来了。”
为寂寞少年辩护
小皇帝召见胡适不但在宫中炸了油锅,在文化圈更是吵得沸沸扬扬,甚至出现多种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跪拜”,一时云里雾里令人晕头转向。为正视听,胡适写了篇《宣统与胡适》一文,他说:“一个17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很可怜,想找个人谈谈,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盘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诧的新闻了。”
对于遗老们来说,胡适是新新人类,他们不能容忍皇上受到“污染”。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来说,皇帝是封建的“糟粕”,注定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不能容忍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为。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睛,双方都恨不得在胡适头上砍几刀。而胡适只是脸红脖子粗地辩解:“他在我眼里不是皇上,就是一个很可怜的寂寞少年,他太寂寞太可怜了。”几天后,胡适还在日记里为溥仪写了一首诗: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诗歌一经发表,就有人推敲出此诗不是写给溥仪的,是写给胡适的情人曹诚英的。可是至少从字面上看,这是写给溥仪的,胡适十分同情这个17岁少年,萌生出拯救之心。当然胡适也很清楚,这个少年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人,他代表着旧的封建制度,就像胡适自己代表着新兴的民主体制一样。他去看溥仪也不是简简单单地去看一个人,实际上是新旧两种制度在特定时代的交会。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溥仪确实太可怜了,胡适要救他。胡适在等待一个时机,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驱兵将溥仪赶出了故宫,并废除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当时全国一片叫好之声。胡适得到消息,立刻致信政府表示抗议:“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堂堂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几个没文化的草莽军阀,凭着自己的武力,就把手无寸铁的那些老老少少,还有白面书生似的皇帝赶出宫去,尽管是打着正义的名头。但当时是签订了协议的,清宫放下武器,然后就给清宫相应的优惠待遇。而在条约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把溥仪赶出故宫,这在胡适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政府首要的是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果你不去遵守你的法律,那么就没有人去遵守这个法律。
胡适为溥仪的辩护引来全国知识界一片炮轰,“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甚至有人提议将胡适赶出北平,所以才发生了胡适为溥仪辩护之事。
胡适苍白的辩护最终被淹没,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11月29日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次年2月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这个17岁的少年怀揣一颗仇恨的种子,最终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又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