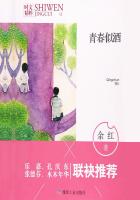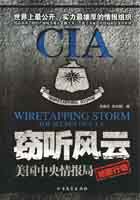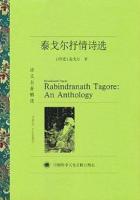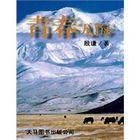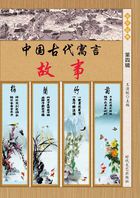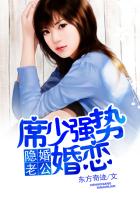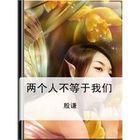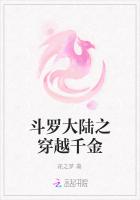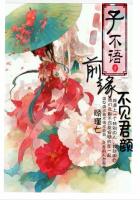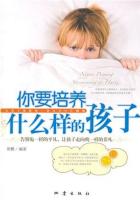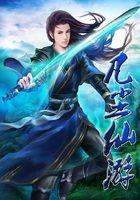三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
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理论观点最早形成于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接受,并非像梁启超的后期文学理论那样形成于自觉的文化立场选择。关于梁实秋如何在文学理论中接受白璧德的影响这一问题,当前人们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这一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国内梁实秋研究中的难点、热点问题。
特别是段怀清教授在《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非常仔细地梳理了梁实秋对白璧德思想的接受过程、借鉴的内容等等,并尽可能地进行了客观准确的评价。段先生的研究深入细致,所得出的结论准确恰当,让人信服。具体地说,段先生在《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先是从分析梁实秋对自己与白璧德之间的关系的几次说明入手,引出了白璧德对梁实秋的文学思想究竟有多大影响的问题。进而,他通过细致辨析梁实秋在接触白璧德前后的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变化,清楚地证明了梁氏与白璧德之间的思想师承关系的存在。他说:“最能够标示并记录梁实秋的文学思想观念从最初的浪漫倾向向古典训练和人文主义标准转化的,是他的《拜伦与浪漫主义》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这两篇论文。前者是他对于浪漫主义文学观最集中的认识和批评实践,后者则是他在初步接触到白璧德的人文思想和西方古典主义文学观之后,对于自己原来所持的浪漫思想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的初步清算。而将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比对,恰好反映出梁实秋从对浪漫派文学的赞扬到对‘唯美派’的纯艺术主张的清算告别的思想转变过程。”【32】
在证明了梁实秋与白璧德之间存在思想上的师承关系后,段先生展开了对这种师承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具体内涵的敏锐而细腻的分析。特别是就白璧德影响梁实秋文学批评的内容,段先生主要谈到了这样几个方面:白璧德帮助梁实秋实现了对重视情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思以及自我反思,使梁实秋重新认识到了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并激活了梁实秋的中国人文思想传统的记忆,白璧德的这些影响集中反映在了梁实秋所坚持的人性论文学观上等等。
具体就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所受到的白璧德的影响来看,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观点“人性论”,是从白璧德那儿借鉴而来的。不妨先看白璧德的“人性论”的具体内容。白璧德认为,一战后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根源在于传统道德观念信仰的沦丧,因而他主张回到传统中去寻找济世良方,希望通过复活古代人文主义精神、重塑人性来解救社会危机。这样他就把全部社会、政治、精神的问题都归结到人性问题,归结到人性善恶斗争这一伦理学问题,据此,他提出人的生活方式有“自然的”、“超自然的”和“人文的”三种。他认为,人文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他的文学批评也正是以这种人文主义的人性论为基础,始终围绕着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折射出显而易见的伦理色彩。譬如在广为人知的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1919年)中,白璧德批评了想象的过度放纵及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视其为文明之大敌,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滥觞。梁实秋不仅继承了白璧德的人性论,且将之与我国古代人文传统进行思想融合,建立起一套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学观。他是如何阐释人性的呢?正如前文曾引述过的,“人在超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梁实秋的这段文字,是他将白璧德的人性观与中国古代人文思想进行“融合贯通”的最完整的体现,反映了其人性论的实质:理性与理性控制。他追求的是人性的和谐与均衡,而这种追求又是与提倡中庸,强调“以理制欲”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相通的。
白璧德人文主义对梁实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具体影响还表现在,促使他立足于古典主义文学观,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全面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包括对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审视和检讨。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梁实秋“审查”新文学的创作,指出了新文学的诸多缺失。首先,梁实秋直接借用了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化观,反思了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白璧德把文化、文学分为“古典的”和“浪漫的”两类——“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古典”的是健康均衡、受理性制约的,“浪漫”是病态偏畸、逾越常轨的。梁实秋借用了白璧德的这一文化、文学分类观来审视文学史,认为西方思想文化史,包括文学史,就是两类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此消彼长。
即与主流性文学史观念相反,梁实秋并不以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是只承认有“现代文学”(即当代文学),不认为有“旧文学”或“新文学”的区分。他的一个大胆论点是:“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换句话说,梁实秋认为,文学并不能依时势转移而决定其“进步”与否,新的并不一定比旧的好,现代的也不见得比古代的强。这里,他实际上是要打破进化论的线性思维,力图对文学作古今并置的共时性考察。具体来说,就是先确定一个符合纯正“人性”的“至善至美的中心”,然后来评判各时代文学距离“中心”的远近:中心的是最高的,凡距离较远者便是二三流的文学,最下乘的是和中心背道而驰的。因此,他提出,文学研究的任务方法不再是叙述文学一代代“进步的历程”,而在品味确定各时代不同的文学距离纯正“人性”中心的远近程度。
这里,白璧德对文化、文学的“古典的”和“浪漫的”二分,以及崇尚古典文化、文学,被梁实秋借用来作为了观察新文学的准绳。梁氏把新文学定性为“浪漫”趋向的文学,视为一场“浪漫的混乱”,进而认为,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五四新文学,其主要资源不仅是“外国的”,而且又是偏重于西方近、现代的浪漫的思想文化,这一资源既不完整,也不健康。在批评五四新文学是“浪漫的混乱”时,梁实秋主要依据的就是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观念,包括比如文学应该表现“普遍的”、“常态的”人性,文学表现的态度应是“冷静清晰的”、“有纪律的”等创作原则。梁实秋的这些看法中,白璧德的深刻影响显而易见。
总之,正是在白璧德的影响下,梁实秋跳出了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传统,并实现了对它的重新审视和思想超越。在这一过程中,梁实秋也接受白璧德的西方思想文化史观念,建构起了自己认识、评价西方文学传统的思想框架,并对我国古代人文传统有了新的体认。后来,他进一步融汇中西,使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转化成了自己的思想血肉,以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从而奠定了自己在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独特地位。
也就是说,根据段怀清教授的分析,在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理论中,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不仅是指白璧德的影响促成了梁实秋文学思想的变化,而且指梁实秋即使在深入地掌握了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并娴熟地运用它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后,白璧德的人性观、古典主义文学观念等思想理念仍是梁实秋文学理论观念中的核心思想要素。所以,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人文传统的影响,很难给以很高的评价,虽然梁实秋后来从自己的独立思考出发,有时有意或者无意地淡化白璧德的影响,夸大中国古代人文传统的作用,这总不太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