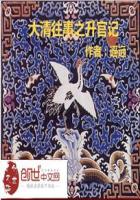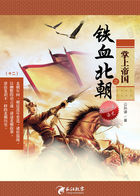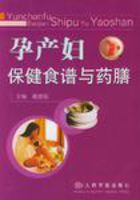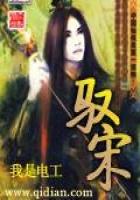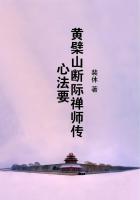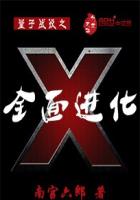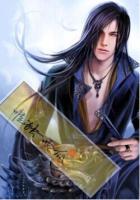这一场面相当生动,也相当惊险和血腥。吕四娘杀雍正的举动,经此描绘,完全如在目前。这里面有一句吕四娘的自陈,即为爷爷、爹爹报仇了。这句话是大有来历的。传说吕四娘是清初文人吕留良的孙女、吕葆中的女儿。吕留良因为著名文字狱曾静案的牵连,在雍正时,不仅已死多年的自己和长子吕葆中被戮尸,且次子吕毅中也被斩立决,所有亲族、弟子都被充军边疆。
这个大仇恨,就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梁羽生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在清朝的野史笔记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比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代述异》等野史就有关于吕四娘的记载。
这一说法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满汉对立的情绪比较浓郁,敷衍出吕四娘刺杀雍正这一段故事,可以满足汉族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排满情绪;二是人们大多有猎奇心理,雍正的死因一直不清不白,用吕四娘行刺这样一个段子,完全可以引起众人的“围观”。
这些,大概就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传说为什么长盛不衰、经久不息了。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历史学家在吕四娘刺杀雍正一事上也表现出轻信的态度,因为历史学家在史学界的权威性,他们的说法更能为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增加筹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学家陈怀的《清史要略》(1910年)吸收了不少无根据的、荒诞不经的野史材料,其中以宫闱史为最多,世祖出家、吕四娘刺雍正等传说都收入书中。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许国英为了反满清的需要,在其著作《清鉴易知录》(1917年)编造清朝皇室的丑事,把吕四娘刺雍正的事也作为信史写了进去。
这些历史学家的言说,当然是不可信的。同时代的史学家孟森就曾经在其《清史讲义》中对许国英进行了严厉批评:“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为失记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殁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愿谈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习。”可见,许国英等人的说法显然是荒诞的,孟森先生的斥责,的确切中了当时史学界浮躁之风弥漫的要害。
前不久,闲看一部叫《清宫秘档》的历史纪录片。片中根据《活计档》(皇宫日用物品内务府总账本)的记载,认为雍正可能死于丹毒。因为在雍正死前12天,在总管太监操办下,还有200斤用于炼丹的黑铅运进圆明园。这个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因此,对吕四娘刺杀雍正一说,我们大可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了之。
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
很明显,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满清一朝,大体上可以说没有建立现代学制,也根本没有“大学生”这个称谓,怎么会有“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这样的问题呢?这话从事实上来讲是有些道理的。但不管是古代学制,还是现代学制,其实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一个农家子弟要成为知识渊博的文化人,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古代,都要经过启蒙、学习、深造等过程,其学历与学力都处于不断累积提高的动态过程中。
因此,询问“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并非就是个无解的答案。
以现在的学制来说,要成为大学生,一般需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这一过程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与现代稍有不同的是,清代虽有官学、义学或书院,但并不普及,人们要想读书,大多得先入私塾。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即可以参加县里主持的考试,考取之后,再参加府考,由知府主持。通过县、府试的便可称为“童生”。之后又再参加院考,由省里的学政主持,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通过院考,便是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
成了秀才之后,可以到官办的学校入学。这些秀才又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供给粮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曾经的官费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秀才中特别的优秀的,入学后经过学政的推荐和朝廷的考试,有机会被选为国子监的学生,成为贡生、监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的大学生(参照史学家萧一山的说法)。
依此看来,在清朝要成为一个大学生似乎并不难,台阶只有童生、生员、贡生等几级,和现在也差不多。但实际上,难度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当时名额有限,竞争相当激烈。且学习的前景很富吸引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于下闻”。史料记载,读书人考上秀才入学以后,就可以穿蓝袍,戴银雀帽,见官不跪,荣耀乡里。——这种虚荣上的极大满足,促使天下读书人一齐奔上了考学这条大道。
其实,历尽艰难爬过“童生”的台阶,成为秀才、贡生,也不过刚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只有取得了秀才“学位”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考举人,然后才有机会参加会试,参加殿试,最终成为进士。
“物以稀为贵”。科举难之又难,考上的人少而又少,于是考上举人、进士便是极为光荣之事。
康熙三十八年,顺天贡生黄章考举人时,已是百岁老人,进场时,书“百岁观场”于灯,令其曾孙为前导,引为奇观。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十八岁的广东秀才谢启祚中得举人,后又参加会试,乾隆特别加恩于他,授司业衔。
名臣张之洞年轻时常以文章自负,但好酒,放荡不羁。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族兄张之万参加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状元。张之洞受此激励,一改旧日行迹,发愤读书,至同治二年(1863),以第三名的成绩中了探花,然而还是比其兄差了一点,到晚年张之洞仍然将此引为毕生憾事。
同为名臣的左宗棠只中过举人,没中过进士,这使他心里头长期不舒服。直到朝廷派他带兵去新疆平乱时,他借口要复习功课考进士,不肯带兵前去,朝廷不得不赐给他一个进士出身,可见进士这个名头在左宗棠心目中的份量。
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到死都还是秀才,一生郁郁,叫人为之心酸。正儿八经的海归思想家严复,虽然翻译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西学著作,却仍然想着如何去获得科举功名,结果四次都没有考中,心里郁闷,抽上了鸦片,以此麻醉自己。
参看这些史实,足见科举在当时人心中有多重。
举人、进士这些头衔,因为人们的推崇,逐渐成为一种荣耀的象征。
光绪三十一年(1905),涉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科举制终于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力并未消除。至詹天佑等留学归来时,科举早就停了多年,可朝廷还是补给了他们进士或举人的头衔。只是,至此时,科举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学制渐渐建立。科举的事情,也渐少有人问起了。
明角们的出场费
旧时没有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之类,娱乐业却同样十分兴盛。古代小说中描写的勾栏瓦肆,就常常挤满了听戏看热闹的人。从事娱乐业的人在当时的地位不高,被称为“戏子”,但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中间不乏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像明末的柳敬亭、《老残游记》中描绘的黑妞、白妞,便是其中“说书”的高手。
高手出场,当然不能和一般演员相比。至少他们的出场费要贵一些。那到底有多贵呢?
往远了说,恐怕说不明白。但晚清到现代,却还有些资料可查。
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晚清京戏盛行,汪桂芬、谭鑫培是其中名角,“声价绝高”。
汪这个人品德不行,经常收了人家的钱,却常常延迟登台或干脆不登台唱戏,搞得人家十分恼火,不时被告到官府里。
谭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也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唱堂会,价钱自然不菲,约五十两银子一出戏,连唱两出就是一百两。他爱惜自己的羽毛,通常唱起来也不超过两出,大概这样可以端高些身价。且说当时杨士骧出任北洋大臣,这位大帅是个不折不扣的戏迷。一日,听说谭鑫培到了天津,心痒难挠,忙托一位盐商去请谭来唱戏,哪知这位卖盐的企业家面子不大,虽然愿出一千两银子,但谭不肯答应。后来又是托人,又是求情,总算把谭说动了,谭的条件是只唱一出,绝不多唱。毕竟是名角,谭到杨府上一唱,杨士骧十分高兴,赏了八百两银子给他。加上盐商的报酬,这出戏谭鑫培共获银一千八百两。这个价钱在当时是蛮高的了,绝不亚于现在的那些顶级大腕们的出场费。
由于条件限制,当时的演员演出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在戏班里唱唱,一是给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家唱“堂会”。像现在的演员那样动不动就开个人演唱会,在那时是不多见的。
从收入来说,在戏班里唱,是比不上到富人家里唱“堂会”的。但唱“堂会”,须得有些名气才行,不然,谁请你啊?曾任北京电灯公司襄理的宝叔鸿是清朝宗室,他的老父亲墨琪(润西)庆祝七十大寿时,宝叔鸿办了一场堂会,请了一帮名角来唱戏,花了六千块现大洋。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一所普通四合院的价钱也不过四五百块,宝叔鸿请人一唱,就唱进去十多所房产。从这也可看出当时明星的出场费是如何惊人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演唱都以钱来计算的。有些名角为了人情、友谊之类,在别人需要时也是愿意出场助兴的。
以梅兰芳的名气,唱堂会的报酬自然不低。但在画家王少农八十寿辰的堂会上,梅兰芳演出了精彩的《麻姑献寿》,事后分文不取,只要了王少农为他画的一幅《梅兰图》。一时传为戏曲界的佳话。
对于普遍民众来说,名角是人中龙凤,可望而不可及。但有时这些成功人士的日子也不好过。
“欢迎陆荣廷,气死谭鑫培”这一当时的流行语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欢迎桂系军阀广西督军陆荣廷来北京,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举行堂会,重头戏是谭鑫培的《洪羊洞》,这时已经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谭鑫培正在病中,身体吃不消,便屡次推辞,但当局都不允,警察局还派专人来强请。
在威迫之下,谭鑫培只得带病出场,结果病情加重,回家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这事在梅兰芳的回忆录中记得很清楚。可见,名角也有伤心时啊。在这种情形下,你拿着再高的出场费又能怎样呢?
古医方的妙与谬
虽然对医学一窍不通,但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对中医还是保持着一种偏爱之情。所以,在阅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对于其中所载的医方也就相对比较关注。
前些日,读清代梁章钜的笔记《归田琐记》,发现第一卷中记载了多个医方。这些医方有些是他亲自验证过的,有些是道听途说的,其中有很多叫人惊异的地方。
其一,治疝气之方。主药为薏仁。方法是用东方墙壁上的土炒薏仁至黄色,然后用水把炒黄的薏仁煮烂,放入盆内,研成膏状,每天用米酒调服2钱,不几日即可治好。传说辛弃疾曾经得了疝气,阴囊重坠大如水杯,一位道人传授给他这个方子,治好了他的病。有一段时间,梁章钜侨居扬州邗江,正碰上房东患了疝气,很痛苦。梁章钜偶翻旧书,见到书中有张纸条,抄的就是辛弃疾用的那个药方。他赶紧告诉房东,结果不到五日,房东的病就好了。
其二,治喉鹅之方。喉鹅这种病症,就是喉间起泡,肿得厉害的话,将堵塞喉管,一旦救治不及,可能呼吸困难,甚至致毙。梁章钜听人说,当时有个钱夫人得了这个病,屡治屡发,十分痛苦。后来,她的丈夫听到一个药方:用几根断灯草,缠了指甲放在火上熏烤,等烤得黄干了,将两物研细,然后又用火烤臭虫十个,一并放入捣成粉末,再用银管把粉末吹向喉间起泡的地方,不久就可治愈。了解到这个药方不久后,钱夫人的病就复发了,比以前更为剧烈,周边的医生都束手无策。她的丈夫就按这个土方子,用银管吹了几次。后来喉间的肿泡忽然溃烂,钱夫人吐出了一碗左右脓痰,很快就好了,并且没有再复发。神效也!
其三,止血补伤之方。这个方子,梁章钜是从《竹叶亭杂记》中看来的。药方如下:生白附子十二两,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风、羌活各一两,各研极细末,外敷。据称,张子畏太守在去圆明园的路上,不小心翻了车,车夫被轮子压伤,把两边的肾脏都压出来了。也算机缘巧合,张子畏当时得到了这个药方,赶忙配药治疗车夫,半月过去,竟治愈了。
其四,治小孩吞铁方。此方由梁章钜从蔡文恭处转述。这个蔡文恭是一个大学士,平日常常校对些古书。有一次,他的孙子不小心吞了根铁钉,用了好多药都“打”不下来,看着日渐消瘦下去。这时,蔡文恭正校对一本叫做《苏沈良方》的书,中间就记载了治疗“吞铁物”的医方:“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于是依法治之,果然他小孙子肚子里的铁钉被“打”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