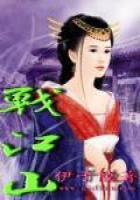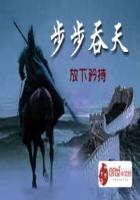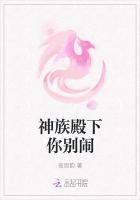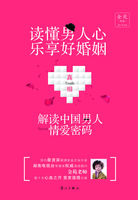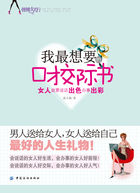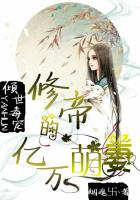5.自我表态
宝廷自己是怎么看因艳遇丢官这件事的呢?
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对宝廷的事迹有多处记载。据称,宝廷纳妓弃官后,有诗言志:“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
全诗明白如话,直抒胸臆。前两句讲自己的文采和买妓的事实,后两句表明心志,有石破天惊之慨。比起那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的伪道学来说,确实可爱得多了。
6.晚节可佩
虽然宝廷在男女问题上不拘小节,但在其他操守上却是令人称道的。黄秋岳同书有一节小标题即是“宝竹坡(宝廷)晚年贫困”,说“竹坡先生之贫特甚,罢官后,徜徉京西诸山间。得诗数百首,春寒如严冬,而著缊袍,面破棉见。松禅诗中之‘长平’,盖记实也。直声著天下,身为贵胄,交游便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本来,宝廷罢官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都主动拒绝了,守贫以终,行吟山水,或许是厌恶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或许是预感到大厦之将倾的历史危机,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现实表现,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名士风度了。
1890年,归隐数年之后,宝廷穷蹙潦倒,病死西山。
消息传到福州,当年的战友陈宝琛写下《哭竹坡》一诗,结尾有一句“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认为宝廷纳妓罢官并非误了自己的前途,而是看破了清朝将亡的命运,以此来躲避被历史洪流裹挟而去的灾难。这种见识,也算是宝廷的知己了。
关于宝廷纳妓故事,正史大多不载。《清史稿》只有简短几句:“七年,授内阁学士,出典福建乡试。既蒇事,还朝,以在途纳江山船伎为妾自劾,罢官隐居,筑室西山,往居之。”语句不多,但亦足证明此事不是杜撰的。
宝廷之事,让人唏嘘。一个人若以道德高标要求别人,自己也要严守道德标准,否则当自己犯下同样的道德错误时,必然会付出更大代价。宝廷弹劾别人不遗余力,当自身犯错时,不得不自劾去官,归隐田园,以实际行动为自己的错误买了单。同时,让人感慨。旧时的士大夫毕竟是有气节的。宝廷在纳妓问题上坦率得可爱可敬,归隐之后的表现也叫人心生感佩。这是不易做到的。如今的现实中,能做到宝廷这样的,只怕不多吧!
补记:
关于江山船,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余绪。1933年11月13日郁达夫游兰溪,他在游记中写道:“晚上有人请客,在三角洲边,江山船上吃晚饭。兰溪人应酬,大抵在船上,与在菜馆里请客比较起来,价并不贵,而菜味反好,所以江边花事,会历久不衰。从前建德桐庐富阳闻家堰一带,直至杭州,各埠都有花舫,现在则只剩得兰溪衢州的几处了,九姓渔船,将来大约要断绝生路。”(《杭江小历纪程》)郁达夫在文中对江山船的发展前景颇为悲观,但从他的记载来看,至少在他游历的当时,江山船还是作为一种风气存在着的。不知自宝廷事件后的数十年间,又有多少故事在江山船上发生?可为一叹也!
趣联偶拾耐回味
小时住在湘西农村,每到过年时节,父亲总要写些对联贴上。所用联句,无非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寄托着纯朴的人们对于新年的祝福与期望。有资料称,第一副春联为五代后蜀主孟昶所写,有一年春节,他在寝室门桃符板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自此后,对联的习俗便流传开来。
其实,对联这种文学形式,早在五代前就已经产生。《易经》、《诗经》中就有对联的样式。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就是很好的对联。西晋左思《咏史》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也是不错的联语。唐朝的律诗中,同样有无数严谨的对联。比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商隐的“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等等,莫不是绝好的对联。
但对联终究和一首诗中的联语有所不同。诗中联语,常常要与整个诗境保持一致,其独立性不是那么强。对联却两句一对,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有时还加上横披,——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其趣味与诗词歌赋又有所不同。
到清朝时,这种文体通过几代文人的浸润和发展,已经相当完备。
不管是风景名胜,还是日常生活中,对联已到处可见。其中有些对联,是文人们为了自娱自乐,或是描摹,或是讽刺,或是表达某种心情,拟出来在一个小圈子里传看,并不一定要写出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久之也形成一种有趣的效应和氛围。
在阅读清代资料时,偶然看到关于此类对联的记载,不由得随手录下来。
一正一反的戏拟对联
嘉庆年间,汪瑟庵担任安徽学政时,到金陵试院(南京)考录遗才(秀才参加乡试,先要经过学道的科考录送,临时添补核准的,称为“遗才”)。汪学政想起自己的经历,不由得兴起,撰写了一幅对联:“三年灯火,原期此日飞腾,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风,曾记昔时辛苦,仍是一囊琴剑,重到钟山。”作者的意思很明显,说的是秀才们三年苦读,期望这一日能通过考试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我如果有点偏私,那就有如江水;我自己也曾苦读五年,昔日辛苦常在心头,现在仍是一囊琴剑,又来到金陵。这幅对联感情丰沛,情真语切,文词优美,确实是一幅佳构。
到了道光初年,有位教官送考来到金陵,参照往年的做法,这位教官向主考的学政要两个遗才名额,如果在往常,这个名额是应该给的。但这年来的是沈小湖学政,不好通融,把所有求情的人一概谢绝了。
这位教官心里怨气积郁,就把当年汪瑟庵撰的联改了:“三年辛苦,只求两个遗才,倘蒙片念垂思,感深江水;百计哀号,不管八棚伺候,拼著一条老命,撞死钟山。”这样一改,原来联语的趣味没有了,但把自己心中那股怨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你看,他说,三年辛苦读书,只求两个遗才名额,倘若你能答应,我的感激之深如同江水;但我千般哀求,不管考棚里表现如何,拼着老命,在钟山撞死算了。这应该是恨极后的玩笑之语。好在沈小湖学政肚量较大,后来听到这事情,一笑置之,也不怪罪。
暗含姓名的对联
又说道光年间,一位巡抚到湖南任职。
初到时,有当地官员来迎。谈话中,巡抚问湖南有没有什么新闻,那官员没作准备,想了半天,才答道:“没有什么新闻。只有副对联甚为工整。说的是有个县令叫续立人,有人用他的名字戏拟了一副对联:‘尊姓原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这对联在当地流传颇广,巡抚也大笑而罢。解读这副对联,倒也蛮奇巧的。
从上联“尊姓原来貂不足”看,这里面暗含了一个典故,《晋书赵王伦传》载:“貂不足,狗尾续。”这一联说的就这是个县令姓“续”。从下联“大名倒转豕而啼”看,也须用典故来解释,《左传庄公八年》中有“豕人立而啼”的说法,把“人立”倒转过来就是“立人”,把人讽刺得如猪一样。
全联没有“续立人”三字,但却把三个字暗暗包含其中,这个文字游戏可称得上高妙了。
据说,那巡抚上任后,找了个岔子,把续立人的官给免了,不知是不是这副对联的缘故。如果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那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说到关于姓名的联,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记载了一副妙联。
晚清时,有两兄弟在朝廷当官,哥哥叫高树,弟弟叫高枬,都是朝廷里相当于御史一级的干部,另外有个叫乔茂轩(字树枬)的学部左丞,和这两兄弟都是从四川来北京作官的。
有人拟了副上联:“茂老并吞双御史。”说是乔树枬的名字里并吞了高树、高枬兄弟的大名,颇为巧妙。
下联也对得工整:“辅翁颠倒一中堂。”原来辅翁是学部右丞孟庆荣的号,而主掌学部的协办大学士正是荣庆。庆荣和荣庆,刚好是颠倒过来的。
这副对联妙相绾合,传诵一时,的确难得。
讽刺性的对联
戏拟的联语,除了巧妙之外,常有以讽刺见长的。
清末,袁世凯窃国称帝,为许多人唾弃。有人拟了一副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上联少了一个“八”字,隐喻“王八”的意思;下联少了一个“耻”字,显然是说袁氏“无耻”,骂得十分痛快。
那时,维新干将康有为晚节不保,正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章太炎撰联讽刺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这副对联以“有为”二字结尾,本来就很绝妙。里面含的意思且更进一层,上联来自于《礼记·中庸》:“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出自《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骂得也很过瘾。
当然,个人拟的对联,“正经”的也不少。“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拟一联:“咬定一两句,终身得力;栽成六七竿,四壁皆清。”上联写读经,下联谈栽竹,虽不见“书、竹”二字,但意义明了。同时,展现了作者潜心向学、清卓独立的高尚品格。
“完人”不“完”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出名了,他的许多事情很快被美化。经过多人的传颂和演绎,缺点说成了优点,瑕疵当成了美丽,整个人被供奉起来,变成了“神”一样完美。
但实际上,一个人要在做人做事上真正达到完美,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完人”这种人,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么现在呢,当然也没有。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也只是“传说”而已。
例一:汤寿潜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大都知道汤寿潜这个人。汤寿潜(1856-1917),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
看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大都是把他当成“完人”来看待的。特别是讲到他淡泊名利的事迹,有人不自觉地会感慨万千。确实,汤寿潜对于做官、敛财不太感兴趣,一生中有多次的辞官经历。
且列举如下:
1895年,他被授为安徽青阳县令,在任仅三月,便辞归故里。
1901年,郑孝胥推荐他任职汉冶萍铁厂及南洋公学,他辞而不就。
1903年4月,有人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不干。
1904年,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不赴任。
1909年,浙江巡抚请他担任浙江署财政议绅,负责全省财政,不就。同年8月,被授云南按察使,未上任,多次上奏辞职。11月,授江西提学使,亦辞不受。
1911年11月就任浙江都督,1912年1月15日辞去此职。民国政府任命他为交通总长,亦未上任。“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傅国涌《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按常理说,这么不愿当官的人,在名利上自然已达到“完人”的境地,但同时代的人却不这么看。
当时的外交家汪大燮说:在杭州铁路问题上,“蛰仙为人,原足钦佩,唯此事恐其干誉之心太重……,蛰仙本是捧名教二字做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约总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这意思就是说,汤寿潜虽然不图官位和实际性利益,但本质上却在追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