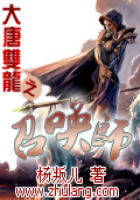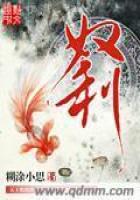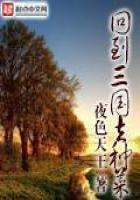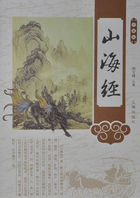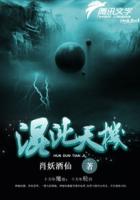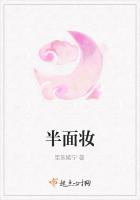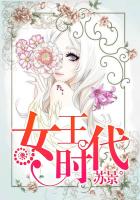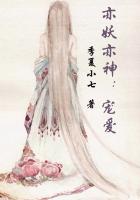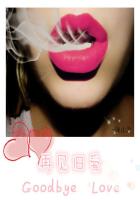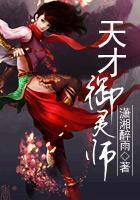(三)
这件事情办得实在漂亮,不仅显示中国人的现代眼光,也确确实实达到了引渡重犯的目的。
按说,这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可问题是,那不懂外交的瑞麟觉得这件事办得太容易,显示不出他的功劳来。于是,到处宣扬侯玉山是自己率兵攻打擒拿过来的。
郭嵩焘极力劝阻瑞麟这种言行,告诫他如此宣传将引起外交纠纷。果然,英国人对瑞麟的论调表现出极度的愤怒,多次发来公文进行谴责。
瑞麟和郭嵩焘政见本来不合,经这一事,矛盾愈加恶化。加之有左宗棠等人在背后使坏,郭嵩焘的政治生涯又一次出现危机。
不久,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交错压迫下,他不得不解职归田,回到故乡执掌城南书院。
面对一片青山绿水,著书立说,排解寂寞心情。
三出使西方更为天下不容
(一)
历史总有它的相似处。
郭嵩焘的再次复出又是在新皇帝上任的时候。这一次朝廷碰上了一件棘手的外交事件,面对这个相当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自然想到了熟悉外交事务的郭嵩焘。
这次的事件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正月,英国人柏郎率领探险队,从上海经贵州进入云南。担任探险队翻译的是英国公使威妥玛派遣的外交工作人员马嘉理。不知怎么回事,这支探险队在云南受到了攻击。马嘉理及一些中国随员被杀害。
事涉人命,当然是一次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不管是当地居民自行组织的,还是政府授意所为,外交人员被打死,地方官最起码也要负领导责任。
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是岑毓英,按理说,他难辞其咎。但舆论并非如此,许多人认为岑毓英干得好,给中国人出了气。
只有郭嵩焘这时保持了清醒的态度。他上书光绪帝,极力弹劾岑毓英,请朝廷罢掉他的职位,以封英国人之口。这样的姿态,在当时来说应该是理性的,也符合通常的外交法则。——结果,却招致骂声一片。
民族主义情感的冲动并不能换来外国人的同情,趁着马嘉理死去的“良机”,英国公使威妥玛不仅使出种种手段,威逼清廷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而且还要求清廷派出外交专使到英国去当面谢罪。
这个时候,外交人才几近于零的清廷,不得不派出熟悉夷务的郭嵩焘。这一下,朝野上下喧哗沸腾起来。“汉奸”、“贰臣”这些大帽子,一顶顶落到郭嵩焘头上。有人甚至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岑毓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郭嵩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舆论对郭嵩焘挥出了讽刺、辱骂的大棒。茫茫人海,知音在哪里呢?斯人寂寞矣!
(二)
或许是舆论对当局产生了一些影响,清廷派给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是极为保守顽固的刘锡鸿。是监视呢,还是牵制?反正,这一趟出使,刘锡鸿所起的正面作用近乎没有,负作用却昭然在世。
《清史稿郭嵩焘列传》里只用了寥寥数语,“既莅英,锡鸿为副使,益事事齮龁之,嵩焘不能堪,乞病归”,这段文字虽短,但可看出刘锡鸿是何等龌龊、何等小人,郭嵩焘之难受、之受掣肘可想而知。
年老体衰的郭嵩焘就这样踏上了出使异国的征途。
这是一次从感官到心灵都十分惊艳的旅程。西洋的风物、文化、体制等都使这位长期生长在中国官场和学术中间的传统士大夫深感“震惊”,大开眼界。
也许是觉得这些中国未曾有的事物大家都应该分享,他每天详细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并辑录为《使西纪程》一书,呈总理衙门刊刻。
他万万没有想到,分享到这些见闻的朝廷官员并没有如他一样喜悦。反之,他在书中对西方文明的称赞,极大地激怒了那些“天朝中心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哪会有比大清帝国更美好的呢?如此赞美外国,实在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一时,竟激起了官场公愤,强烈要求将郭嵩焘革职查办。
(三)
最令人恼火的,是他的副使刘锡鸿,在郭嵩焘遭遇严酷舆论围剿之际,他跳了出来,使出釜底抽薪的招数,向朝廷弹劾了郭嵩焘的三大罪状: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现在看看,这些罪名都十分幼稚可笑。郭嵩焘所做的,不过是正常外交礼节中该当之事,却被刘锡鸿等一帮“天朝”斗士上纲上线,将其判定为清廷的异类。刘氏本人更是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事小罪大。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事件中的一贯特色。罗织政敌罪名的时候,国人常用“莫须有”代之,何况郭嵩焘还有一些不算罪名的“把柄”让人抓住呢?他的《使西纪程》不就是最大的罪证吗?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位被英国人称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士大夫不得不辞去大使的职务,凄然回乡。
叫人痛心的是,那些守旧的家乡父老也无法理解他,送给他的,只是“汉奸”的大帽和无尽的唾骂。
四寂寞凄凉的结局
郭嵩焘作为一个独异的个体,一生都不太顺利。
他只是一个人,和他战斗的,却是一种保守文化。或许,他醒得太早了。这就注定他要独自走在黎明前的寂寞里。
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病卒。王先谦、李鸿章等人启奏朝廷,希望朝廷对郭嵩焘的贡献给予表彰和肯定,但朝廷答复:“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事隔多年之后,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的开篇指出:“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郭嵩焘)、湘乡曾劼刚侍郎(曾纪泽),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同为湖南人的谭嗣同对湖南人的表现是痛心的。湖南好不容易出了郭嵩焘这么几个精通洋务的人,湖南人却纠结起来大加诋毁,怎么不叫人寒心呢?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将郭嵩焘与魏源、曾纪泽并称为“中国首讲西学者”。
中国维新变法以后的历史进程,都应验了郭嵩焘的先见和预言。——只是,他再也看不到了。
左右为难张之洞
刚开始的时候,张之洞是以清流猛将的身份出现的。
他和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一起被称为“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清史稿》)。
清流知识分子,既是官员,也是文人。由于长期战斗在一起,加上志趣和爱好相投,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张之洞既然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自然会有这个群体的集体特征,比如,他喜欢和文友来往,喜欢写诗,喜欢研究学问。
情势的变化,常常令人不知所措。
随着时光的转换,张之洞当上了封疆大吏。在这个位子上,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服从,服从最高权力者慈禧的一切安排。
在清流失去其利用价值之后,慈禧对张佩纶等人颇不喜欢。同时,因戊戌之变,慈禧对变法也恨之入骨。而张之洞,内心深处,不仅喜欢和清流旧友交往,对变法也持较为开明的态度。怎么办呢?要保住官位,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服从于慈禧。
这就造成了他的“两难”。
在“会友”上左右为难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昔日文友张佩纶恰在南京。
时过境迁,职换位移。这时的张佩纶,已经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议论风生的样子了。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佩纶被委以船政大臣,一介书生应对战争风云,结果福建水师覆灭,马尾船厂被毁,受到朝廷严厉惩处。
这样一个老朋友,住在自己地盘上,张之洞犯难了。和张佩纶来往吧,他是上头记恨的人,只怕慈禧不高兴;不和张佩纶来往吧,终究有故人之谊。
如何是好呢?张之洞想了一个馊主意,就是发议论、说风凉话,想让张佩纶听到这些言论后,自觉移居苏州,免得两人尴尬。
哪知,张佩纶听到这些议论后大怒:“我一个失职闲居的人,难道连南京也不许我住了吗?”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张佩纶并没有搬走。据说,张之洞还悄悄去看了他,两人相见,抱头痛哭。
权力阴影笼罩下的友情,一面要屈从上级,一面要维护旧谊,除了痛哭,他们又还能做什么呢?
在“学王安石”上左右为难
张之洞对王安石,是打心眼里喜欢的。
他的诗歌,学的就是王安石。他自己有一首诗道:“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吊袁爽秋》)点明了自己喜欢北宋的诗歌,且推崇双井(黄庭坚)、半山(王安石)。
然而,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却再三标举自己和王安石不是一路人,他在《学术》一诗的注中写道:“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语气之间,好像推崇龚自珍、王安石这些人,是世风日下的表现,否定之意甚为明了。不仅如此,他还写下《非荆公》一诗,直接对王安石表示批评。梁启超当时写了一本《大政治家王安石》,倡扬王安石变法的功绩。张之洞见了,极力诋毁这本书,对其进行批驳。
这种种表现,是不是说明张之洞对王安石的态度真的发生了变化呢?非也!论者黄秋岳在研究过张之洞的诗后,指出“今观其诗,晚年诸绝句实宗北宋,尤学半山(王安石),岂可讳乎?”
这说明,在隐秘的内心里,张之洞不但没有否定王安石,甚至到老都在学王安石。
那他为什么要如此呢?很简单,为了逢迎慈禧。王安石以“变法”闻名于世。慈禧最恨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倡言“变法”之徒。在这种情状下,张之洞就须和以变法出名的王安石撇清关系,彰显自己的立场,以获得慈禧的信任。
左右为难,实质上就是选择之难。
可以看到,张之洞在仕宦和文学等的选择上,把天平偏向了仕宦一边,但内心里却又与文学等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八面玲珑,方能左右逢源。
做到这一点,需有高超的心理调节能力。张之洞是有这种能力的。
在此,也别笑话张之洞,试想想,要是我们处在那样的情境下,又有几人能把自己的爱好坚持到底呢?
朝廷亦可成弱势——晚清朝廷与地方关系的一种观察
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
在古代,把皇帝、朝廷比作大腿,把地方官吏比作胳膊,想来也不会失当。因为一般来讲,“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作为皇权象征的朝廷,总比地方官要威严得多。
但这只是以常理度之。
实际上,朝代更迭,权力交互,皇权总有衰落的时候,而地方大员恃宠而骄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东周列国时期,所谓的君主便时常被列国欺凌。汉末时的汉献帝亦曾被曹操软禁,发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著名事件。唐代宗时,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陕州,大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怕踏破长安城”。面对地方大员的这种骄焰,代宗只能默默含忍。
清代官员似乎并没有周智光这般猖狂,但至“太平天国”兴起,地方官员在征讨中权力逐渐扩张,对于朝廷亦就变得渐次侮慢,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分明在言说着胳膊与大腿关系的倒置。
得宠太监安得海的被杀颇富戏剧性。
这一轰动性事件,既显示了地方官员的权谋,更表现了他们的强悍和朝廷对他们的无奈。
同治八年(1869),太平天国燃起的硝烟刚刚散尽,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把奉命南下过境山东的太监安德海抓起来杀掉了。以常理论之,安德海奉朝廷之命,属于钦差大臣,在地方应享受隆重的接待。但丁宝桢明白无误地表示:“吾闻安德海将往广东,必过境山东,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及至安德海真的成行,丁宝桢一面向朝廷请旨,一面派人封堵。
而不明形势的安德海自恃钦差身份,完全不知末日来临,反而詈骂追杀者:“我奉皇太后(慈禧)之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丁宝桢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在未知请来的朝旨内容的情况下,“欲先论杀之”。结果被一地方官极力劝止,后朝旨到,“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
从以上的记叙看,这一事件相当曲折回环、惊心动魄。安德海和丁宝桢两人,一个是朝廷代表,一个是地方大员,三番五次地在“死”与“活”中穿梭,但终归的结果是,――安德海死了,并且死得很惨。
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在地方官员权力日炽的现状下,即使是钦差的“命”,朝廷也难以保住。――朝廷的弱势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在这一事情上,值得玩味的是朝廷和地方官员各自不同的心态。
听说丁宝桢杀了安德海,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是兴奋莫名,连声称羡:“稚璜(丁宝桢)成名矣!”
当时的地方官领袖曾国藩更是激动异常,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有关史料引自杨国强《百年嬗蜕》)
地方官们意气风发的语句,展示了他们对朝廷的态度。而朝廷的做法是什么呢?廷议给安德海所列的罪名是“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
事实上,安德海是奉皇太后(慈禧)的命令去广东办事情的,压根儿就没有“擅出”。朝廷之所以给他罗织这个罪名,实则是惧于地方官员的“威力”,不得不从之罢了。
地方官员“威力”的积累和朝廷势力的衰弱,一般是由于战争(如太平天国)的原因。
当战争发生,朝廷无力对抗,地方官员乘势而起,在维护朝廷命运的同时,自己也增长了力量。
而朝廷要倚重地方官员对付反抗者,不得不对其依赖顺从,时光一长,这种态势便成为固定模式,没有办法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