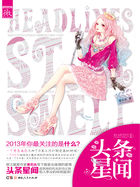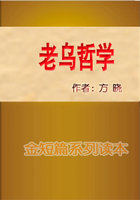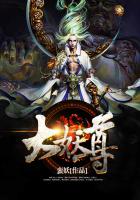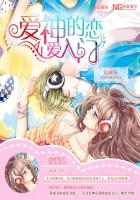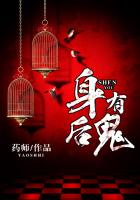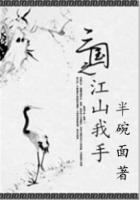赵俊林被关进了一个窄小的屋子里,里面潮湿,充满了霉味,赵俊林依着墙蹲了下来。过了好长时间,门又被打开了,一个士兵背着枪,把他带到一间大屋里,迎面的大桌子背后,坐在一位戴着军帽,穿着制服的军官,正在喝茶。旁边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年轻人,面前放着纸和笔,是在准备做记录的。赵俊林知道这是来审问他了。
士兵把他按坐在一张木椅子上,然后背着枪站在一边,双脚并拢地说:“报告长官,共军俘虏押到。”
长官拖着腔调问赵俊林:“你叫啥名字?”
赵俊林说:“王磊。”赵俊林报了一个假名,以便掩护自己。
“你是干啥的?”
“在八斗做生意的。”八斗是一个集镇。
“做生意?那怎么和共产党在一起了。”
“长官,现在不太平,原不准备出来的,但我母亲生病了,多次来信催我回家看看,说临终前要看我一眼,好闭目。我就咬着牙出来了,路上遇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战士和我老乡,就与他们一起同行了。”赵俊林看着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官,长官抬着头望着他。赵俊林胸有成竹地说,这都是他在路上想好了的。
“把他的鞋子脱下来我看看。”长官阴阳怪气地说。
旁边的士兵走过来,弯下腰,把赵俊林脚上的鞋子脱了下来。赵俊林知道,这是国民党审查的一种方法,因为共产党军队长期走路,脚上没有泡的,只有厚厚的茧,而赵俊林的脚上却有几个黄豆粒大小的血泡。长官走过来低下头看了一下,没有作声,又回到了座位上去了。
“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怎么穿着共军的衣服?”长官沉默了一会又问。
“天冷了,游击队里的小老乡给了我一件衣服挡挡寒,我就穿在了身上。”
“你回家怎么不走直路,绕着弯子走?”长官站在地图前看了好大一会,然后转过身来问。
“走直路,怕土匪,所以跟着游击队走,觉得安全。”
赵俊林回答的都在情理之中,长官纳闷起来,难道眼前这位真的是商人。
审问草草地结束了。
长官站起来,对士兵说:“把他带走。”
赵俊林被带了回去,松了绑。过了两天,士兵来把他带到一个大屋里,这里坐满了人,主席台上,有一个军官在训话,意思是说,前线正在和共匪作战,人员短缺,这些青年人,都将分到部队里去了,将来就是一名军人了,要为党国效劳。
训话后,开始学习军队纪律。
中间休息时,赵俊林观察了一下,这里约有百十人,年龄不整齐,有的年龄大些,沉默寡言,唉声叹气,有几张年轻的面孔显得很活跃,对军人的生活充满了新奇。还有几张老油条的面孔,嬉皮笑脸的,赵俊林还看到几张娃娃脸,他们穿着单薄,瘦弱的身子,说话的嗓音还处在青春变声期。
晚上,赵俊林被安排睡到大通铺里。
几天的学习,赵俊林摸清楚,这些人,有不少是国民党拉夫来的,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土匪,被俘虏后,自愿加入国民党军的,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
三天后的早晨,这批人被押着上了几辆军用卡车,卡车是布篷子的,没有一个窗户,卡车颠簸着上路了,开了不久,就有人开始晕车呕吐了,空气里充满了一股难闻的酸味。车子是晚上停下来的,大家从车子上疲惫地下来,在蒙胧的光线中,赵俊林看到一片平房,来来往往都是穿着制服的军人身影,门口站着岗。赵俊林判断这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地。
这批人拉到这里后,发下部队的制服和帽子,开始了正规的学习。每天一大早起来跑步,做操。吃过早饭后,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这天吃过早饭,大家来到操场上排好队,教练把赵俊林从队列中叫了出来,然后,让他跟一个通信兵走了。
赵俊林走在路上就纳闷,这是让他去哪里?
士兵在前面走,赵俊林跟在后面,他们来到一排红砖瓦房前,士兵推开门,立正,报告:“报造连长,你要找的人带来了。”
连长穿着皮靴,站在墙上的地图前看,他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赵俊林,又继续看地图。赵俊林坐在椅子上,望着这个连长,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过了一会儿,连长才来到赵俊林跟前,对他说:“我们从转过来的信息中,知道你是一个商人,有文化,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军训了,去和司务长把厨房搞好。”
赵俊林这才放下心来。
士兵把赵俊林带到厨房,介绍给了司务长。司条长是一个胖子,身上围着一个大围裙,肥胖的脸嘟着,没有一丝笑容,埋头在热气腾腾中忙碌着。
晚上,赵俊林就搬到橱房来住了,食堂旁边有几间平房,一间是储存食品的,司务长和赵俊林各住一间。
第二天,赵俊林还在熟睡中,司务长就喊赵俊林起床了。司务长对他说:“我们要起早去买菜,去晚了,买不到好菜了。”
营地里静悄悄的,只有门岗亮着灯,司务长和站岗的哨兵打了招呼,出了院门,外面就是空旷的田地了,两个人在黑暗中走着,走了一里多路,就到了一个镇子上。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走,街道黑洞洞的,两边的人家都关着门,有一两户卖早点的店铺,开了门在生炉子了。走过街道,一拐弯,进了一处大棚里,这里灯火通明,人影幢幢,买卖的呦喊声此伏彼此。
司务长与这里的许多摊铺都熟悉,他一来,许多摊主就主动招呼他,司务长一边应着,一边往前走,待一个市场看完了,司务长心中也有了数,他蹲在摊子前,看菜的成色,然后讨价还价。
司务长买好菜后,赵俊林按照要求给人家结账。
买完菜,天已大亮了,两人往回走,还没到营地,远远的就听见里面的士兵们出操的口号声了。
两人忙过早饭后,就是一段长长的时间了,赵俊林开始算账,司务长站在一边和他对账单。
司务长坐在赵俊林的对面,看着赵俊林把算盘珠子拔拉得啪啪响,佩服不得了,他说:“我们部队里的兵部是拉壮丁拉来的,没什么文化。我也是一个大老粗,这次碰到你这个文化人了,了不起。”
赵俊林说:“我们做生意的,不会这个还行。你把菜烧得那样好,我也不会哩。”
司务长说:“唉,你别看这些兵娃子们,要给他们吃好,他们上了战场就不一定能回来了。这些年,我见的多了。”
几天下来,两人熟悉起来,说的话也多了起来,赵俊林感到这个司务长还是挺善良的。
一次, 司务长问赵俊林:“你是一个做生意的,怎么跑到这个鸟军营里来了。”
赵俊林就按照事先计划的经过,给司务长说了。司务长听了,唏嘘不已。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出门真不容易,那你在这里,城里的生意怎么办?”
赵俊林叹了一口气说:“这年头还想啥生意呢,能把命保住就行了。我娘还不知道可在世了哩,老婆孩子还不知道我的死活哩。”
司务长也同情地说:“等世道太平了,我们都回家去。我也不想在这个鸟部队里干了,我干够了。”
赵俊林说:“现在你是大哥,我们回去了,我还喊你大哥。”
两人的感情渐渐深厚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司务长的口里,赵俊林知道,这儿离宁州市很近了,只隔一条江。赵俊林想起皖北特委在宁州市活动的消息,他的心里动了一下。
再去菜市场买菜时,赵俊林就对那些渔民关注起来。
他终于物色了一位老渔民,这位老渔民叫老李,人很憨厚、质朴,脸上满是风里来雨里去留下的刻痕。他打的鱼又大又多。每次司务长买他的鱼,赵俊林都暗暗地给他多算一点,老李也心领神会,对赵俊林充满了感激之情。
有一次,司务长买完鱼,赵俊林趁机与老李搭讪起来。
“老李,你打的鱼怎么又大又多?”
老李拾着渔筐说:“哈,不到大江中间去,哪能打到鱼。”
“到大江中间去打鱼不危险吗?”
“当然危险,经常有小船在江里翻了的,但我家世世代代打鱼的,有经验了。”
“有时间我跟你去江上玩行吗?”
“好,我家住在李老庄,就在江边上。”老李直起腰来。
司务长在前面又买好了菜,喊赵俊林赶快过去付钱,赵俊林走了,但老李说的话,他记住了。
不久,赵俊林生病了,发着高烧,这下子可把司务长急死了,他找到军医,叮嘱一定要尽快把赵俊林的病看好。
司务长每天来给赵俊林送水,看着这个年轻人,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心里很同情。心想,他可不是受罪的人,他这是落难了。
两天后,赵俊林的烧退了,但他的身体很虚弱。司务长精心烧了糖水鸡蛋,补补他的身体。
晚上,两人坐在一起聊天,司务长说:“你这几天发烧,讲了许多胡话,可知道?”
赵俊林心里惊了一下,莫不是暴露了身份?他漠然地说:“我哪知道?”
司务长停了停又说:“你在不停地喊你娘。”
赵俊林心里踏实下来。
司务长说:“我看你这次病得很厉害,现在,你身体好,想不想回家去看看?”
赵俊林说:“想,但走不了。”
司务长回屋去,一会儿拿来一个红本子,对赵俊林说:“这是特别通行证,费了好大的劲,找部队里的人批下来的,准备留着自己回家用的,现在给你吧。”
“给我了,你回家怎么办?”
“我再想办法。”
赵俊林看着站在眼前这个胖胖的老大哥,眼睛里充满了感激。
司务长说:“你明天吃过饭走,那个时候部队管理松些。”
“不会牵连你吧。”
司务长沉默了半响,然后坚定地说:“不知道,但我在这儿人熟,我会想办法的。”
第二天吃过饭,赵俊林拿着特别通行证大摇大摆地出了门,然后,就去李老庄找鱼民老李去了。
老李在家补鱼网,一张鱼网,高高地挂在树杈间,展开来,像一幅巨大的翅膀,老李坐在网下,梭子飞快地在鱼网的破洞中穿来穿去。
赵俊林喊了一声老李,老李直起身来,看到是赵俊林来了,很高兴,忙停下手中的活,把他让进屋内,赵俊林就把自己想渡江去宁州市的想法告诉了他。
老李想了想,说:“不好走,江上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的巡逻艇。”
赵俊林看到老李为难的样子,感到很失望。但他在心里码算过了,老李是最佳人选,如果老李不愿意去,就找不到人了。赵俊林诚恳地说:“你要是不愿去,就算了,我另找人吧。”
老李挠了挠头皮,感到拒绝他不好意思,说:“晚上,我们试试看吧,如果不行再撤回来。”
听说老李愿意,赵俊林放下心来。
傍晚,老李从家里拿了一盒土香,夹在腋下,要带赵俊林去土地庙烧香。
赵俊林笑笑说:“烧香干吗?”
老李认真地说:“我们夜里渡江,要请菩萨保佑的,这是我们鱼家的风俗,下江都要去烧香的。”
为了尊重鱼民的习俗,赵俊林跟着老李去了。
土地庙在江边的一处高坡上,一个窄小简陋的小瓦房里,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个木雕的牌位。老李把香点燃了,放到台子上,然后,双手合十,默默地念了几句,跪到地上磕了三个头。赵俊林也学着他的样做了。烧完香,两人来到江边,江水宽泛地流着,轻轻地拍着江岸。
老李说:“今晚江上风浪会很大的。”
赵俊林感觉了一下,只有细细的风从脸上轻轻的拂过,说:“现在不是没有风吗?”
老李说:“江上无风三尺浪,到了江中心风就大了,我们打了一辈子的鱼,对江的脾气熟透了。”
赵俊林信服地点了点头。
晚上,老李让老伴烧了几个好吃的菜,和赵俊林吃得饱饱的,天黑透了的时候,老李带着赵俊林来到江边,把小木船解开,开始渡江。
江面上黑糊的一片,只看到船舷边的水,浑浊的,静静的流淌,老李划着桨发出轻轻的哗哗声。
赵俊林坐在船舱里,江面上的风吹过来,身上冷得一阵发紧,波涛果然大了起来,他担心老李会不会迷了方向。
赵俊林说:“老李,这是不是在向对岸划?”
老李笑着说:“你放心,我划了一辈子船,眼闭着也知道划向哪里?”
过了一会,远处忽然划过一道光柱,江面上响起了机器的隆隆声。老李说:“不好了,巡逻艇来了。”
赵俊林紧张地问:“怎么办?要不要往回撤。”
老李停下桨,说:“不能往回走,已经到江中心了,你坐着不要动,我们的船小,江面大,我们躲躲看。”
巡逻艇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光柱也越来越强烈,借着射灯的光柱可以看到前面江水的汹涌。
一个浪头打来,小船随着波涛沉下了谷底,然后又被浪头托举起来。两人伏下去,老李稳着桨,尽量把船顺着波浪的谷底躲避。小船有时在波涛里,有时在漩涡里,像一片树叶摇晃,颠簸,浪花拍打过来,两个人的身上很快就潮湿了。
巡逻艇上的隆隆声越来越清晰了,灯光从远处划着轨迹过来了,眼看就要打到小船上,这时一个波涛涌起,把小船要掀翻了一样,掀到了一侧,灯光从波涛的脊背上划过,小船躲了过去。巡逻艇的灯光移到别处乱晃了一阵子,过去了。
两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赵俊林紧按着心跳,说:“老李哎,可把我吓死了。”
老李拿稳了桨,说:“菩萨保佑的,菩萨灵哩。”
船到了江心,船身颠簸得更厉害起来。江涛拍打着船身,发出哐哐的声音。赵俊林紧紧地抓着船邦,老李说,这是过大溜了,不要动,过去就行了。
老李用力的划了起来,过了一会船终于平稳下来,离江岸也不远了。
上到岸上,天已朦朦亮了。和老李告别后,赵俊林走了半天的路,来到一个小镇上,乘了火车,去了宁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