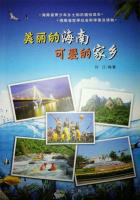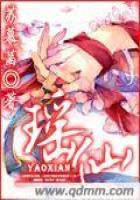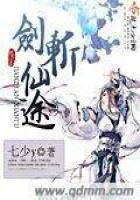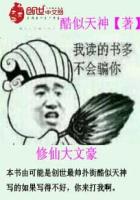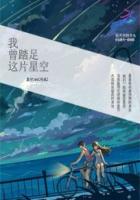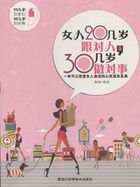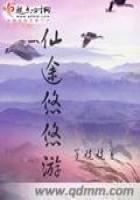“找寻”保尔及其他
刘亚丁
找寻保尔·柯察金
我很喜欢刘小枫的《怀念冬妮娅》,因为它将我们在“史无前例”中偷偷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复杂心理写得惟妙惟肖。在禁欲年代里这部小说和《牛虻》对我们进行了爱和美的启蒙,也进行了革命崇高感和神秘感的教育。正像很多老同志一样,我也很关注保尔·柯察金和夏伯阳在故乡的“命运”。因此利用到莫斯科大学做高访的机会,我开始了对保尔·柯察金的找寻。
我问大学生冬妮娅·卡萨特金娜:“你对有与你同名的女主人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看?”
她说:“在读中学的时候,我读过这本小说。我印象并不深,只觉得是很多类似的小说中的一本。我知道,我们的父母和爷爷辈很喜欢这本书。但是我读完了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特别打动我的东西。”
我也向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学生萨沙问过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一本什么小说,写什么的?”
我继续问:“萨沙,在中学或大学里难道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俄罗斯文学课的老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物、这本书?”我还不死心,因为我知道在俄国中学的“俄罗斯文学”课实际上是一门非常详尽的文学史课。
从表情可以看出,萨沙的脑海“奔腾”了好一阵,可是终究没有搜索到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任何信息。
后来我了解到,在现在的中学的“俄罗斯文学”课中已经没有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作家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了。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也将这部作品略掉了。
其实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消解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在进行了。我在自己的《苏联文学沉思录》(1996)中指出了这样的事实:
在《癌病房》(1963—1967)中索尔仁尼琴认为,最能体现意识形态神话的作品是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试图通过对这部影响深远的作品的主人公的价值观念的戏拟,将保尔·柯察金的悲壮化为喜剧,借以肯定他自己认同的生存哲学。
《癌病房》第一个提到保尔·柯察金的是新潮少女阿霞。这是一个中学生,时装、跳舞、享乐、性交是她的全部生活乐趣。她谈起老师出的作文题《人为什么活着》,她说老师提示他们要谈谈“你对保尔·柯察金的功勋怎么看,对马特洛索夫的功勋抱什么态度”。阿霞对此是颇为不屑的。她向病友说起她和她的同学的态度:“什么态度?那就是问,你自己会不会这样做。我们都写上:我们也会这样做。都快毕业考试了,何必把关系搞坏?”叙述者暗示读者:保尔·柯察金的崇高形象在阿霞们的心中坍塌了,英雄的“神话”就这样消失了。
第二个提到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的是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在同护士卓娅谈论该不该用激素疗法治他的肿瘤时说:“你将来是不是也会这样做?学校里是这样教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对不对?那就是说,该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不放,是吗?”这里打单引号的那句话是保尔·柯察金的闪烁着生命光彩的名言。叙述者通过科斯托格洛托夫这句话是想暗示:一代代苏联人不是自发地受到保尔·柯察金的形象的鼓舞,而是在学校强迫接受的(阿霞的话说得更明白)。略掉了保尔·柯察金那段话的更重要的部分,并且加上科斯托格洛夫的引伸,就完全歪曲了原义:本来是舍生取义的英雄的浩叹,变成了苟且偷生的庸人的哀鸣。我们可以责备索尔仁尼琴反讽崇高,但他确实敏感地点出了当年苏联人理想主义价值观失落的残酷现实。他的洞察力得到了证实。
在2000年和2001年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我好不容易重新找到了“保尔·柯察金”。一本是П.尼古拉耶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作家辞典》,书中有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词条,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该书写道:
在严格的真实事件与意识形态的强制、鲜活的个人体验与革命者的道德规范的整齐划一、文献的叙述与理解了自己的英雄时代的艺术家的想象之间的难以察觉的“缝隙”中创作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该书还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夏伯阳、斯达汉诺夫等一起成了罩着“非宗教神圣”灵光圈的形象。词条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保尔·柯察金热潮产生的过程。
《文学问题》2001年7、8月合刊上发表了伊·孔达科夫的《我们苏联的“一切”: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文本》。该文详尽分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认为前者“复兴‘新东正教’”,后者“宣扬‘新专制主义’”,“两者都寄希望于多灾多难的人民,他们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创造,尽管历经磨难,遭受损失”。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因此它们都是“苏联”的。“吾与点也”,在某些问题上我赞同孔达可夫的看法。因为在《苏联文学沉思录》中,我曾谈到保尔·柯察金式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俄罗斯圣徒阿瓦昆《生平自述》的内在联系,孔氏也谈到了保尔·柯察金的宗教情怀。
我还发现,在如今的俄罗斯夏伯阳也在蒸发。富尔曼诺夫塑造传奇英雄的小说《夏伯阳》在20世纪90年代成了小说中的小说,年轻作家维·佩列文的长篇小说《夏伯阳与普斯塔托》(2001)就反讽了《夏伯阳》。小说是以莫斯科的颓废诗人普斯塔托作为叙述者写的,他即“我”成了夏伯阳的助手。在专列上的司令部里夏伯阳请普斯塔托喝酒,普斯塔托说出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我可以完全相信自己,”我说,“但我不能完全相信您。”
“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让您难为情?”
“我可以直言相告吗?”
“当然哪,我和安娜都很欣赏直率。”
“我很难相信您真是一位红军指挥员。”
夏伯阳扬起了左眉。
“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真诚地,但我明显感到痛苦地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我说,“这一切很像是一场假面舞会。”
在另一个场面里,普斯塔托还怀疑红军与白卫军究竟有没有实质性区别。
历史,在这里被虚无主义化了。
卫国战争的历史也在被改写。谢尔盖·卡拉-穆尔扎的《战胜苏联十年祭:被战胜者的总结》(《我们同时代人》2001年第10期)指出:“众所周知,伟大卫国战争的意义广泛的象征对于我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开始对它是出语不恭,然后在整整十年里毁坏这个象征几乎成了正式的国家计划,冒出了一系列美化叛变、为其洗刷罪名的书和节目。背叛是相对的,形成了叛徒文学的体裁,还有大量学术著作。众所周知的、经过大量文献证明了的事件,被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借助德国人的档案和回忆录重新叙述——而且常常不指出祖国的相应史料。在期刊上发表早已被德国人否认了的谎言(比如根据戈倍尔的《斯大林格勒来信》草草拼凑出来的货色)。这些庞大的、得到大量资助的计划完整地从我们的历史集体记忆中排挤走了卫国战争的形象。在这里应该强调,在这场运动中,完全没有‘西方人’的力量。因为志愿参加者已经十分踊跃,他们的作用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合力。”
保尔·柯察金被淡忘了,夏伯阳被解构了,卫国战争的形象在被摧毁,其实我们怀着激动和温馨忆起的“苏联”的一切都在蒸发(尽管有人竭力要挽回它,比如上面说到的孔达科夫和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多次到中国演出的俄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表演的节目在俄罗斯是找不到舞台的,“喀秋莎”的歌声除了“人民电台”而外,在哪里也听不到——可那是一间小电台,到了晚上该频率就转给了一家宗教电台。我想找到一张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五月的原野》之类歌曲的C,跑遍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音像商店,终究无功而返。在各大书店里,只有一张苏德战争爆发时艺术家创作的英雄母亲的宣传画还能令人联想起“苏联”;只有在庆祝十月革命的游行的老人斑驳的银发上,在他们佩带的琳琅的勋章上,还能依稀辨出几分“苏联”。
我的浓浓的“苏联情结”在2001年的俄罗斯已经无所寄托。
“保尔·柯察金”渐行渐远,“苏联”也日益疏淡,但是那个国家,那个时代,连同其成功和失误是不会被遗忘的。
“梅希金公爵”的秘密
2001年秋天,一次我外出旅行,从一个小站上火车,因为是预定好包厢票的,自然就免了找座位这档子事——其实现在坐俄罗斯的长途火车,早已不同于《日瓦戈医生》写的内战年代,那时大家纷纷逃难,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往车上挤。现在假如你没买到普卧和包厢的票(长途一般没有硬座),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你也休想上火车。
上了车后,我找到了列车员,一位瘦瘦的中年妇女。她看了我的车票后,迟疑了片刻,说:“那您就到2号包厢的5号位吧,是个下铺。”
我到了2号包厢,拉开门,旅行包一放,坐了下来。只见对面下铺躺着一位男士,我同他打招呼,他坐起来,很有礼貌地向我还礼。好一个美男子,就是现在新派人物说的,帅呆了!
他30岁上下,面庞白净,刮得很干净的下巴,两腮泛着青色,两耳前的鬓脚修得笔直,唇须也剪得很有形状。脸的轮廓线条既分明又硬朗,透露出阳刚之气。穿着合身、干净、几乎没有皱纹的牛仔衫和牛仔裤。我的第一判断是:他是一位职业演员。
我开始欣赏窗外流动的俄罗斯田园风光,秋收后的田野在没有尘埃的阳光下亮出了它的本色,黑黝黝的,宽阔得总也没有尽头。突然闪出两行高大挺直的杨树,为这黑色基调的大画镶上了绿色的框。杨树一闪而过,一块没有边际的庄稼地,仔细一看,是耷拉着头的向日葵,在等待农人去收获。又是黑土地涌向眼前,一条印着深深车辙的小路,向远方起伏蜿蜒而去,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令人对俄罗斯的辽阔产生遐想。走在那路上,难免不想起俄罗斯谚语:“Подитуда,незнаюгуда,пРинесито,незнаючто”——“你到那我不知道的地方去,带着我不知道的东西来。”俄罗斯人在这空阔浩大的土地上酝酿着幻想、吟咏着诗、产生着艺术和哲学……
对面的那位美男子将我的视线吸引回了车内,他在翻动着一张小报,动作显得很有派头。我开始悬想:假如他真是演员(他一定会是电影演员)的话,他适合演什么角色呢?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高贵的出身,高傲的派头,乖戾的性格,这位可以演得惟妙惟肖。
我似乎听到他发出了轻微的抽泣声,我抬头看他,他也抬起头来,他的蓝得像浅海的眼睛好像在看我,但分明不在看,而是透过包厢壁遥望远方。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梦幻般的东西,也许患夜游症的人也有这样的视而不见、充满梦幻的眼光。
正在此时,有人拉开包厢门,一个比他更年轻点的人进来,坐到他的身边,轻声吩咐他躺下。他好像没有听到来人的话,依然在遥望着、幻想着。
我突然想起了,对,他更适合演梅希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的心爱的主人公,《白痴》中唯一的理想人物。这位男子也有梅希金公爵的英俊,有他的高贵气度,更有他那种常人不可能有的梦幻般的眼神。
这时第二个青年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一瓶矿泉水,让“梅希金公爵”喝。他接过瓶子,打开盖子喝了一口,突然他喉咙里喷射状呕吐出那口水。他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拉开包厢门冲了出去。
“梅希金公爵”的同伴一脸尴尬,向我解释说,他昨天感冒了,所以坐车很有些不适。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我发现他白净的脸变得更苍白了,病态的、不正常的苍白。同伴让他躺下,他顺从地躺下。
我转过头望着窗外,看着那黑黝黝的土地,不由得想起了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一句名言:“走了好几百俄里,好像仍在同一个地方。”
此时有人敲门,他的同伴拉开包厢门,是一位富态的俄罗斯老太太。她交给同伴一包袋泡红茶,说:“你给他用开水沏上,少加点水,浓浓地,让他趁热喝下,感冒就会好的。”然后拉上门走了。同伴将红茶的纸袋放进茶缸里,去锅炉冲了开水,凉了一会给“梅希金公爵”喝。他刚喝了两口,又做要呕吐状,他再次冲到走廊去了。他到底怎么了,我很纳闷。
已是中午时分,一阵困倦袭来,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低声在喊:“瓦洛佳,瓦洛佳!”
我眯缝着眼睛瞟了一眼,见“梅希金公爵”背朝我躺着,同伴坐在他身旁,以手抚摩他的左肩。我不明就里,只好继续装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再相机行事。
“瓦洛佳,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不再吸毒了,怎么忘了……”
这下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一瘾君子。
同伴还在不停地低声规劝他。过了一会,传来瓦洛佳的呜咽声,声音越来越大,我又眯缝着眼偷瞧,只见他浑身战栗,四肢抽搐。此系是非之地,不能再呆下去。我立刻站起来,背上旅行包,走出了包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找到列车员,对她说我不愿意呆在那个包厢里,请她给我换一个地方。她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能暴露别人的隐私,所以只是说,什么都没发生,只是不愿意呆在那里。列车员见问不出缘由,就请我等一等,现在全部满员,只有等晚上6点到一个站时才能空出一个铺位。
我就只好在走廊的边凳上坐下。刚坐下一会,只见列车员到2号包厢去了。我心里觉得不安,就像莱蒙托夫《塔曼》中写的毕巧林一样,本来是城防司令分派他到一个地方去过夜,不料他却无端卷进走私犯的老窝里。列车员让我到2号包厢去,我却在无意中窥视了别人的隐私。虽然我什么也没说,但毕竟因为我要求换包厢,引起了列车员对瓦洛佳的注意。
列车员出来后,就离开了这个车厢。过了一会,她同另一位高大健壮的妇女走进车厢,去了2号包厢。我估计那妇女是列车长。他们过了一阵才从那里出来。
他们走了后,瓦洛佳的同伴拿着杯子出来。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对不起,打搅您了。他病了,一会儿到站时,有医生上车来给他检查。”我也对他说,我对列车员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求换一个包厢,请他原谅。他如此通情达理,我多少松了口气。
后来到站后,我进了另一个包厢,在那里看到了送茶叶的那位老太太,原来她也是昨天晚上从2号包厢里出来,换到这里来的。她一连说了几句:“那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没有附和她。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列车员在让我进2号包厢之前迟疑了片刻。同时我的负疚感也略为减轻了一些,因为引起列车员注意2号包厢的不止我一人。
后来听同包厢的人说,有医生进了2号包厢,与医生一起去的还有一个警察,让病人签字后才让他们下了火车。
第二天,大家安全到达莫斯科。我看着瓦洛佳和他的同伴下车离去,我才下车。
据说直觉联想是一种重要的认识方式,梅希金公爵与瓦洛佳的内在联系有一点:他癫痫病发作起来与我在2号包厢窥视到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莫斯科出刊的《劳动报》2001年9月8日报道:近10年来俄罗斯处于嗜毒病状的人增加了11倍,成年吸毒者增加了8倍,少年吸毒者增加了18倍。
我所听到的“中国”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很关心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利用这次到莫斯科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在与俄罗斯朋友交往当中,经常主动提到中国这个话题,好听听各方面人士的看法。
我的朋友、作家瓦连京·奥西波夫对我说:“戈尔巴乔夫简直是个傻瓜,他搞改革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中国的经验是很成功的。”
我对他说:“当时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兄弟,老大哥怎么会向小兄弟学习呢?”
在顿河边的哥萨克镇,米佳老爹对我说:“中国人口那么多,土地又比较少,我听说山地和沙漠还很多,而他们生活得还比较富裕,这就说明他们用脑子来思考,很勤快。”
1990年5月我第一次到苏联时,著名作家法吉利·伊斯坎德尔也曾对我谈起他对中国的印象:“我本人没有到过中国,我去澳大利亚访问时曾途经香港,看到香港很繁荣,街上有很多人。每当我看到中国的地图,我就会想,中国有这么多人口,他们都很勤劳,我就会联想起蚂蚁兄弟的童话。”
在俄罗斯文化(尽管其中伊斯坎德尔是阿布哈兹人)中,蚂蚁是勤劳、和睦相处的象征。维·古谢夫的《托尔斯泰传记资料》记载,列·托尔斯泰在童年时曾与他的两个哥哥玩过蚂蚁兄弟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演绎着勤劳和睦的生活。
冬妮娅·卡萨特金娜,莫斯科理工大学新闻系的学生,选修的外语是汉语。我问她为什么要学汉语。她说,她学汉语是非常偶然的。一次她到图书馆想借一本日本的小说,图书馆拿错了,给了她一本中国小说——《金瓶梅》。她读了后,很喜欢,就产生了要学汉语的念头。开始她在自己的大学里学汉语,后来他们的汉语老师到中国进修去了,她就到市里的汉语学校学习。她还自费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了半年。
菲利克斯·库兹涅佐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2001年2月10日我应约去他的办公室采访他。刚刚落座,他就非常激动地说:“我刚从中国回来,先在上海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然后又在北京参加了另外一个会。中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上海的那些新的摩天大楼,人民的自信,经济的繁荣。这些使我有充分的理由说,21世纪并不是什么美国人的世纪,而是中国人的世纪。”周游列国的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这番话,不是凭空说出来的。
我同我在莫斯科大学的合作者谈起库兹涅佐夫的这番话,她说:“库兹涅佐夫的话很有分量,很聪明,但不乏外交辞令。”我不服她:我算什么人物,库兹涅佐夫犯得着给我来虚伪的外交辞令吗?
谢尔盖·叶辛,著名作家,高尔基文学院院长。他对笔者说:“我3次到过中国,最后一次到中国是3年前,到了中国的西安,然后到了越南。中国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尤其是她的文化对于世界有巨大的意义。”3年前他在高尔基文学院开办了汉语班,培养翻译中文小说的专门人才。
李福清,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与他算老相识了,1992年,他莅临成都参加“三国文化国际研讨会”,我曾受系主任龚翰雄教授委托邀请他到川大中文系演讲。作为一位汉学家,李福清经常到中国“出差”,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在他家里,喝着他沏的中国绿茶,我请他谈谈对中国的看法。他说:“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59年,到今年——2001年,已经42年了。没有想到中国的发展这么快。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赶不上中国。”
在俄罗斯的一些汉学家也利用各种媒体介绍和宣传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魅力。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М.季塔连科在《亚洲和非洲》杂志2001年第11期上发表长篇论文《中国的现代化,时代的召唤》。他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成就,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材料:
“经济得到稳定高速的增长。从1979年到1997年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世界最高的9.8%。中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增长了20倍——从1978年的3 624亿元,达到2000年的86 000亿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跃居世界第7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之后。而且,按13种传统的、基本的工农业产品(煤、钢、铁、棉布、丝绸、人造纤维、水泥、电视、通讯设备、粮食、棉花、油料(семянРапса)和肉类)产量的指标看,中国均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人口数量极大,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仍然居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水平。”
季塔连科在充分肯定中国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下,客观地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比如下岗问题、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和东西部的差距等问题。他对中国的发展持非常乐观的态度。科学院院士、著名俄中关系权威弗拉季米尔·马斯尼科夫在《俄罗斯与中国·21世纪亚太地区伙伴关系的前景》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成绩。
2001年10月18日,因为普京总统到上海参加环太平洋高峰会晤,体现俄罗斯政府观点的《消息报》在第10版发表了整版专题报道《中国是一条河——俄罗斯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由《消息报》住北京特派记者奥列格·奥夫契尼科夫撰写的。记者在文章末尾写道:“有这样一种看法: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的经验就是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偏见。中国的道路恰恰就是第二条道路——它不过是在与东方世界观传统相联系的现代文明成就影响下的变形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理想不是投身这条河,在这条河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就足够了。”他还谈到了未来的俄中关系。“正在告别舞台的第三代领导人——他们当年曾留学俄罗斯,懂俄语,至少可以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们的继承人是在哈佛和牛津受的教育,在联谊晚会上唱的未必不是《月亮河》。他们必须重新发现俄罗斯——如果我们想保持友谊的话,我们就该帮助他们发现俄罗斯。”当然这篇文章还有另一种调子,这里不去说它。
就我眼界所及,近年来俄罗斯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图书很多,其中有Палея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文集·改革、发展、稳定》(2001),文集收入了从江泽民1989年9月29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到2000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共57篇文章,还附有江泽民的传记和一组照片。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实问题》(2001年),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出的纪念论文集,包括了该所研究人员的论文8篇,既有关于党的“一大”的文章,又有讨论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还涉及“三个代表”的意义等内容。
2000年莫斯科3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马良文的著作《道的黄昏·新时代门前的中国文化》。这是一本文笔优美的学术著作,作者用大量的史料和生动的故事,叙述了17世纪明代的艺术和历史。书的两侧印有当时精美的艺术作品,如国画和人物画等。马良文认为,17世纪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各种艺术发展最完美的时期。
作为“世界遗产”,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儒家学说》两卷,第一卷是《论语》,第二卷是《孟子·荀子》。
《文明·汉学家论中国》,该书囊括了一批汉学家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的精神文化:古代文字,“四书、五经”;宗教和中国人的崇拜物;中国的生活原则;中国的众神;中国人的宗教世界观和神话;中国:她的居民和风俗习惯,等等。
李福清同我谈起两件事情:彼得堡的水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特殊的《论语》译本,每一句话都有5位译者5种译法,译者中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这样的大汉学家。第一次印了10 000本,他以为卖不完,可是很快就卖完了。第二年又印了10 000册。李福清到医院看病,第一诊室的医生同他谈孔夫子,第二个诊断室的医生向他请教《易经》。
我同朋友去参观圣谢尔基三一教堂,教堂前的广场上有很多摆地摊卖纪念品的小贩。一个卖俄罗斯漆器工艺品的男子问我:“是中国人吧?”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对我说:“我非常崇拜孔夫子,他是最聪明的人。”然后给我说起了大致相当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类的话,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在俄罗斯的魅力。
注释:
(1)托尔斯泰童年游戏,寻找埋藏在森林中扎卡斯峡谷旁的小绿棒,据说找到这根刻有秘密的小绿棒就可以使所有的人得到幸福。托尔斯泰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相信有一根小绿棒,上面写着消灭人间一切的罪恶并给人们巨大的幸福的方法,我现在同样地相信这种真理是存在的。”晚年,他还以《小绿棒》(1905)为题写了一篇严肃的哲学论文。托尔斯泰去世后,人们根据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当年寻找小绿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