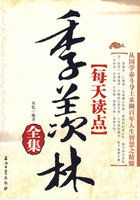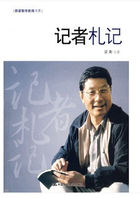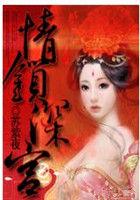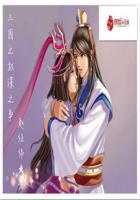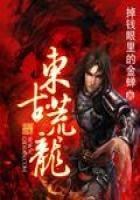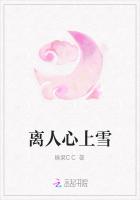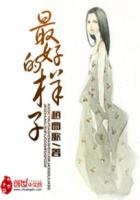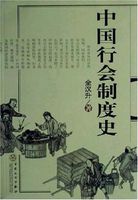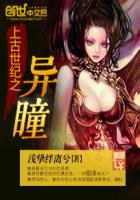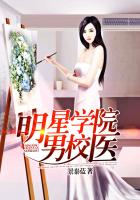我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 爱好不多。有一点点听音乐的兴趣, 但只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听, 不愿意去观看热闹的音乐会, 尤其是那种有所谓大明星出演的大型演唱会, 更是不愿前往。有时候, 碰到热心的朋友, 硬是塞过几张票子来, 也许, 人家拿来的票子, 都是市面上极为难得的热销的“烫手货”, 也不可能打动我的心。碰巧有喜欢此道的人在身边, 我会立即转手相送, 否则, 宁可把票子放进碎纸机, 我也不大会接受对方的邀请。
讲心里话, 我不喜欢看现在那些演员的过分华丽的服饰, 不愿意看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夸张动作。还有, 对台下左右晃动着身子和脑袋、手里拿着吹起来的塑料棒“嘭嘭” 敲个不停的观众们, 总觉得有些变态。我宁愿相信, 如果让他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这种形象, 很可能, 大多数人都会因羞愧而脸红。
当然, 自己心里也明白, 这些想法, 肯定与社会时尚格格不入, 不大合乎潮流。
女儿这样评价我: “爸, 没有你这样儿的, 连歌星的名字都不知道。哼, 你真老了, 已经落伍啦!”
是“落伍” 吗? 就自己心底的感觉, 对女儿的批评, 还真难以接受。他们那个年龄阶段的男男女女, 是很难理解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唉, 有时候, 还真不习惯用这几个字来述说自己目前的状况) 的心境的。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更曾经兴奋和激动过, 而且, 在我们心底涌动过的那些或许是很平凡的经历, 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美妙动人, 更加精彩绝伦!
不相信吗?
说说四十二年前的一段往事, 请朋友们帮忙评判评判。
那是1967年的12月初, 西北风刮得正猛的时节, 我们北京四中的八个同学(吕斌轩、朱景济、赵振华、王林、王致公、黄孝国、陈朝以及在下), 和众多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年一道, 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列车。
这是一趟专列, 开往北大荒的专列。车上上千名乘客(这是我估计的数字,年代久远, 记不清楚, 可能会有些出入), 清一色装扮: 羊剪绒的帽子, 蓝色的棉制服, 身边放着大小差不多的行包。
除了大串联的时候, 北京站好像没有这样热闹过。车上车下, 欢声笑语,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 气氛极为热烈, 用现在的语言形容, 那煽情的场面, 让人无法不动情。
和时下描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告别大城市时悲悲切切的场景绝然不同, 我们那时候不敢说是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但绝对是精神饱满、喜气洋洋,个个笑容满面。
理由很简单: 我们都是自愿到北大荒农场去的。那时候, 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的指示还没有发表, 没有任何行政组织的强迫命令, 也没有任何媒体的宣传动员, 我们这伙年轻人, 只是听了北大荒农场的简单介绍, 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就我本人来说吧, 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 有两个原因。
其一, 学校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经过近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学校里来了军宣队, 宣布进入所谓“斗批改” 阶段。每天早晨, 需要到校参加“天天读”。名义上是要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实际上, “天天读” 变成了“天天赌”, 全班几十个人, 四个人一伙, 分成若干组, 打扑克。我的初级扑克入门,就是在那个特殊年月里训练出来的。你想想, 接连几个月, 过这样的日子, 而且不知道还要过到何年何月, 长此下去, 该有多么的痛苦! 在这种情势之下, 不可能不考虑自己今后该选择的生活道路。
其二, 或许是因为家庭出身和情趣爱好的关系, 我一直对边疆垦荒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读过北大荒作家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 以及林青的散文集《冰凌花》、《大豆摇铃的时节》(有意思的是, 真的到北大荒之后, 很快地, 我就结识了林予、林青两位仰慕已久的作家, 并且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朋友) 之后, 对那里辽阔宽广的土地, 对垦荒者粗犷豪放的性格, 对北大荒的传奇和神秘, 我早已心驰神往, 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
而且, 在决定奔赴北大荒之前, 我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过了。在下本名“硕儒”, 是长辈们精心琢磨出来的。从这两个字里, 谁都能悟出他们对我寄予的期望。我的长辈们学历普遍不高, 只有一位叔叔读过大学。但在我们家里, 对儒学的景仰十分虔诚。还在上小学之前, 爷爷就从家里的旧书中捡出《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 教我认字, 还让我背诵其中的名句。所以, 后来当我从《论语》中得知, 孔子的弟子司马牛, 名“耕”, 而且算得上是真正的“硕儒” 时,不由得激发出了自己改名的灵感。
得知北大荒农场来北京招收农业工人的消息, 没有和家长商量, 我就兴冲冲地赶去报了名。填报名表的时候, 需要有家长的签字, 当时也是灵机一动, 拉过好朋友陆鸿明, 请他帮我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对陆鸿明帮的这个忙,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他感激不尽!
当然, 现在回忆起来, 当初下定决心走这条路, 脑子里并不完全想着投身边疆建设、报效祖国, 而更多地是想走出学校, 走出家门, 在广阔天地里自由地呼吸, 创造自己感兴趣的全新的生活。
可以想象得出, 千数名走进这趟专列的同行者, 尽管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家庭背景, 甚至还有着不同的愿望和追求, 但毫无例外地, 我们都是被北大荒人的精神和他们的传奇经历所感染, 满怀激情地聚在一起, 形成了奔赴北国边陲的浩荡行列。
列车驶出北京, 穿越宽阔的华北大平原, 直奔遥远的东北边城。
这样一群年轻人, 这样一列火车, 自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格外地引人注目。
火车在飞奔, 我们的心还在激烈地跳动。毕竟是第一次自己把握着自己, 即将展开自己崭新的生活场景, 心情怎么能平静下来呢?
就在这时候, 就在车轮和铁轨的混合吟唱声中, 忽然, 车厢里响起了悦耳的歌声。
独唱, 女声独唱, 声音高亢而生动, 饱满而激昂, 一下子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力, 数百道惊喜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歌声的源头!
看清楚了, 是她!
一位个子不高的女生, 正站在那里动情地歌唱。一身相同样式的蓝色棉制服, 穿在她身上, 肥肥大大, 显得不是很协调。仔细望过去, 这位不知名的女生, 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 圆脸上的一对大眼睛, 比一般的大眼睛还要大上许多, 又大又黑, 亮晶晶的, 灵光四射, 分外有神气。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像个大娃娃的女生, 从她喉咙里发送出来的声音, 竟是那么清脆、嘹亮、铿锵有力, 似乎还具有某种神奇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不知不觉地, 热烈而杂乱的聊天声消失了, 轰轰隆隆的列车行进声减弱了, 偌大的空间里, 仿佛只飘荡着她那动听而美妙的声音。
她就那样轻松而平静地站着, 除了偶尔甩动两根短小的发辫, 不时地抬起胳膊强调一下语气, 再没有另外的多余的动作。
说实话, 就是她那种单纯、朴实、平静、镇定和真诚, 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伙伴们。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 那抑扬顿挫的歌声, 竟然具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拨动我们的心弦, 可以激发我们的热情, 可以燃起我们胸中的火焰,可以调控我们的喜怒哀乐!
记得以前读过晚清著名作家刘鹗的《老残游记》, 其中描写女艺人歌唱的文字, 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我一直认为, 那只不过是刘鹗老先生精美的文字技巧制造出的特殊氛围, 人世间, 不大可能出现黑妞、白妞式的人物, 更不会有那种近乎天籁之音的绝妙歌唱。
但四十二年前, 在奔赴北大荒农场的火车上, 我仿佛被引入了刘鹗老先生描述过的境界之中!
刘鹗在《老残游记》里, 只是传神地形容了黑妞和白妞美妙绝伦的声音, 而我们之所以被同行的女生所吸引, 除了她那掷地作金石之声的歌唱, 还有她巧妙地传递给我们的歌词的内容。
时隔四十来年, 当年听过的歌词确实记不起来了。好在如今信息发达, 从电脑上, 找出了那首《铁道兵志在四方》: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离别了天山千里雪,
但见那东海呀万顷浪,
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那个)江南稻花香。
同志们哪,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 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劈高山填大海,
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
今天汗水下地,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
同志们哪,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看过这两段歌词, 我相信, 年轻一些的朋友应该能理解, 我们为什么会被打动了吧。
我们不像一两年后来北大荒的知识青年, 没有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光荣称号, 和“兵” 字毫不沾边。但是, 我们也是匆匆忙忙“背上(那个) 背包”, 兴致勃勃地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像铁道兵战士那样“志在四方”!
当年的北大荒开发, 不就是铁道兵将士们亲历亲为的吗?
我们要去的八五二农场, 不就是铁道兵八五零二师创建的吗?
天籁般的声音, 铿锵悦耳的旋律, 把我们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同样的意境, 同样的感受, 把我们引进了铁道兵和北大荒垦荒英雄的行列。
这首歌, 她不止唱了一遍。从北京唱到牡丹江, 然后换乘列车到完达山深处的迎春火车站, 最后唱到我们此次旅途的终点: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 彻底地完成我们从学生到农业工人的身份转换。
毫不夸张地说, 她的歌声, 伴随着我们在冰天雪地中斗志昂扬地行进了数千里路程。
那时候听歌, 不像现在, 没有近乎疯狂的喝彩、吼叫, 没有没完没了的掌声。我们更喜欢静静地聆听, 细细地感受, 默默地体味。然而, 实话实说, 她的声音在我们心底引起的涌动和冲击, 可以使我们历经四十二年而难以忘怀。我相信, 这种感觉, 还会陪伴我们走完生命的里程!
朋友, 你能想象得到, 这奇妙的力量能有多么巨大吗?
有过这番经历, 后来再听其他的歌唱, 总觉得提不起兴趣来, 无论如何找不到那种难得的美妙感觉。日久天长, 自然而然地, 就形成了我在本文开头部分说过的、被女儿指责为“落伍” 的心态。
或许, 这就是古人所述说的意境: “曾经沧海难为水” 吧。
随着歌声, 我们慢慢地知晓了这位歌唱者的底细, 对她的仰慕之情也渐渐丰盈起来。
写到这里, 朋友们可不要产生什么误会。这里说的“仰慕之情”, 绝对不是非分之想, 更不是男女间的情爱。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感情哪里有那么丰富? 况且, 我们的同行者大都分别毕业于男女分置的学校, 异性之间绝少来往。
以往在北京的时候, 碰到五一或十一的天安门广场晚会联欢, 需要和女校联合举办, 和女生手拉手跳集体舞。当时, 没有几个人觉得这是什么好事,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做出逃状, 生怕被老师“押送” 到联欢会现场。
然而,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总有特殊的现象出现。前面说过, 我们四中同学中有一位吕斌轩, 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很凑巧, 他和那位“歌者” 分配到了同一个生产队。“歌者” 有个女性味十足的名字: 阮丹妮。阮丹妮在北京就读的女六中, 和我们学校仅是一街之隔, 再加上阮丹妮一路上动人心魄的歌唱, 肯定为他们两个的感情交流提供了相当的方便和可能。
紧接着, 吕斌轩和阮丹妮顺理成章地结成了一对夫妻。
按说, 吕斌轩比我们大上两三岁, 算是学长。那么, 阮丹妮就应该是我们的嫂子了。可我却从来没喊过她一声“嫂子”, 甚至连“丹妮” 这样的昵称也没叫过。我们北大荒人的习惯, 总是直呼其名: 阮丹妮!
屈指算来, 和吕斌轩、阮丹妮得有三十多年未见了。
我时常想, 不知何时, 能再听一遍她唱的《铁道兵志在四方》, 寻找当年的那种感觉。
但愿这不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