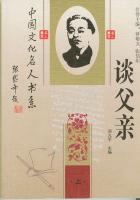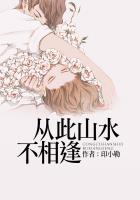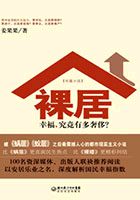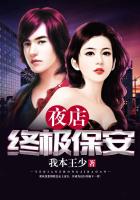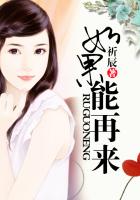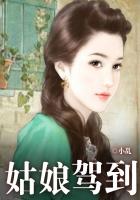洛阳处天下之中……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洛阳)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与唐共灭而俱亡者……予故尝曰:“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乎,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阳名园记》所列宋代洛阳名园19座,记述翔实,但用意绝非写景记事,它警告公卿士大夫们:不可沉醉园林美景,忘却天下重任。
李格非,生卒年不详,据《宋史·李格非传》推算,约生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约卒于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
这样,我们也许就能读出:《洛阳名园记》“出版发行”时,徽宗可能还没打算营造艮岳。
艮岳营建,约始于1104年。
这样,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徽宗、朱勔、蔡京等,在铄古震今的《洛阳名园记》中,读出的不是“唐之末路”,而是一种别样味道——好玩?生气?献媚,抑或是攀升工具?也许不一而足。
他们也许就此达成一个共识:李格非、司马光等,这些元祐党人,手下败将,跑到洛阳后,还在唠叨什么“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
更可气的是,司马光在洛阳搞了个“独乐园”,躲在里面写《资治通鉴》,也在喊叫什么“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啥都看洛阳,还要京师干什么?
这些人,竟不把朕放在眼里。朕孬好玩玩,你司马光的“独乐园”不就乐不起来了吗?
于是,徽宗君臣“风云际会”,建造艮岳的玩火计划,出台并被实施了。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反对党官员”在洛阳闭目静养时刮起的造园风,“吹”出了东京艮岳,把京师给刮垮了。
而且,人欲静而风不止,直把赵家天子的行宫,吹到了杭州凤凰山下。
这儿,是“艮岳之裔”赵构的梦中艮岳;在这儿,赵家天子的皇宫,竟然也不再追求庄严;整个行宫,都被建成了一个御花园——徽宗艮岳的杭州版本。
隋炀帝在洛阳建起庞大的西苑后,还觉得不好玩,于是这位中国大运河的策划人、第一任董事长,顺流而下,在江南玩翻了天;徽宗觉得炀帝这样干,太累太傻,不如把江南好山好水搬到汴梁来得痛快。艮岳起,赵家江山却成了残山剩水;赵构觉得他老爸也有点儿神经病,好山好水的,搬个啥,还惹得民怨沸腾?把京师、行宫搬过去,不就得了吗?
金人南侵,恰是赵构迁都的好借口、好机缘?
这样说,不会太冤枉赵构这位皇帝老儿。
在大宋皇帝中,他是徽宗之后最有艺术气质的人,诗、书、画都直追老爸。航海避难,他还雅兴四起,在温州江心寺写下“清辉”、“浴光”。
要是赵构有徽宗的大环境小气候,玩得可能比他老爸还浪涛击天。
他“直把杭州作汴州”,还不是小菜一碟!还都汴梁?
那儿残垣断壁,一点儿都不好玩了,还回去干啥?
金人非要,拿去就是。朕只要能有西湖、钱塘凤凰山,就够玩的了!
《洛阳名园记》出,而有艮岳;艮岳出,而北宋亡;北宋亡,而有《东京梦华录》。而在杭州“录”尽“东京梦华”,为汴京谱写下最后一曲挽歌的孟元老,恰恰正是艮岳督建人、户部侍郎孟揆——
孟揆,《东京梦华录》著作者。孟氏家族,谁作“梦华”?
《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是研究东京汴梁的左图右史。
一个是不厌其细的图像盛宴,一个是不厌其烦的文字满汉全席。两者“互补互助”,800年前的东京梦华,就会在今天复活。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尽管身世难以详述,但轮廓清晰,没有太多秘密可以追问。
而《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云遮雾绕,其身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这样写道——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京师)之下……”
《宋史·选举五(铨法下)》记载:“崇宁以来,类多泛赏,如曰‘应奉有劳’……皆无事状可名,而直以与之。孟昌龄、朱勔父子、童贯、梁师成、李邦彦等,凡所请求,皆有定价……”
史料告诉我们,孟昌龄在崇宁以后呼风唤雨,成为朝中高官。从时间上看,它和孟元老“到京师”,契合起来。
孟元老说得清楚:“先人”到京师做官,自己“渐次长立”;崇宁癸未,也就是1103年,他当在18岁以下。
从时间上,能判定孟昌龄和孟元老有着父子关系吗?
《宋史》云:“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许翰言:‘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聚敛金帛……而昌龄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势,顿取百年浮桥之费……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诏并落职:昌龄在外宫观,扬依旧权领都水监职事,揆候措置桥船毕取旨……”
孟昌龄家族是徽宗年间一统水利与桥船等国家基本工程建设、收受买官贿赂(见前面引文“凡所请求皆有定价”)、贪污公款的高官之家。
《续资治通鉴》载:“靖康元年(1126年)夏,四月……癸丑……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戬、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应奉,童贯西北之师,孟昌龄河防之役……所得爵赏,悉夺之。”
宋人徐度所著的《却扫编》还写道:“(徽宗)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虽前宰相,亦莫及矣。”
宋朝有严格的官员交流制度,一般情况下一位官员居京、任近、任远,是要隔几年轮换一次的。而在徽宗当政期间,孟昌龄“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稳居京师,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享受这种“待遇”的孟姓高官,在徽宗时代,唯有孟昌龄家族矣。
至此,孟元老似乎只能在孟昌龄家族成员中产生了。
《东京梦华录·序》云:“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这三条信息合在一起,就排除了孟昌龄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东京梦华录》写于绍兴十七年,距靖康元年已经二十多年,跟着先人在崇宁癸未(1103年)来到东京的孟元老,此时也该在60岁上下,而他的“先人”,至少应在80岁左右。也就是说,倘若是孟昌龄,他以这等高龄,不厌其细地写作《东京梦华录》,恐怕已经力不从心。
这样,我们就只能从孟昌龄的儿子中寻找《东京梦华录》的作者。
《宋会要辑稿》说,孟昌龄与其诸子——扬、揆、持、扩,在政和至宣和年间分居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都水监、将作监诸大要津,勾结内侍,“权倾中外”。
“扬、揆、持、扩”,谁作了《东京梦华录》?孟揆撰写《东京梦华录》
折腾得昏天黑地,想起学术顾问、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程民生教授。
说起此事,程教授当头泼来冷水一盆:这事儿太大、太糨糊,折腾点别的吧!
不依不饶道出折腾路线与眼下进程,程教授转愁为喜:“思路不错,有门儿!”
于是,他应承下来,帮助我们查找更多历史资料,以相互佐证。
首先,他闷头就给我们抛来一块“黑砖”:《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东京梦华录》的作者是孟钺。
孔宪易先生认为,《东京梦华录·序》中有“观妓藉则府曹衙罢”,此乃孟元老之“夫子自道”也——《三朝北盟会编》诏云:“开封府仪曹孟钺……皆以蔡京……孟昌龄之子弟、亲戚……”,以此推断:孟钺是孟昌龄家族中经蔡京保奏推恩而担当“府曹”的,是孟昌龄的“有服”本家,时在“宣和元年”。
但是,宣和元年是1119年,距孟元老离京只有八年。何况在孟昌龄家族中,那时能领这等小官的,定是个小混混类的“待业青年”——如此这般,孟元老在东京“数十年烂赏叠游”,何来也?
就此请教程民生教授,他很快就回了话:“查,孟钺是孟昌龄的孙子。”
这样一来,“孟钺说”,已然不攻自破矣——无他,年龄不符,孟昌龄孙子辈的人,与“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不符——从年龄上说,在这一时段,能够“渐入桑榆(晚年)”的,只能是孟昌龄的子辈——孟昌龄早已“渐入桑榆”,而他的孙辈,也就是孟钺,则正值盛年,不该在这一时段“渐入桑榆”也。
接着,程教授抛出第二个问题:注释《东京梦华录》的著名学者邓之诚先生认为,“元老本末不详”。邓先生在《东京梦华录注自序》中,曾批判清代开封籍学者常茂徕仅凭孟元老巧写“花石朱勔”,就推想《东京梦华录》作者是督造艮岳的孟揆,盖因常茂徕“不甚读书”、“异想天开”、“胸无黑白”云云。
这不是明明在说我们吗?
只好临阵磨枪,查阅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自序》。邓先生在“自序”云,孟元老“靖康丙午南徙”,也许没错;但邓先生忽略了一个过程或细节,那就是孟元老本人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说的,却是:“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
这个细节很重要。
先让我们看看“靖康丙午之明年”的大宋,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年一开头,已经禅位钦宗,做了太上皇的徽宗,带着他的一干亲信,南赴镇江,避祸金兵,其中有高俅、童贯等人。这次离京,在孟昌龄家族中,最有资格护驾相随的,也许正是孟揆。此时,孟揆比他老爹孟昌龄都更讨徽宗信任——是他,督造了艮岳!
而《东京梦华录》对京师每个角落,乃至皇宫之内,都多有详述;唯独不记东京城最最“梦华”的艮岳,其隐情,也许正在于此。
《东京梦华录》成于江南,江南百姓对艮岳恨得要死(艮岳甚至是方腊起义的导火索)。这也许是孟元老不署孟揆、不写艮岳的一大因由。
署孟揆,《东京梦华录》就臭不可读了。
蔡京、秦桧的书法不好吗?但,很臭很臭!
如署孟揆,《东京梦华录》就很难“出版”流行,能否留下来,则更加难说。南宋初年,谁会愿意出版将北宋引向灭亡的“奸臣”写的这类小书呀!孟元老还要在江南生活,就是为了自身安宁,他也会隐去其“揆”,不写艮岳——在江南,艮岳的“冤主”,太多太多。
倘若孟揆是在靖康元年一月跟随徽宗离开东京的话,那么到了二月,就有大臣奏请钦宗:诛窜昌龄父子,以昭示天下。
之后,在徽宗返京时,孟揆也许自“窜”了:他可能留在镇江一段时间,是故有了“靖康丙午之明年(建炎元年),出京南来……”;在“宣和六贼”相继被诛杀后,他为了避祸,继续南徙,到了杭州——不然,一个“出京南来”的“瞬间”,怎么会让孟元老花去了两年的时间呢?也许迁徙,从东京到杭州,持续了两年——这种迁徙方式与迁徙时间,也许只有孟揆才能“独享”——靖康元年初,东京衣冠还没有发生大迁徙;有的,却是清算“奸佞”的大诛窜。
建炎元年五月,赵构登坛受命,大赦天下,但“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见窜者,更不收叙”。而孟揆,继钦宗之后,再次成为高宗这位新皇帝的前朝遗老。
但很快,隆祐太后崛起。她与赵构携手,“一凤一龙”,都是开创大宋“中兴”局面的中流砥柱。甚至可以说,隆祐太后是“中兴”大宋的“定海神针”,她的每一句话,都在左右着赵构前行的方向。
隆祐太后崛起,自然能够改善孟揆的政治境遇,也让他能静心养老,不必担心被继续诛杀了。
为什么呢?
“查,隆祐太后姓孟,就是孟太后;孟昌龄,是隆祐太后的本家。”程民生教授说。
孟太后的哥哥孟忠厚,护驾太后,在1127年离开了东京。
孟忠厚有六个儿子,这就有了孟元老在杭州的“近与亲戚(有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
《东京梦华录》为什么署名“孟元老”呢?
孟氏家族起家,是从孟太后的爷爷“孟元”开始的。
孟太后本为元祐皇后,她是哲宗的皇后。
在应天府(今商丘),赵构即位,先尊孟太后为“元祐太后”——元祐是她的夫君哲宗的年号。
马上,赵构就知道自己错了,改尊孟太后为“隆祐太后”。
为避祖讳矣。
孟太后的爷爷,名曰“孟元”呀!
《东京梦华录》既然回忆旧都,连“建炎元年”都不想提,别扭地称之为“明年”——“靖康丙午之明年”。
隐去“建炎”,隐去“孟揆”,梦回东京旧都,梦回孟氏起家先祖“孟元”——其书,曰《东京梦华录》;其作者,曰“孟元老”。
“孟”、“梦”都是梦,书梦的是旧都,揆梦的是先祖“孟元”——他的老祖爷爷。
这,无疑佐证着《东京梦华录》,当出自孟氏家族之手。
在孟氏家族中,只有孟揆写《东京梦华录》,“诸相”圆融……
在杭州,孟揆“录”尽“东京梦华”,给杭州留下了一个梦回旧都的标本。没有《东京梦华录》指引,杭州人也许会错把杭州当汴州。没有《东京梦华录》指引,今天的我们也许找不到梦回东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