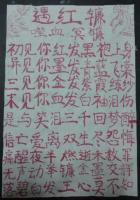当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自由在哈耶克哲学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此外,人们还认为这位《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作者可以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相媲美。穆勒研究自由的那部论着乃是在20世纪中叶出版的,而那个世纪则被称之为英国的世纪和自由主义的世纪。穆勒的着作反映了人们在当时对自由的普遍接受与他们对自由的信奉。
然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则是在大约80年以后出版的,而此时,自由已被“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搞得名誉扫地了,因此哈耶克这部着作的矛头乃是特别指向他们的。在这部着作中,哈耶克对自由在社会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经济(Keynesianeconomics)中普遍衰败的趋势感到悲愤。与人们认为哈耶克可以与穆勒相媲美一样,《自由秩序原理》(TheConstitution of Liberty)也被盛誉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OnLiberty)一着作在20世纪的后继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Law,Legisla tionand Liberty)的第一卷《规则与秩序》(RulesandOrder)也可以被视作是一部专门为自由而撰写的着作。
哈耶克本人也清楚地表明,他始终把保护自由视作是其论着的目的之所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序言中承认,这部着作乃是一部政治论着,是为“某些终极价值”而撰写的。该着作书名页上的引文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哈耶克的观点,即在这些终极价值中,自由乃是他所认为的最为重要的价值。
哈耶克征引大卫·休谟(DavidHume)的话说:“几乎没有一种自由是会立刻就全部丧失的”;紧接着,哈耶克又征引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话说:“我相信,不论在什么时代,我都会挚爱自由,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却准备崇拜自由。”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他的目的在于“勾画一种理想,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途径,并解释这一理想的实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显而易见,哈耶克所说的那个理想就是自由。《自由秩序原理》可以被视作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续篇,因为《自由秩序原理》这部着作的讨论确实始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亦即他在开篇所征引的Pericles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达致当下境地之道路为何”,而这一境地的特征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
这种做法明确无误地表明,哈耶克征引Pericles的文字的目的乃在于用一种使自由理念处于中心地位(亦即由强调法律之价值的文字所保障的那种中心地位)的方式来突出自由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哈耶克指出,“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thelaw)……乃是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之所在”。颇为重要的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结尾处还征引了亚当·斯密的两段文字,后一段文字所论及的便是“恒久不变的一般性原则”。
由于哈耶克公开宣称自己属于自由派,所以他明确认为这些原则就是那些自由原则。正如《自由秩序原理》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续作一样,《法律、立法与自由》则是对《自由秩序原理》的延续和阐释。哈耶克写道:“如果我早在出版《自由秩序原理》一书时就知道我会着手本书所试图进行的研究工作,那么我就会把那部着作的书名留下来,用在现在这部书上。”
《法律、立法与自由》乃是对《自由秩序原理》那部较为理论化的着作所做的一种实践层面的补充,因为它揭示了那些有助于在具体的社会中最大限度实现自由原则的宪法安排。
《自由秩序原理》出版1年以后,哈耶克在一篇探讨威胁自由的各种因素的论文中,即刻对其在该书中扞卫自由的思想进行了补充,他似乎是想加倍地确认保护自由的价值之所在。哈耶克指出,“对自由的有效扞卫必须……是毫无弹性的、专断的和奉为教条的,而且也绝不能对权宜之策做任何妥协。唯有把追求自由视作是一项政治道德的一般性原则,追求自由才能获得成功;而所谓政治道德的一般性原则,亦即在具体个案中对该项原则的适用并不需要一种正当性的证明。”
在这篇论文的结尾部分,他甚至指出,“自由并不只是诸多其他价值中的一种价值,亦即并不只是与所有其他道德原则处于相同地位的一项道德原则,而是所有其他个别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显而易见,这实是哈耶克对《自由秩序原理》一书德文版所草拟的那篇导论所做的一个重大修正,因为在那篇导论的草稿中,他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即“自由并不只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是大多数其他价值的渊源与条件”。自由不再被认为是大多数其他价值的渊源和前提,而是所有其他价值的渊源和前提。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秩序》中,哈耶克重申了这一立场:
“对自由的成功扞卫,必须是以坚守原则为基础的,而且绝不能向权宜之策做任何让步,即使在那种除了已知的有益影响以外无力表明对自由的侵犯所会导致的某种特定且有害的结果的情势下,亦须如此行事。只有当自由被公认为是一项在适用于特定情势时亦无须证明的一般性原则的时候,自由才会占据优位之势。因此,那些指责古典自由主义太过教条化的观点,实在是一种误解。
在我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缺陷并不是它在坚守原则方面太顽固不化,而毋宁是它缺乏足够明确的原则以提供清晰的指导……”此外,哈耶克还征引了斯特拉伯(Strabo)的这样一段文字,即“自由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最高的善”。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由在哈耶克的价值序列中所占据的不容置疑的首位性,并不能遮蔽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哈耶克来说,自由乃是法律下的自由,而且是根据法律而存在的。
哈耶克的确指出,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和无所不涉的并不是在法律下的普遍性自由(generalfreedom);在这种自由当中,只有部分是由法律所定义的并因此是在法律之下的。
人们并不能从哈耶克对“自由”(liberty)与“自由权项”(liberties)所做的界分中发现他的上述观点,因为他认为无论是“自由”还是“自由权项”都是法律下的自由。哈耶克的这个观点源出于他所做的其他陈述。
例如,他征引林肯的话说:“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对自由一词的精当定义”,他引证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关于人们把自由理解成众多情形的着名文字;此外,他还征引了其他一些无法就何谓自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论者的观点。
在这种并非由法律所定义的自由的周围所笼罩着的神秘网恰恰证明了这种自由的存在,而这一点又得到了下述事实的进一步确证,即对于哈耶克来说,“自由(libertyorfreedom)的状态”(亦即他所认为的法律下的自由)乃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的状态”。哈耶克因此承认,他的这种自由乃是某种关系性的(relative)状态,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它存在于社会之中。于是,他认为,必定存在着一种比社会中存在的自由更绝对也更宽泛的自由。由于社会中的自由乃是一种根据那个社会中的法律而确定的自由,亦即一种由法律所定义的自由,所以必定存在着一种无从界定的、超法律的自由;鉴于法律从其定义本身来说乃是限定自由的这个事实,这种超法律的自由肯定要比法律下的自由会受到更少的限制。再者,哈耶克指出:
“从最终的角度来看,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源出于我们对自己知识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承认。”人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限制了人的知识,当然也包括人关于自由的知识。这些局限性的存在导致了人们不断通过法律对那种普遍的、无所不涉的、超法律的自由中为人所知的那一部分自由做越来越多的规定或界定。
尽管上述论述表明哈耶克洞见到了一种比法律下存在的那种自由更宽泛的自由,但是由于哈耶克宣称“人类从未生存在没有法律的状态中”,所以他又强调指出,他所关注的那种自由(“每个人都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状态”)乃是一种法律下的自由。这在他所征引的Pericles的文字中是显见不争的。他参引了西塞罗(Cicero)的文字:“onmnesLegumservisumusutliberiessepossimus”(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他还赞同洛克(JohnLocke)对此更为清晰的陈述,即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并且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比较详尽地征引了洛克的观点。他对孟德斯鸠“将法治确认为自由的实质”和伏尔泰(Voltaire)信奉法律下的自由表示欣赏。
他在一篇论文中阐述了休谟关于“法律下自由”的概念。他称誉美国宪法是“一部自由的宪法”,亦即一部型构自由和保护自由的法律。他赞同康德(Kant)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他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自由“始终是法律下的自由”这个观点。
如果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说自由乃是次位于法律的。然而,这种推论却是与哈耶克的观点相悖的。虽然自由在法律之下,但是法律并不优位于自由。自由在形式上从属于法律这一点,并不影响法律在实质上从属于自由,因为法律只不过是一种视保护自由为旨归的手段。法律服务于一个目的。
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哈耶克指出,一般性法律规则的目的在于保护私人领域不受侵犯。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秩序》中,哈耶克用一整节篇幅来讨论“法律的‘目的’”。在这里,他在“目的”一词上加注了引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认为法律是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或者意味着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有一个目的,或者意味着强调另外一个事实,即哈耶克想指出人们对法律“目的”的不同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他征引了许多论者的观点,从康德强调正当行为规则较少目的性(purposelessness)的观点,到以边沁(Bentham)和耶林(Jhering)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视目的为法律的核心特点的观点;这表明在法律的目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含混不清之处和思想混乱之处。然而,哈耶克却明确无误地指出,如果目的指的是特定行动可预见的具体结果,那么边沁所主张的特定论的功利主义(theparticular istic utilitar ianism)就是错误的;如果目的指的是旨在一种抽象秩序(这种抽象秩序的特定内容乃是不可预见的),那么康德否定法律目的的观点便是没有道理的。
他赞同休谟的观点,即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它的作用,而不论其特定的结果为何。当哈耶克指出“一种抽象秩序能够成为行为规则的目的”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法律是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个目的不仅是实施法律规范(legalnorms)——这是对哈耶克视法律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的另一个证明——而且还在于增进自由。
哈耶克对于法律应予扞卫和支撑的那种秩序的要旨乃是明确无误的,亦即它是一种为人们提供社会中最大可能之限度的自由的秩序。只有自由秩序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内部秩序(cosmos),即大社会(thegreatsociety);他把“大社会”这个概念一直追溯到了亚当·斯密。他相信“在古希腊人和西塞罗经中世纪到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伊曼纽尔·康德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直至19世纪及20世纪的许多美国政治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伟大的传统:对于他们来说,法律与自由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最后,他还以KarlBinding所做的一个陈述作为结论:“法律就是关于人之自由的秩序。”法律之所以是一种关于人之自由的秩序,乃是因为法律通过把部分自由转化成具体的自由权项或权利而对自由这一不甚明确的超法律概念做出了规定。通过这一转换,法律把无形的自由转变成了有形的产权(properties),而这正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不可能忽视的。对于哈耶克来说,法律是“自由的基础”。所有上述文字都清楚地表明,哈耶克(颇为重要的是,他在题为“内部规则[nomos]:自由的法律”一章中讨论了法律的目的)认为,自由就是法律的目的,而且法律乃是实现自由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